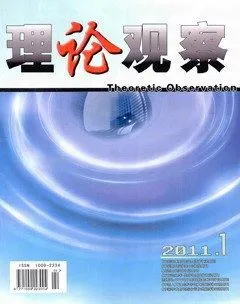集权体制下乡村治理结构的功能与绩效
2011-01-01张健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是集权体制。其功能表现在:完成了国家在乡村的政权建构,奠定了权威主义政治动员基础,控制着农民的行为,实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其治理绩效是:乡村社会呈超稳定特征,乡村经济缓慢增长。
[关键词]集权体制;政治功能;治理绩效
[中图分类号]D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79-04
集体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自觉的改造乡村社会的尝试。通过集体化运动,共产党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再造。关于这一历史变迁过程,学术界已经有了丰厚的学理性研究。但时至今日,关于“集体化时代”的概念、集体化乡村治理模式和集体化社会背景尚有不同观点,真正理清研究思路正逐渐达成共识,尚需借助当时的文献资料,寓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理解。
本文基本立足点是:认为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只是共产党倡行互助合作的探索,新区土改后,党内主要领导人对推进集体化的具体步子怎么走尚存争议。新区土改后,办互助组是集体化运动的开端。1958年底,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标志集体化的实现,而人民公社是更高程度的集体化。所以,“集体化时期”是指从新区土改后办互助组始,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前后历时30年。关于推进集体化的原因,笔者认为,集体化是共产党理想信念的诉求,推动小农经济集体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共产党政权只有占领农村阵地,开展阶级斗争,才可以彻底改造乡村社会,集体化是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集体化顺利推动的社会基础是在阶级斗争浓郁的环境中依靠政治压力改造了农民的灵魂,革命作为一种日常化机制成为农民生活的日常内容。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研究了集体化时期集权体制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治理结构的功能及治理绩效,设计描绘了中国乡村治理的一个范式。
一、集权体制下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土改打击了旧有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垄断势力,使得乡村内生性地方权威赖以存在的基础彻底消失,原来的权势阶fBNTQaGm8ur0nVXdZTKygw==层在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中迅速沉寂。土改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将权力渗透到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的紧密控制。但由于这些基层组织并不掌握乡村生产生活资源,所以他们对农民的影响也仅仅体现在一种政治强制力上,一旦牵涉到具体的利益,基层组织的控制失灵就出现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控制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乡村社会新的两极分化:二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导致国家无法掌握乡村社会粮食流通,产生了粮食供应紧张。解决这两个困境就必须要改变农民土地私有制,使农民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农场的工人。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如果希图更为深入地控制乡村社会,必然要推动乡村的集体化进程,从而实现在占有资源的基础上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掌控,集体化运动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展开的。
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终过渡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乡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经济生产单位。政社合一体制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管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国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各种发展资源,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
同时,为了实行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运动,通过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宣传动员,把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乡村社会,“创造了农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氛围和群体压力,并通过这种氛围和压力来提高或干脆说维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热情的”,从而建构起他们的政治意识,实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认同。集体化时期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了乡村社会的全部权力,控制了乡村的一切资源的“集权体制”。
二、集权体制下乡村治理结构的功能
集权体制结构下政府以一个政治化的干部队伍和一个同质化的集体为基础,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强化乡村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仅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占有,即通过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实现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计划性管制,而且培育出了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话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国家对乡土社会“全能主义”政治整合模式。集权体制乡村治理结构的政治功能表现在:
(一)集权体制完成了国家在乡土社会的政权建构
新区土改时,新政权将权力赋予忠诚革命的阶层执掌,而且不断重新调整权力执掌的标准,不会让其享有任何的自由空间,达到与政权保持同质性。所以,成功的土地改革“代价不是很大而且是暂时的,而收获却是根本性的和持久的”。
合作化初期,中央强调“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但是,在尽快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支配下。尤其是毛泽东将推动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后,合作化的进程开始提速。到1956年4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很快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11月,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行政权与经济组织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使得生产和生活集中化了,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形成了。而集权式乡村治理只有通过对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才能强化国家权威,就是说“那些具有政治势力,且试图创造和维护合法性或接受性的政权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靠政治社会化过程”。所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集权”控制并不仅仅是管理体系的强化,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伸到社会底层,而是通过支配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将其组织到集权体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激发了农民膨胀的自我效能感,不得不依附在集体组织之中。
(二)集权体制奠定了权威主义政治动员的基础
划分阶级成分,进行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彻底荡涤了乡村社会原来的权势阶层,此后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社会运动“非常彻底地动摇或瓦解(了)既有的行为模式,并激发出快速的社会变迁”。此时的“运动中国”中,动员扮演了关键的工具性角色。因为“在一个政治介入和政治参与观念得到鼓舞的世界里,民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以实现其利益和理想”。通过采取种种动员方式,中共改变了此前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权力不能够下达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状况。集体化的逐步推进,既是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也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里,动员的潜能同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这种动员方式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农村进行了剥夺式的社会动员,积滞了农民对国家的反抗,压抑了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能动性,使社会成员流于政治运动和权力争斗中,形成了权威主义政治动员方式。
权威主义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取人力资源,为领袖设定的政治议题服务,最终使得民众完成对议题的认同聚合,达到政治议题的目标,还是依赖权威政体高度强制性的政治身份管制机制。最能显示权威体制治理特色的是,对政治组织的垄断以及迫使群众弱小化,以至于群众政治参与的唯一通道是政治权威提供的动员运动。
与此同时,权威政体的政治运作也因此陷入长期困境:政治运动成为自己的宿命,停止则意味着政体的坍塌。权威政体下群众的认同聚合具有双重效应。统治集团暂时获得了革命或激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模式;大众则为免于身份剥夺带来的边缘化、异质化的恐惧,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高度压力体制下的政党与群众交往规则,决定了双方只能按照非公正原则展开博弈,群众往往违心地参与政治。权威主义这种低权利、高义务的体制,特别是暗含暴力色彩的虚无主义的阶级身份管制机制,造成了动员议题下高度一致的认同聚合行动。
(三)集权体制控制着农民的行为
为了活跃农村经济,东北局于1950年1月正式允许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并把这些作为活跃农村经济的具体政策。其后华北局也提出了“四个自由”的政策。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新解放区也实行了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允许“四个自由”是当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农村大多数农民。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买卖和租佃、雇佣、借贷关系,对恢复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克服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结束不久,1953年“四个自由”被当作提倡“四大自由”受到严厉批评,认为“‘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等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这样也将原本与当时农村生产条件简陋下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扼杀了。
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快导致管理混乱、生产松垮、分配不合理。为了整顿和巩固已成立的合作社,邓子恢强调:“编好劳动组织,三固定也好,四固定也好,要把它固定下来,劳动组织编好,规定一些制度,编好劳动定额,包工包产,这个东西不搞好,集体经营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希望搞的”。在邓子恢的倡导下,“包产到户”作为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的探索在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但是,随后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胎死腹中。
1956年上半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一部分农民由于形势所迫,更由于一些农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农户匆忙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年底进行收入分配时,他们的收入普遍减少,各省一般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另外,“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干部不民主,对社员的日常困难问题不照顾、不体贴,甚至还给予打击,伤害了社员对社的感情”。到1957年春,各地出现了严重的退社、闹社风潮。由于认为退社风潮是农村中的坏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并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的一次进攻,在处理农民退社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完全不考虑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一味地以意识形态划定生产行为。
(四)集权体制实现了国家权力意志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有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要实现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有限的农业积累。但是,如果土地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小农经济的生产,既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能满足国家战略,获得各种资源。所以,为了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国家必须将原先独立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使之与市场相脱离,对国家形成强烈依附,消除个体化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而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充分的保证。
通过土地改革,政府在乡村社会中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泰维斯认为:“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在合作化过程中,政府的权力使乡村社会改造顺利进行,农民被纳入到了新的制度之中。1958年人民公社全面建立,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大功告成,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到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与农村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结束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状态,为利用行政手段管理农村经济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也为行政机构全面介入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组织条件,实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全面重构,建构起了一个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为国家可以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城市工业投资的原始积累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集权体制下乡村治理的绩效
辛逸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理论界的赞同。但是,从乡村治理的视角来看,集权体制的治理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超稳定的乡村秩序;二是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一)乡村社会呈超稳定特征
新政权通过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获得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中国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农业进步,农户生活水平提高,并开始出现了当时所说的“中农化”趋势。同时,通过镇压反革命、划分阶级成分等做法,中共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确立了新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地位,为稳定乡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1956年出现了农民“退社风潮”,全国闹退社的一般占农户1%,多的占5%,想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广东省委1956年12月4日报告,“从1956年夏季以来退社的高潮先后发生5次,永宁曾发生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秋收以后,退社户已达7000户,占总农户1%,垮社102个,正在闹退社127000余户,约占2%”。然而,1957年社教运动的开展使之迅速平息。正如周晓虹所说:“总的说来集体化运动是一路凯歌、高潮迭起”。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会多灾多难。1959至1961年各地灾荒严重,1959年受灾面积62189万亩、1960年受灾面积80374万亩、1961年受灾面积80346万亩。全国总人口和乡村人口出现了递减,全国总人口从1959年的67207万下降到1961年的65859万人,乡村人口从1959年的54836万人下降到1961年的53152万人。人口出生率从1958年的292‰0下降到1959年的248‰、1960年的209‰、1961年的180‰;死亡率大幅提高,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是1958年的120‰的两倍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的172‰下降到1959年的102‰、1960年的45‰、1961年的38‰。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认为,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金辉认为,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但是,乡村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社会骚乱。“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引起了社员的强烈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四清运动扩大化,部分正派干部受到打击,一些农村党员被开除党籍,随意隔离审查,出现了打人、捆人的现象,甚至一些干部自杀、逃跑。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发展,并没有因为激烈的政治运动而导致乡村社会的混乱。
(二)乡村经济缓慢增长
集权体制下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使千百万被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丧失了个人责任感,对自我力量的幻觉沿着不恰当的方向急剧膨胀,以虚报产量为代表的浮夸风在层层批右倾保守的压力下越刮越烈。大跃进时期,广东省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乡甚至报出了早稻亩产36900多斤的奇迹。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由于中央没能及时而明确地予以制止,相反助长了这种歪风。陈吉元说:“下面的浮夸乱报,赢得了上面的喜形于色,上面的喜形于色又助长了下面的浮夸乱报。”
实际上,此时农业发展非常缓慢。1959年-1961年,粮食作物、棉花面积减少和产量呈下降趋势。195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91420万亩,1959年下降到174034万亩;1958年亩产105公斤,1959年下降到98公斤、1961年更是下降到8l公斤。棉花播种面积1958年为8333.6万亩,1961年下降到5805.4万亩;1958年的亩产为24公斤,1961年则为14公斤。已经开始好转的1962年同1956年相比较:粮食减产17%;棉花减产48%;油料减产61%;黄红麻减产49%;糖料减产63%;烟减产68%;桑蚕茧减产49%;水果减产13%;造林面积减少79%;大牲畜减少21%;猪减少10%:水产品减少14%。同时,1962年的经济好转也没有改善农民生活。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参考文献]
[1]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政治学导论[M],张定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C],//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8]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N],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1956-12-06.
[9]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迟福林,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12]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J],中共党史研究,1997,(02).
[13]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03).
[14]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J]社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