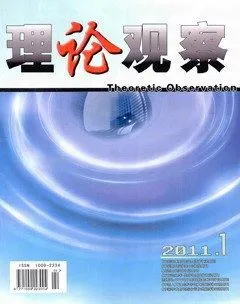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治理
2011-01-01温璐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人权问题作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解决某些主权国家难以涉足的人权危机中发挥了其力所能及的作用,但这些组织的行动同时也受到来自外界阻碍和自身不足的影响,行动效力受到了约束。
[关键词]NG0;全球治理;人权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62-02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分布地域、多样性、内部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同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一样,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例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等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保护人权的热潮。但是,由于人权本身就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且人权问题主要还是由主权国家参与解决,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参与解决人权问题上的效率很难估算;加之非政府组织内部固有的一些局限性,使得它们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受阻,影响了解决问题的效力。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的概念
当代全球化的速度与规模都是前人所意想不到的,社会领域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人口迁移、经济活动和全球环境都受到了全球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人民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各种“蝴蝶效应”。另一方而,全球化发展也致使各种全球问题变得异常突出。
戴维·赫尔德作为著名的全球治理理论专家,他的世界主义全球治理观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赫尔德的全球治理理论主张建立一种以世界主义原则和世界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全球多层治理的模式,其中,多层治理是赫尔德理论的核心。“多层”的含义主要指:参与全球政策制定的行为体不仅仅局限于国家,而且包括全球、区域、区域间、国家、次国家甚至是个人层面的所有行为体。这些层次之间不是一种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关系,每个层次都形成一个以公民自我管理为主导的自治共同体,也即在一个全球公民社会里,每一个层次都形成以公民为主导的有效治理。而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公民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非政府组织还没有一致的、普遍认可的定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黎青教授概括了学术界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指那些在政府体制之外而且不是根据政府之间的协议建立的、同时也不是企业的社会组织;第二种看法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第三种看法则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本文论述的非政府组织将参照第一种定义为标准。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发展中国家人权治理所发挥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得各国人民开始意识到对人权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践踏是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捍卫人权的话题开始逐步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就提出要“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概念”。1948年10月9日,联合同大会一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迄今为止对国际人权规范做出的最权威的论述。尽管有各种国际法与国际制度为保障,战后的六十余年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尽可能有效的解决,世界各地的人权危机此起彼伏,有时候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人权危机频发的地区,又往往不谋而合地相约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之中。
从大体上分析,现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权危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客观环境造成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受阻。这是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领土本身处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或者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国土资源丧失。第二,战争、政治和军事冲突、种族屠杀以及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生存威胁。第三,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不自由。这一点放在亟待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中看似无足轻重,但这一点也往往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借“保障人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的一个主要借口。
针对以上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治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权问题上,往往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首先,参与联合国人权大会的规则和日程设定。当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最主要还是由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解决,联合国人权大会作为解决人权问题最有力的途径,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也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选择。国际非政府组织只要取得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咨商资格,便可以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享有发言权,或是通过游说各国代表,使他们同意自己所提建议(如规则设定),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作为日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或是将本地区或组织所关注的议题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游说大会将这些议题纳入讨论议程,由此加快解决某些特定的人权问题。
其次,直接援助弱势群体或者人权侵犯的受害者。由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一些国家内部发生人权危机的时候,往往会谢绝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坚持的独立与中立就显示出了其优越性。例如无国界医生深入非洲腹地刚果(金)的伊图里地区对深陷种族屠杀囹圄的平民实施医疗救助;又如,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打响开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向所选择的医院以及6个身体康复中心提供支持,同时还帮助恢复供水与卫生服务,对被阿富汗当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或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拘留的人员进行探视,以及恢复或维持因连年武装冲突而失散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
最后,促进国际人权机制的完善,加速全球民族的进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联合国人权体系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通常,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人权方面制度的安排提出了新的建议,并且还通过国际分布到人权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展开工作,这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者制定保护人权的制度。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使得保护人权领域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变得制度化和规范化,例如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在联合国大会的通过都和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分不开。人权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追求最大程度的人权发展,客观上也加速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进程。
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发展中国家人权治理的局限性
在当今社会,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人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公民的认可,但是他们所宣称所要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还是受到了许多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局限性的制约。从外因来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存在着缺乏广泛认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从内因分析,由于人员和经费来源的制约,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也很难得到保障;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认同的“人权”观念存在着同有的差异,价值观念上的分道扬镳也使得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
首先,缺乏广泛认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国际法学界通常认为,国际法主体是指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交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且具有为维护其权利而提起国际诉讼能力的国际关系参加者。在现阶段的国际社会中,完全符合这个定义的国际行为主体只有民族国家、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民族解放组织,目前的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这一点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是不相符的,它不能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拥有各项特权和豁免,不具有法律、资金、财政、安全等各项保障,同时,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缺失也容易使国际社会产生对其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疑虑。为此,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了长期的努力,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决议,允许享有咨商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在经社理事会上独立发表意见,这实际上是为缺乏主体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中开了一个绿灯,这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努力的结果。
其次,独立性受到挑战。国际非政府组织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营利性,他们的经费来源大多局限于会费、社会捐赠以及政府和企业赞助,经济来源的局限性成为他们活动受限的最主要障碍之一。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保障行动的流畅性,不得不接受一些国家或政府的有条件资助,这使他们的行动不得不打上政府支持的烙印,组织行动的自由度大大降低。并且,在全球多层治理的模式下,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这两个治理的主体在方方面面都打着交道,而现阶段,作为社会的一个代表,非政府组织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主权国家的制约。当主权国家有意将在其本国范围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以及行动空间纳入自己的政治影响领域内时,就会利用国内立法承认,控制经费来源等方式影响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在现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要在一国内很好的行动,还不能跳出主权国家的势力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后,人权话题的敏感性。人权的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人权作为对抗强大国家机器的压制性权力以及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诉求,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可。但因历史、文化和文明背景的不同,各国对人权的理解和看法也大相径庭,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以国家综合实力为依据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概念的理解就不尽相同。虽然也存在着许多内部差异,但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人权是从个人出发,追求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其中,享有个人财产自由,行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有待提高的发展中国家看来,其他一切基本权利都只能在保障了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享有,生存的权利始终排在其他权利之上。并且,战后至今,一些国家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直接插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问题上去,又产生了人权与主权的激烈碰撞。出于历史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民众对非官方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产生了警惕心理,直接使得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受阻,或是他们的行动对象不予配合。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大规模种族屠杀中),某些人权践踏者还会以主权为借口,抵制一些善意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展开救助,这些组织的志愿者甚至不能保障自己应享有的人权不受侵害,这更为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设下了重重障碍。
虽然种种局限极大地妨碍了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但是从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诞生以来,他们就以“世界的良心”为宗旨,为遭受强权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权受害者摇旗呐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以大赦国际为例,从1961年组织成立起,直到1997年,组织共对4570位受害者进行了法律援助;来自全球的80000名志愿者参与到85个国家的紧急救援中去;10000余名医护人员参与了多个国家的医疗援助。正如这个组织的座右铭所说的,“与其诅咒无边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一支”,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一盏盏烛光,发光发热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能平等享有人权带来了希望。
[参考文献]
[1]李刚,论戴维·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2]李刚,论戴维·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3]王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
[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EB/OL],http://www.icrc.org/web/CHI/sitechio.nsf/htmlall/afghanistan?opendocument&link=home.2009-06-11/2010-01-08.
[5]王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6-397.
[6]蔡拓,吴雷钊,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分析[J]理论与现代化,2009,(06):27.
[7]王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8.
[8]王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06-407.
[责任编辑: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