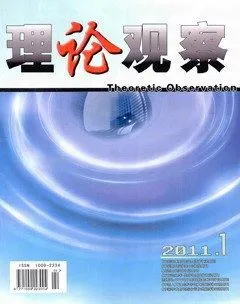中国画的哲学视角
2011-01-01王健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中国画必须与哲学联系起来,建构起一种“关系性视角”。在这种关系视角下,运用哲学来思考人类学,运用人类学联系宗教学,运用道家学说来实践哲学思维辩证方法。这是哲学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理性归纳与抽象思维的根本法则。对于促进我国哲学,宗教学,人类学及艺术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主要意义。
[关键词]道家思想;宗教;中国画;神秘主义;象征主义;阴阳关系
[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54-02
本文正是在充分认识到理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画与哲学关系性视角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人类学与宗教学的社会契约,这表明哲学思想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基础。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
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欧洲,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都有它现实的不同点。直观的欧洲绘画是我们感觉和情绪的反映,就像招人喜欢的大自然和世界作品一样,我们喜欢这些去代表物质世界。我们准备“走进”库茵芝和稀什金的世界,去欣赏他们的艺术思维,默默地穿梭在神像与大师之间。我们要明白,这仅是中国绘画的宗教本质,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能承担多少掌握的各种格格不入的中国艺术,能在遗失的神与人之间供给这种紧张的灵感。我们在欧洲的文化上到处可以遇见基督极端的善良与灾难,罪孽与悔过,宗教的爱与人类的极端贫困。通过自己的流传百世的作品作为一种痛苦的告别。
老子、孔夫子不能提供宗教所回答的问题:“那是谁,谁关心你?”。
道家思想与宗教没有关系,道家思想原本就具有无神论的倾向。老子的道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神,神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而“道”则是非人格化的。道是无个性的,因而可见,在宗教和道之间中国人没有产生个性的态度。就像弗拉基米尔·洛沃里提到的,前面的宗教就是各种艺术表达的价值的范围,在中国形成的独一无二的典型神秘论。
道教任何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一种学说,就像基督教一样。他们可以掌握象征主义的方式、方法在文化范围里。我们可以从道家的圣人那里学到各种真理一样的知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逻辑学的冲突。他们一致完成“入世”和“出世”的象征主义对世界观认识的论证。因为我们跟随弗拉基米尔·洛沃里察觉到了道家哲学——这种思想不是简单关于生活文化条件的,而是自身境界领会的一种文化。
有些研究领会道家思想,就像尝试形而上学解释世界一样。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些。各种没有思想的世界,产生开始结束并保存在对立的思想上,而这也不是形而上学,这仅是告诉我们道是反作用于世界的。我们提倡老子领会美丽与真理,具体的绘画目标应用到文化中去,而对象实际采用的是人,没有逻辑学普遍的抽象的推论,就像被弗拉基米尔·洛沃里察觉到了。
孔夫子就像老子那样,在充足的这些文字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过宗教,因为他们不回答这些带着神圣基督教思想的宗教生活。天地是自然的存在,没有理性和感情,它的存在对自然界万事万物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因为万物在天地之间依照自身的自然规律变化发展,不受天、神、人的左右。与弗拉基米尔·洛沃里在一起,我们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些问题的宗旨:两千年前在坟墓里曾经存在或发生过,没有被奉为神明的孔夫子与没有被批准的宗教信仰人道主义学说吗?这个问题总是带有欧洲哲学的声音。回头我们将回到有趣的中国文化中。中国将来一定要有高级的国家传统共性、历史性、还有要保持孔夫子的预约祭祀者,怎样才能满足中国人对宗教的需要等等,答者建议很多,而我们停留在资料数据资料中。
如果重新转变对欧洲艺术的看法,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绘画大师对许多中国前辈画家的尊敬。中国人在现实世界里,画家反驳自己喜爱的那种创作,他们只是颜色的填充。这些各种卓越艺术作品的代表的方式关于家具、屏风、陶器和瓷器。像弗拉基米尔·洛沃里,自己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的见证者与注视程度,和关于创造者的想象力,甚至自己也随心所欲的制造大师的灵感等问题。
仅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能直观的看到鸟的翅膀,然后大师准确精细的进行独一无二的表达。有没有事实证明说明关于中国的画家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就是放在研究花草上了?
中国绘画能召唤出视觉观众源源不断的感觉吗?中国传统绘画没有灵感,而他们在直观的领会中找到了共性,在共性中找到了自己。中国画家注重个人的理解,讲求意境,给人以丰富的寓意与联想,注重抽象的理解。世界集合统一体组成全部的事物,每个事物都具有组成部分或组成元素,是人类通过认识实践活动从自然事物中发现、界定、彰显、抽取出来的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中国文化具有特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反映到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上。
我们生活在很小的世界中,我们通常通过传统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去认识一些国家的艺术。
艺术作为宗教的内部思想,从第一视角去看全部不明白,画家阐述内部而不是外部方面的生活。它喜欢这种神秘的关系,在丰富的生活中搜索神秘,而画家将成为创造者。假如说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的创作是“精神与物质婚姻”的果实,那么各种创作将确定为画家创作的特殊认识。画家的幻想反映在自身的创作上,转换为艺术创作的内容经验与精神素质。他有绝对神圣的个性或盲目的力量吗?人有怎样的天分?除了丰富的价值观他有很高的诚信、直觉、思维、感觉还有什么?可以经过分析自然世界,或他应该处于神秘状态么?暂时我们不认识自然的本质,人或神或作为中国人来讲的天、地和人,我们没有注意认识任何文化传统艺术的终结。
老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无为”与“自然”。通过日常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阐述了世间万物存在,都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论说了对立统一的规律,确认了对立统一的永恒的、普遍的法则。“无为”字面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这就是说:“道”是绝对自由的,不取决于自身的性质。因此道遵循发源的原理,就是品行,与宏观的人道与微观的天道相符合。老子无为思想是生命的一种智慧,一种对“道”的理想化追求。“无为”在老子那里同“道法自然”同等看待,“无为”就是“自然”。宇宙之本就是《道德经》中的“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奉献,有所作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随心所欲,而是要以辩证法的原则指导帮助画家寻找顺应自然、遵循事物客观发展的规律。圣人不应该根据个人的主观限制愿望与偏见,抵抗自然周围的物体与现象。相反,他应该“遵循物体”。所有物体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真正的圣人是自由的,摆脱偏见与成见:他同等看待富贵与贫穷,从永恒联系、从宇宙联系、从不忧伤的生活联系、从不忧伤的逝去联系、认识自然的必然性。
中国画区别于纯净的完美艺术。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创立了中国画发展的文化氛围。这两个流派为适应各历史时代的要求而改变。
中国的画家是那样的神秘,道家可以称为自然的神秘主义的变种。其神秘性、不可触摸性和无限作用的最直观和最形象的譬喻。只有扎根于形象,才会使蕴含的丰富性、概括性、抽象性和外延性得到能动和富于想象力的发挥,老子对道的这种不拘常规的描述方式,给予后来道家人物自由放荡的思想和行为以先导和启迪意义。道家在世界观上同孔子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天(阳)、地(阴)是原本存在的,而道家神秘主义认为是道派生出来的,并由“道”进行支配。道家渴望宇宙和谐与世界全部存在着的联系。画面呈现在我们之前描绘的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深处的内在含义。自己选择物体进行描绘,给予客观自然的新思想,因为我们考虑到,神秘的道存在着参与。为了保守的石头,不属于动物界的物体,为了中国人,他将充满生活。处于“道”中的画家,用艺术的形式去表现内在生命意识,完全集中对自然界的观察与理解,理性的描绘对自然的细致与观察是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倾向性的。
在中国画的画面上全部对准象征主义,全部都是固定的思想寓意。树位于中国画的植物象征之首位。它主要是象征常青之树,是一种有价值生长在悬崖边缘或顶部或水体岸边的植物。因此,最常出现的松树——永恒(不朽的思想)之树,天生生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外部不利条件无懈可击,力量的象征)。竹子是与松树同义的,生存能力的象征与松树相似(弯而不折)。常青树也可以熟悉的灌木林、小树林,森林。杨树、橡树等象征男性。竹子是一种很高尚的植物,在中国画面上有欢迎的寓意。竹子象征长寿与精神力量永恒。这种常青的植物生长在寒冬,在强风下不折不弯,所以它形成了坚固堡垒的精神。它也可以联想为对生活的热爱。如果竹子同梅花一同描绘——这就是象征丈夫与妻子。在一组欢迎竹的图片上,松树和温柔的梅花,那时候他们象征着永恒的友谊。这三种植物是不可分割的朋友,因为他们保留着冬天里的绿色。
道本身作为形成生存永恒的溪流,道可以看到全部,不需要领会什么,画家喜欢刻意的描绘它。在《道德经》中说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是大无边而运行不息,运行不息而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又返回本原。
在阴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紧张状态——大与小之间、天与地之间、阴阳之间等等道处于紧张状态。为了找到完美,在自身的山水画画面上相互存在着对立的不足。山在中国艺术史中是非常常见的形态,同快速致富相联系。山是大地的最高点,所以它离天堂最近。“花鸟”是中国画三个方向之一,因此,确定花要适应具体的鸟。凤凰、孔雀、公鸡和野鸡同牡丹一起描绘;鸭子同荷花一起描绘;燕子同杨柳一同描绘;鹌鹑和鹧鸪与稷一同描绘;鹳同松树一起描绘。人的经验和自然生活之间不存在一次或永远的边界的建立,换句话说,物质世界保持质量不是科学解释的对象。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而道家思想的影响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但是道家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在两千多年前,道家思想将客观世界还原为可认识的物质的存在,以道家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观察体验客观,深切的体验到宇宙间的阴阳关系的对立。对立的双方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并且能够反方向逆转。老子认为这样的变化才是自然的本质。
中国人建立自己的绘画与绘画理论,基础课题的建立未出现自负与相互转换的对立,而是存在永恒的溪流,事实上,是明确“物质精神”与道的关系的统一结合。
[参考文献]
[1](春秋)李耳,蒋信柏,道德经[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李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