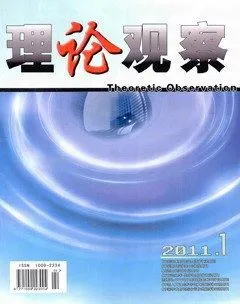浅析协商民主的价值与挑战
2011-01-01张宁宁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期,在当代得到了许多政治学者的青睐。协商民主强调平等、自由的公民参与公共协商,进行公开理性辩论的话语过程。平等、自由、协商、公共、理性、共识是其核心。协商民主的决策程序体现了高度的合法性,有助于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培育当代公民精神。
[关键词]协商民主;合法性;公共协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46-02
协商民主兴起于20世纪后期,近十几年来,协商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界可以说是一门显学,正如其代表人物萨瓦德所言,“协商的理念正在重塑我们对于民主的想象”。其理论渊源既有对古希腊传统民主理论的继承,也有对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是现代政治学家们为克服代议民主的局限,进行深入反思的理论成果,对于提高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培育现代公民精神有着重大的价值。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
协商民主是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关于协商民主,不同的政治学家界定的角度也都有所不同。政治学者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协商民主是一种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的回应文化间对语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它要求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对话和讨论达成共识,制定公共政策。正是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使得公民们相互理解其观点,以最大程度的合乎公共利益为目标,使决策的制定具有高度的同意性,从而获得更高的合法性。政治学者米勒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形式,“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做出的,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这种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做出的判断,以及应该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和程序。”这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强调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平等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愿意去倾听、考虑他人的观点。经公共协商制定出来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参与者原初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体现了参与者可能在经过充分的理性辩论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偏好,这种偏好的转变也是之前的民主形式所忽略的。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要求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公民都参与到公开性的协商过程中来,平等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尊重、考虑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并且考虑到了偏好的可变性,只有做到这些,政治决策才会有更高的合法性。
二、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通过公共论坛式的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无疑比代议民主、远程民主更具合理性,它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增强了公共决策合法性,培育了公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美德,使公民内心的责任感增强,从而也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公开化和更具责任性。
(一)增强公共决策合法性
公共决策合法性的获得途径就是要参与者的认同,协商民主通过利益攸关的参与者直接进行公共协商的民主程序之后才做出的决策,得到了受决策影响的参与者的同意,正如“决策具有合法性,不只是因为它碰巧符合大多数公民未经审视的偏好,而是因为它已经经过了正当性的考验。公民应该能够认为这种方式做出的决策是合理的”,因此经协商制定的决策也就具有了很高的合法性。在协商过程中,受决策影响的公民都能自由平等的参与到讨论中来,并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深切思考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人的观点,在认真比较了各个观点之间的分歧之后,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说服他人或者是被他人说服的途径达成共识。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公民都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样就超越了公民狭隘的私人利益的视角。这样每一个参与者都对政策的前提、实施以及之后的结果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由此做出的决策才具有高度的认同性、合法性。
(二)培育现代公民精神
良好的公民精神代表着妥协、宽容、履行义务与承担责任等良好品质。“在协商过程中,公民通过交流理解其他公民的思想与经验形式的内在逻辑,学会理解并尊重他们,因为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每个公民都可能存在着差异性的规范信念和责任。”通过充分了解不同的人性与道德信念,人们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对方,妥协和节制自己的需要等,这在无形之中培养了现代公民精神。公民在协商中通过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会逐渐意识到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也应该分担一部分社会整体的利益,所以在对政策进行协商时,会自主的产生一种社会责任感,从而做出对整个社会都有利的决策,而不单是从私利的角度考虑问题。社会日益多元化,通过公共协商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公民变得更具包容性,能正确对待文化的异质性,理解多元文化,为社会发展建立必要的信任基础,从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现实社会中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集体责任感,包容性等等这些良好的公民精神是协商民主所必须的,同时也是在协商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三)促进政治决策科学性
国内政治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破解选举民主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缺陷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注重公民的协商讨论,经过“讨论可以减少公民个人有限理性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具有‘附加’价值,二是讨论具有‘倍增’价值。”可见,经由协商讨论做出的政治决策更具理性与科学性。协商民主强调通过参与、协商、合作确立认同的目标来实现公共利益,有利于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在有关决策的各种协商中,公民自由参加,公民与政府是平等的主体,通过平等交流,反映公民的利益诉求,促使政治决策充分体现公民的利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对决策具有高度的认同性,因此对制定出来的决策也都有遵守的自觉性,有利于政府执行政策的顺利执行,并且公民对自身认同的政策具有责任感,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开放的协商环境赋予了协商民主以合法性、合理性,促进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正如博曼所言“协商民主价值最好的辩护就是公共协商提高了政治决策的品质”。
三、协商民主的挑战
协商民主以其平等自由的公民经过公共协商、讨论达成共识而取胜。然而作为一种新发展的理论,它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多方的挑战,当前的多元社会的复杂性、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不平等,以及公民自身的态度都对协商民主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否克服这些挑战也是协商民主理论能否具体指导实践的关键。
(一)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
20世纪后期,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等逐渐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认同,社会分化也日益加剧,社会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要求也逐渐分化,导致社会分歧愈加扩大。这种环境中的公民可能很难形成一致的目标,难以有效的达成共识,不可否认这是对协商民主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也承认,“要真正实现自治,需要大小适当的政治单元、相对的政治平等、充分的文化同质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不能达到足以引起冲突等等,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协商自治才成为可能”。而当今社会的现实却与之相反,社会多元价值认同越来越突出,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各自协商,而不是相互协商。并且在多元社会中,社会并没有提供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则,不同的文化体系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但从相反的一面来理解的话,协商民主通过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恰好可以缓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为缓解多元文化之问的冲突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协商民主必须面对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通过一系列的公共协商,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进而制定公共的框架和原则。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实际也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动力,正是这个多元性的挑战会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理论的进步与完善。
(二)面临社会中存在不平等的挑战
文化多元的存在使得协商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在协商过程中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的现象给协商也造成了很多障碍。哈贝马斯列出了很多相关事实“公共领域的结构反映了信息获得方面的难以避免的不平等”,以及“协商过程本身想要运作就得有资源这一个事实也导致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占有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公民知识积累的差异使得公民的判断思考能力有着明显的差别以及社会处境不平等导致公民缺乏有效参与的能力等。由此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减少了协商参与者的效力和影响力,由于他们缺乏施展公共能力的机会,他们的利益需求将很难体现在决策之中,这也影响到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我们把协商的这种不平等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权力不对称,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可能会影响到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途径,使得那些处于劣势的公民可能都无法进入到协商过程中来。二是交流不平等,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影响了公民的参与能力。不可否认,“一些公民的表达、说服能力是要比普通公民好一些,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更擅于游说,更容易被聆听”,这导致大多数公民都认为他们所言的都是合理的主张。然而有些人的意见很明显的因为表达能力欠缺,知识不完备,环境因素等,不如那些人的有说服力,可能会遭到忽视。三是公共能力的缺乏,指的是一些公民或团体无法有效的利用机会来影响协商过程。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力是有差异的,某些公民能够抓住机会施展能力,而有些公民则缺乏此能力。所以协商民主要取得新的发展也必须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处理好协商民主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总之,协商民主理论有其独特之处,平等自由的公共协商过程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协商民主理论的新发展的前提在于承认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异,核心在于继续保持公共协商、话语交流,从而达成共识。协商民主能够有效的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培育公民精神。平等、自由、公开、协商、理性辩论、认同已成为协商民主的关键,要使协商民主更好的赋予实践,良好的制度框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通过不断完善现有的制度建构来促进协商民主的中国化,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谈火生,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David Miller,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Disadvantaged Groups?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New Perspectives,Edited bv Maurizio Passerin D'entreves,Manchester Universitv Press,2002,P201,转引自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03).
[4]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03).
[5]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6]李君如,协商民主:重要的民主形式[N],文汇报,2006-07-27.
[7][美]詹姆斯·D·费伦,作为讨论的协商[M]上海:三联书店,2004.
[8][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2]谈火生,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