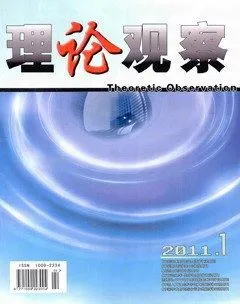法律是否值得信仰
2011-01-01罗施福李津津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人类社会有人治与法治两种经典的社会治理模式。梁治平在《法辨》中为我们提示了中、西方社会两种貌似相同、实则迥然的社会治理传统;厚重的人治传统深深地嵌入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这样的传统与我们现代追求的法治理想形成了文化裂痕,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法治理想的实现。以自然的名义宣布期待中的理想的西方自然法追求,为中国的法律人提供了一种信仰的路径,一种努力的精神。
[关键词]《法辨》;人治;法治;信仰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38-03
一
有人类,即有社会;有社会,便有社会治理之命题。这是因为人类利益诉求的差异,必然意味着人类社会有合作,有竞争,更有冲突。在这种合作、竞争或者冲突中,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治理模式,那么,合作必然失败,竞争必然无效率,冲突将导致毁灭!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斯·C·诺思所言:“若是没有约束,我们将生存在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于是,既作为一种渊远的传统,也是一种深刻的思想,人类长期以来一直缠绵于法治与人治这两种经典的社会治理模式中。
在人治模式中,少数的治理者掌握着社会的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等物质与精神手段,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规导,并实现社会秩序的治理。由于人治建立于人性本善的假说上,而治理者的个人品性将直接决定着这种治理模式的效果如何,所以,人治强调治理者的个人道德素养与道德发展。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人治模式中,治理者也会强调“法”治。但这种“法”治,是在人治之下的“法”之治理。也就是说,“法”的治理服务于人治之目的。所以,人治之下的“法”,仅仅是一种手段和工具,仅仅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仅仅只是一堆事实、一种现象。这样的“法”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寄托,没有信仰。
在法治模式中,法被奉为社会系统的最高权威,成为凌驾于其他个人与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法治不关注人的个性,而强调法之优良品性与法之普遍遵守!法之优良品性,意味着法的制定是集合多数人的经验,经过多数人的智识审慎考量而成。这样的“法”,尽可能地排除“法”之“兽性的因素”,成为“没有欲望的理智”,并因此而获得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社会基础和真正根源。法之普遍遵守,意味着,任何个人与组织都不能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人人皆应在法律之下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法治”模式中,法律获得普遍的感召力与至上的神圣性;法的践行不依靠其严酷与冷峻,也不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而是依靠公众对法的真诚信仰与朴素情怀;人们对法律没有恐惧,而只有敬畏,没有排斥,而只有信仰、归属与依赖。
正因为人治与法治的上述迥异性格,使得法治在人类的历史思索中被界定为人类社会治理的理想与追求。
然而,即便如此,法治始终离不开“人治”。如,任何形态的法都是人的建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人类基于自身的经验与智识而制定的法律,定然深嵌着立法者的主观性与局限性,而这些特性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法治理想与追求。于是,为了对这种人类制定法可能具有的局限性进行指引和限制,西方社会产生了自然法观念。尽管这种根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和哲学文化土壤中的自然法观念,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了若干不同的形态,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和近代古典自然法等;而且,“除了名称相同以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而大相径庭自然法观念,却都有着一个基本的内核:除了人类制定的实在法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更高形式的法律存在,即自然法;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自然法应当成为人类制定法的基础,也是评判人类制定法善恶的根据。换言之,西方社会秉承二元法观念,并通过自然法这样的假说将法律至上、权利、正义等信念深沉地潜入社会治理的思维模式中。作为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一种心态,自然法就是这样绵延于两方社会的法治实践中。无疑,在这样的理念下,法治之“法”不仅仅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同时包含着人类内心的深刻追求;不仅仅只是一堆事实,同时还是充溢着生命神性的价值。
西方有自然法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呢?我们有自然法传统吗?我们的传统为何?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曾这样形容中国:“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法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种“快乐”的迷雾?
二
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梁治平老师的《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置于书架上已经很久了。记得,七年前,带着懵懵懂懂,带着一知半解,坐在图书馆里勉强读完。读完之后,有激情,也有迷惘!那时,我们激情于我们的法治理想,迷惘于我们的法治之法。然而,正因为懵懵懂懂,正因为一知半解,我们除了感受激情,感知迷惘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思考。
两个月前,无意间打开了尘封于书架的《法辨》,有了再读的想法与冲动。坐在书桌前,翻开《法辨》,慢慢地渐入意境,终于有所体悟,终于明白它为什么会是一种经典!
《法辨》是一本文集。收录的文章都是梁老师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并多刊发于充满着思辨与呐喊的《读书》杂志。或许,以当年的视域来看,梁老师的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带着愤青色彩,然而,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百废俱兴、日新月异的发展大潮和在这强烈冲击下迫切寻找方向的学究之风,才能催生出这样真诚恳切、又具有超越理想色彩的文字。即便放在当下,尽管时间已经流逝很久,文化已经有了更多的沉淀,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思考,但这些文字仍毫不褪色。这是一位负有历史责任感的法律思想者,他以文化和传统的高度,通过中外法律制度、渊源的对比,来探寻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法的过去、中国法的现在,也明了了中国法这样的过去与现在的深刻根源。
掩卷而思,慨叹不已:中国法治的现代化竟是那么漫长那么复杂那么难以明确方向的一个过程!或许,真的怨不得中国的法律人不争气,也真的怨不得中国的民众对法律没信仰。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法并非值得奋斗卓绝的法律,也并非真正属于民众的法律。
三
在拉丁词汇中,形容“法”的词汇很多,典型的是“jus”和“lex”。据考证,这两个词都包含权利和正义之义。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法”的记载。被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说文解字》关于法之古体——“灋”的解释。《说文解字》该该字的解释包含两个部分,即“平之如水”与“触不直者去之”。按此解释,我国古代的“法”即已蕴含“公平公正”与“惩罚”之义。然而,据学者蔡枢衡的考察,“平之如水”,“乃后世浅人妄增”,不足取。“触不直者去之”却有充足的依据。此外,我国古文中还有两个字可以找出来训为“法”,即“刑”与“律”。据梁老师的考证,刑、法、律可以互训,如《尔雅(释估)》:“刑,法也”;“律,法也”。《盐铁论(诏圣)》:“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并没有西方古代“法”关于权利、正义之内核,而其核心在于刑罚,在于威慑,在于制裁,所以,其本质更在乎于一种惩罚工具,一种统治艺术。
为什么均是一种治理文化,西方古代法蕴含权利、正义之义,关注于法之优良品性,而中国古代法却没有呢?这与两者的历史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尽管古代文明形态各异,但在社会的初期治理文化中,它们都有着一个近乎相似的命题: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并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换言之,此时的社会治理之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在家族中,“个人”被淹没,“个人”并不能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法律权利;他所遵循的规则,是其出生的场所,以及来自于他作为其中成员的家长所给他的强制命令。进一步而言,权利的配置取决于人们在家族中的身份,而义务则无时不刻纠缠着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所以,从最初形态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法与西方古代法在价值追求与功能界定等方面并无重大差异。
然而,西方古代法却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并完成了历史性的穿越:个人从家族中分离出来,成为法律的目的。这种穿越的典型体现就是契约精神的贯彻与个人主义的确立。契约,意味着自由合意,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平等,意味着个人以充分的理性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与契约精神相呼应的是个人主义。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偏见与误解,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它是一个中性词,是与家族主义或团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于一种自主人格的主张与张扬。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与独立价值,他不但要维护这种价值,还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完全责任。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核心。所以,在契约精神与个人主义面前,法律的制定必然蕴含这样的一个假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并被赋予同样的法律人格。尽管西方古代法的这种转身与穿越具有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具有艰难性与反复性,但它毕竟实现了。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难怪乎,英国著名的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梅因在其经典的著作《古代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自此,西方古代法正式确立了其两大核心功能:一是政治功能——法是不同社会集团共同遵奉的准则,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二是民事功能——法是私人事务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仲裁者,与市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与理念认知上,在西方社会,法律应该被信仰,法律可以被信仰,法律被信仰着,便成为它的必然性格,也是其法治的全部秘密。
反观中国古代法,其始终纠缠于制裁,始终没有走出“人治”工具的窠臼。我们国家的产生是建立在氏族征伐基础上,是“由战争中强化的权力和族长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并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为国家的组织方式。一种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系统始终以高度的戒备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服从与被服从状态。一种恰当推演是:法,代表着威慑,代表着征服,代表着服从;是“赤裸裸的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是一族一姓施行其合法武力的正当化工具。这样赤裸裸的威慑、制裁、征服最为直接的载体,即刑。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之法,已然不是一种西方的法治之法。所谓权利,所谓自由,所谓正义,对于中国古代法而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自此,我们悲观地发现,这样的“法”,除了给我们制造恐惧,还言何信仰?
其实,我国历史上曾存在着极具“温情”的“礼”治传统。作为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礼,是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之上的包罗万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在很长时期,“礼”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强调对祖先、对神意的敬畏,并成为社会治理阶层进行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根据。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正因为礼的这一特性,使之成为弗朗斯瓦·魁奈眼中最为完美的自然法,成为伏尔泰眼中能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的至善之法。然而、遗憾的是,这仅仅是因为距离而产生的误解之“美”。其实,在礼治的规则体系中,“礼”对个人的要求,首先是对社会或国家、家族的各种义务,主要表现为要求和禁忌;“人的定义只能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发现,人的位置只能在亲疏贵贱的等级序列中确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最高纲领表明,人只是家族的一份子,君王统治下的一份子;个人始终无法从家族身份中分离出来,并作为独立的单元来对待。毋庸置疑的是,对这种的“礼”治的推崇与强化,必然衍生了个人地位的异化,也意味着服从被人们视为个人的首要品质。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推崇与强化,个人与家族、国家之间形成了奇异的关联。一种水到渠成的结局便是,对荣耀者的推恩与对犯禁者的株连。所以,在我国古代这样的“礼”不是西方哲思中的自然法,而只是人治模式下另一种治理文化。我国春秋史上曾存在过令人津津乐道的“礼”“法”之争,即法家强调“法”治,即务法,儒家强调“礼”治,即务德。然而,不管是务法,还是务德,这两种治理文化都没有离开“人治”的本质。所谓务法,乃是只信奉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所谓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两者的差异仅仅在于统治方式的不同选择而已。所以,秦汉之后儒法合流,“礼入于法”。这除了与时势变迁和统治者经验日益丰富有关之外,更在于两者内在性质的共同。
就这样,中国古代法以这样的品性在中国社会的数千年发展中始终秉持着,并形成了厚重的传统,深深地嵌入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里,法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神圣的”。所以,尽管在中国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古代法在形式上已经消沉歇绝,并为所谓“泰西”法治所取而代之,但那种源远流长的“法”之认知与体验,始终在我们的民族心态、我们的行为模式中顽强地延续着。纵观现今之中国,为什么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了,但总是会牵扯进那么多不可避免的案外因素?明明有法,明明自己就是受害者,但人们却总是情愿绕过法律,去找关系,去上访?执法者为何总是堂而皇之地认为执法即为特权?为什么我们常常把权利救济的希望寄托在某个道德贤明的领导人身上呢?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会成为我们别样的“国粹”呢?“……恰好不是各项成文的法典、法令、而是法律生长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包括民族的观念与心态,是这些东西决定着法律的命运,它们才是支配社会的真实的法律。”自此,我们找到上述现象的根源,但同时也令我们看到了一个暗淡的结局:法律应该被信仰,法律值得被信仰,在我们这里,或许,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然而,这就是中国法的一切么?我们的法律学人应该就此而沉默么?中国法应当如何,我们的未来在哪呢?
四
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这样的观察确实鞭辟入里。任何法都无法割裂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也只能选择继续在这片曾经生长独特历史的土壤上继续酝酿未来。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现在实施的法律制度与我们的文化存在着某种意义的脱节与断裂。我们现代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是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代表着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然而,这样的精神价值,这样的传统,恰恰不是我们的文化与传统。不仅不是,而且还存在着背离。于是,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出现了“法律死亡”的征兆。所以,梁治平老师在《法制传统及现代化》作出了极为精当的评论:“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如果不能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难免陷入尴尬境地,旧的业遭破坏,新的却无以产生”。
看来,改变是必须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梁治平老师在书中给了我们一种选择、一种方向、一种希望:“两种或多种文明的融合往往会进发巨大的力量,产生新的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于欧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于日本,都是如此。”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期待这样的法律,它既承继了我们的传统,又映照着西方法治文明的精髓,既照顾了我们各式的情感,又能坦然面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狂澜,成为一件既国际又传统的文明瑰宝!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希望,虽美妙但又有些近乎渺茫。因为“古代社会是相对静止的封闭体系,与身份所表示的那种社会状态正相吻合。而当代社会则不能不是充满变易的开放系统,在现代化的压力之下,身份关系的不合理性愈益突出,并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演成尖锐冲突”。
或许,中国法应当是什么,应当如何,本身并没有绝对的答案,而只能在社会变革的深刻脚印中,在无数法律人的持续探索下,在思考、碰撞、融合的明天,才会慢慢地水落石出。但西方的法律人给了我们一种勇气、一种追求的启迪:“现实的法律往往不是应然的事实,已然的事实并不总是期待中的法律。否则,为什么要以自然的名义宣布一个期待中的理想?”“我们很难想象,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一直到近代启蒙学者,两千余年间,(自然法)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曾经占据过那么多智慧的心灵,唤起过如此纯洁的理想……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看成是特定时代的偏见,一种幼稚可笑的怪想。如果我们拉开距离,以一种富有同情的眼光去观察它,或许能够发现,在它那幼稚而又偏执的面貌下面,隐伏着人类心灵热情而大胆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会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终止,它将与人类同在。”所以,中国的法律人,总归是要有那么一点点担当,总不能因为不争气就甘于不争气的。中国的法律人,有没有勇气,从自己做起,哪怕被误认为传统的叛逆者,也要高昂起头,在法律下,做一个真正的膜拜者?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7.
[2][春秋]孔子,论语·子路[O].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9.
[4]林吉辉,名不符实的“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评赵明先生《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EB/OL].http://artl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5636,2010-11-8.
[5]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蔡枢衡,中国刑法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170.
[7][汉]桓宽,盐铁论·诏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22.
[8]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6-97.
[9]佚名,礼记·曲礼[EB/0L].http://www.confucius2000.com/ziliao/lijil.htm.2001-5-4/2011-2-23.
[责任编辑: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