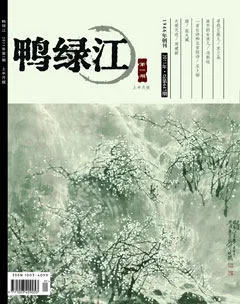记忆的翅膀
2011-01-01高维生
鸭绿江 2011年1期
高维生,吉林人,满族。1962年12月26日,生于延边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午夜功课》《有一种生活叫品味》。从1988年开始,在《民族文学》《中华散文》《文学界》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诗歌和散文介绍到韩国、马来西亚,并被选入多种选本。
一
一切都是从大巴车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小刘村教堂在意识中飘荡,促使我踏上寻访的路途。我和往常上班一样,背上随身的黑兜子,装着两支中性笔,硬壳笔记本,一盒名片,手机,还有面巾纸等一些零碎的东西。
大巴车出了城市,在国道上奔跑。我没心思观望闪过的情景,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车载电视播放的流行音乐与机器的噪音合谋,在车厢里充斥,让我无法为耳朵竖起一道隔音的墙。我只好把思绪抛向天空,寻找安静的地方,回味从少得可怜的资料中读到的小刘村教堂:
1927年,美国宝血会传教士在阳信县小刘村建天主教堂,设小刘村教堂医院,借诊病之机传播教旨,发展教徒。1943年,传教人员撤走,医院关闭。
短短的信息,概述了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教堂。我在晃动的车上,无法用想象拼出教堂的形象和漫长的经历。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了教堂正面的照片,青砖凹进的距形的匾池,上面水泥铺底,镂刻“进教保佑”几个大字。下面是教堂的大门,探出的门上,有三角形的拱顶,一个黑色的十字架标志。就是这幅照片,引起我对小刘村教堂的兴趣。
我准备了很长时间,搜集资料,向当地的朋友打听教堂有关的人与事,我一直弄不明白,是在地图上随意地圈到小刘村,还是沿着黄河的脉搏寻找,抑或是穿着教服的神父骑着马,或一路徒步,直到再也抬不起落满尘土的鞋子,最后选择了这个地方。文史资料对教堂的记录很少,我像闯进了一团乱麻中似的,梳理不出头绪。小时候,在我家的不远处,有一座天主教堂,“文革”期间被砸烂,窗子拆毁,圣像被铁锹铲掉,整座教堂没一处遮挡,风儿从中穿过,鸟儿在屋顶筑巢。我们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常爬上不宽的台阶,在墙上涂写,在墙角撒尿,坐在二楼光秃秃的窗台上,注视街上来往的行人。有时向下投掷纸叠的飞机,看着它飘飘悠悠地落在民房的旧瓦上。它坐落在一条胡同的路口,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人们叫它天主教堂,别的就不知道了。教堂的神圣和庄严,早被红卫兵砸得无影无踪了,没人敢提“教”字了。我又一次接近天主教堂的时候,已人到中年,我想了解历史上有过的人,有过的事件。我要把这一切,通过文字,传达给更多的人。
2006年,刘宝德主编了《梨乡风情》一书,他是阳信的“文史通”,田野调查做得非常好,我们有过多次接触。交谈中,我问过小刘村教堂,他也没新的线索,关于小刘村教堂,他编的书中记载:
天主教堂建于1916年,分路南、路北两个院落。路北院间隔为东西两院,西院有礼堂一座,瓦房38间,为教士专用房。东院有房40间,后20间为职工和贞女宿舍,前20间为女子学校。路南院为修女院和经言学校,有修女楼两座,经言堂17间。
1925年,教会开设教会学校,初设两个班,以宗教课为主,外加算术、国文。1934年改称道德学校,全部招收女生,设高级班10个,初级班1个,每班学生定额50名。2名修女讲宗教课,5名教师分讲国文、算术、历史、地埋、自然、公民等。1935年,高神甫创办磐石学校,设高级班2个,初级班1个,全部招收黄河以北各县的男生,两学校分别于1939年、1940年停办。
1935年,开设教会医院门诊,由3名美国籍修女为主治医生,全部为西药,一年后改换中国籍修女为主治医生,1941年停诊。
文字粗线条地写出教堂的外貌,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主要人物和事件始终没有记录。时间叠在时间上,很多生命逝去,曾经生活过的人和思想过的头脑,虔诚的信徒都消失了,只留下了教堂。青砖、红瓦、十字架,如同醒目的黑体字,在天空干净的大纸上,每天在书写着日记。透过教堂的窗子,向外面的天空望去的时候,会读到很多的东西,这和向里面眺望是不一样的。青砖墙围合的空间,聚集了天、地、人、神。
二
我看到了。一拐过路口,踏上乡村的主路,我就捕捉到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贴在天空上。无数次推断、猜测过的教堂,几乎是疾速地飞来。教堂就在眼前,而我用读过的文字和想象拆解,寻找被丢弃的历史。路两边晒满了棒子粒和光裸的棒子芯。这些棒子芯,冬天的时候,作为引火的烧柴,必须晒得干透。一排泥土的房子,夹在砖瓦房中显得落旧,新与旧的建筑,在时间中摩擦,旧的消失了,新的存下来了。
教堂管理员孟宪亮是个老教徒,1943年出生,他老家在滨州秦董姜镇,那里有一座更大的天主教堂。2009年神父让他来这里服务,打扫教堂的卫生,种菜,做饭。一个老人,天天围绕着教堂忙碌,守护着它。我来时,他正好有事去邻居家,教堂的大门上锁,无法进去,我只好透过院墙,观望院子里的教堂。教堂的门锁上了,紧闭的大门,使空间保持独立的寂静,只有阳光,穿越玻璃,带着天空的气息,在空间里自由地游荡。经受了许多个四季的转换,青砖墙淋了太多的风雨,砖中蕴满了阳光的气息。勾的白墙缝和青砖,褪掉了色泽,有了沧桑的感觉。关闭的大铁门上,贴的白纸黑字的横幅“恭贺圣母荣如升天”,还是那般清晰,只是白纸变得脏污了,铁门顶端的十字架伸向天空。
孟宪亮老人来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朴实,脸上有一股祥和,让人一见面就拉近了距离。他生在教徒的家中,在父母的祷告声中开始了人生,神灵的爱护佑着他长大。院子里很干净,红砖铺地,我在教堂的门口,看到砖缝中长出几朵黄色的野菊花。我蹲下身子,注视它们,这是来做礼拜的教徒们必经的地方,无数双脚经过,却没有一只脚,暴力地踩上去,毁掉弱小的生命。孟宪亮老人打开教堂的门,一片阳光跟了进来,秋天的风儿在空间里回荡。我注意到老人的双手,垂直地立在裤线两边,从不乱动。经受了生活磨难的老人,站在阳光中,脸上露出单纯的笑。
一排排长条椅子和跪凳,现在空荡荡的,等待着虔诚的教徒诵经,面对天主进行赎罪。
我沿着窄小的楼梯,登上了二层阁楼。在岁月中,木楼板保养得不好,有的地方残缺,踩上去微微颤动,吱吱作响,再也不可能承受超负荷的重量。我放缓了脚步,走在上面,害怕哪一只脚稍用力,会踩落下去。教堂的二层阁楼是“唱经台”,作为主日乐队演奏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台坏弃的风琴,踏板的木板变黑,再也演奏不出圣歌了。我似乎又听到巴利奥斯的《大教堂》,此曲描绘了清晨去做礼拜,在教堂里虔诚祈祷的情景,以优美的音乐语言描述大教堂在清晨中的形象,一点点地从远处推来,在纯净的天空背景下,几颗没有离去的星星,还在眨着眼睛,在大教堂的尖顶徘徊。阳光从彩色玻璃中透过来,使教堂带上了温暖的气息。我对风琴有特殊的情节,在龙井东山小学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风琴。每一节音乐课,都要有几个壮实的同学到别的班去抬风琴。音乐课是一个女老师教,齐耳的短发,皮肤白白的,她坐在风琴前,椅子上放一块绣花的垫子,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格外的艳丽。她弹奏琴键,脚不断地踩动木踏板,风琴在她的弹奏下,发出动听的乐曲,她领我们唱音阶,然后教唱歌。风琴磨得很旧了,从窗口冲进来的阳光攀到琴身上,我学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下课的时候,我们要把风琴抬到教员室,老师夹着谱本走出教室,她的身影一消失,同学们就掀开琴盖,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在黑白键上胡乱地摁,还有的人伸出脚,没节奏地踩踏板。音符痛苦地乱跳,一个个地蹦出,又快速地逃离。在这架风琴上,我们跟着学会了好多的歌——《火车向着韶山跑》、《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国际歌》……
我趴在窗前向外眺望,看到了散落的院落,一条探过来的枝桠,枝叶遮住了半扇窗子,阳光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美国建筑学家丹尼尔·李布斯金说:“光线进到屋内,会如何照下来,改变、跳跃?石头、玻璃、木头、光——这些不起眼的材料,建筑师能用它们达到更高的目标,表达想法与情感、诉说故事,描绘历史。”光和木头,这两种最质朴的东西,形成了一股生命的力度,构成了庄严的氛围。2001年,春日的一天,美学家潘知常,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大教堂,待了很久,他在给几所高校的讲座中说:“那天我想来想去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做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而思考的结果,就是我终于意识到,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逼’出了信仰的维度。也就是‘逼’出了作为终极关怀的爱。”很多人走进教堂,很多人离开教堂,人们在教堂庄严的大厅中,对世界和生命的思考不一样。
从教堂里走出来,我和孟宪亮老人去看他种的北菜园。一排破败的房子,门敞开着,一缕光溜了进去。园子里种着一垅垅葱,几垅辣椒,地上爬满了冬瓜秧,肥硕的冬瓜,圆咕隆冬地趴伏在叶子中,瓜蒂联结着秧蔓。地头有一挂喇叭花,花冠由白渐变成粉红,一朵朵,鲜艳美丽,在教堂的背景下,显得充满生机。无数朵喇叭花,昂起头,对着天空吹出自由而快乐的曲子。它凝固的姿势,迎接着太阳的初升,送着落日的离去,在夜晚等待风儿和星星的絮语。孟宪亮老人用手指了一下盛开的花说:“多么有生命力,它是在神灵的护佑下。”我们在菜园子里,观看着阳光下的植物。我在菜地的中间,从另一个角度注视教堂。乡村教堂,规模不大,但它的神圣和庄严,却让人有着敬意。规范自己,不大声说话,没有乱七八糟的私心杂念。
路南和路北,教区分两个院落,“路南院为修女院和经言学校,有修女楼两座,经言堂17间”,这一切是材料上记载的数字。南院已经荒芜,没有人居住,很少有人走进院子里了。我还是请孟宪亮老人打开南院门,毕竟这么远的路途,来了就要都看一看。由于不常开锁,钥匙在锁眼里困难地转动。
我拍了很多教堂的照片,多少年后也许会变得珍贵。我还有一个想法,当地的作家冀新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曾在这里上过初中。也许哪一间房子,她就曾经住过,在院子中和同学们玩耍过。院子里比北院荒凉多了,坚硬的青砖,一层层地剥落,房子残破,门窗脱落,杂草长满了,蔓生在门和窗子前,这里感受不到神圣,只有无尽的荒凉和落败。我搜尽词汇,却找不到准确的词,表达触目的情景,纳兰性德的“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倒是适合当时的心情,衰旧的建筑,吹得我的心塞满了沧桑。那条不平整的砖路,呲牙咧嘴地向前延伸,心沉重了,思想就复杂了。在岁月中有的建筑消失了,存下来的也在经受着危险的到来。窗子上挂着一只老式的路灯,白瓷的灯罩,结了很多的锈痕,灯泡落了尘土,不那么光亮了。一根白塑皮的电线,接着灯头,墙上穿出了一个细眼,电线从这里进去。电灯的开关在房子中,有人居住时,天黑了,一伸手就可以,点亮饱经风雨的路灯。现在没有人住了,夜晚的院子也不需要灯光了。
一只肥大的灰喜鹊飞过,留下的声音还没来得及凝固,就被天空融化了。几声狗吠,从远处传来,院子里有一股股凄凉的气息在游动。
拐过房角,第一扇窗子上拱形的水泥面的窗眉上,留有“文革”时期的残迹,上面有一行“要斗私批修”的大字,不知哪一年用黄颜料写上去的,淋漓了风雨和霜雪,现在只能勉强辨出字迹了。一株马缨树,树冠蓬开,遮盖住一片墙,树快要超出房子了。这和冀新芳记忆中的情景有些相似,碗口粗的马缨树,树龄也不小了。我来的时候,早过了开花的季节,院子的寂静和空旷的凄凉,与树的名字有了巨大的反差,我不知道将来它和这座房子还能坚持多久,命运如何。我的记忆来了,要有耐心存下这里的一切,它是留给后来的怀念。
三
我和冀新芳终于见面了,我们一行人吃完午饭,我并没急着赶回滨州,而是来到了一位文友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急切地想了解她在小刘村教堂上初中时的情景。
南院有一排翠绿的柏树,还有几棵马尾松。夏天开的花,红艳艳的,很漂亮,香气浓郁。这些把她快速地卷入过往的生活中。过去的生活,现在是记忆了,思绪扯动的情感,让一个中年人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中,拨开时间积攒的尘埃,讲述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少年求学的艰辛,这里有说不清的滋味。她家是在西大寨村,离学校六七里路,背着书包,穿着母亲做的布鞋,推开家门,一次次走在乡村的土路上,那一年,她只有12岁。初一都是步行去学校,初二才会骑自行车。年龄小,不可能天天回家,同学们都住校,一周回家一趟。大家一天只是吃早饭和晚饭,中午不做饭,饿了就啃冷馒头。菜用罐头瓶盛着,从家中带的咸萝卜条,豆瓣酱,虾酱。平时吃窝头,到毕业的那一年,才能吃上馒头。开运动会,上体育课就在教堂前的空场地上。教堂后面是一片小树林,边上有小卖部。上体育课的时候,她们就站在小卖部门口看女主人做饭,她做的包子很小。我听冀新芳的口述,她原生的生活细节促使我调动想象力,恢复和修补过去发生的事情。
圣·奥古斯汀说:“什么是时间?如果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什么是时间。如果我试图向提问者进行解释,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时间……我们衡量时间,但是如何衡量那种不存在的事物?过去已逝,将来未至。”时间是什么,它就是生命划过时的痕迹,是一种记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文革”的影响,小刘村天主教堂,只剩下一座高大宽敞的空房子,所有宗教设施均被破坏得荡然无存。由于初中扩招教室紧张,教堂摇身一变而成为教室。教堂比普通教室的面积大得多,课桌摆放在中间,五六十个孩子坐在里面,教室里都是土台子,砖头垒的垛子,上面架着水泥板,同学们一年四季趴在桌子上。夏天时还较凉爽,一到冬天手触在水泥上,冰冷浸骨。四周还很宽绰,这给学生们提供了追逐耍闹的地方,学生们的吵闹声在空旷的空间响起,发出一阵阵的回声。下雨和雪天,沾着泥土的自行车,随意地堆放在边上,硕大的教室里,仍然不觉得拥挤。
乡村没有电,夜晚的所有活动全凭一盏油灯,她住的西面的邻居家,晚上念经,一家人的身影,被光投映到泥土墙上。一道土墙,切割出温暖的氛围,那团火焰生出的光,映出一个个教徒的影子。瘦弱的光,搜寻教徒的身影,剪贴到泥土墙上。黑色的剪影,勾勒出生命的轮廓,虔诚的祷告声,沿着光的指向,奔向辽远。墙外面是村庄,是大地,不远处的教堂,隐在夜色中,被月光裁剪出的十字架,贴在夜空,融入到无限之中。乡村的夜安静,虫鸣在一段段拉扯着夜向深处走去。
在校上学的孩子们也很虔诚,入团是不允许信仰宗教的,每次发展团员,老师就做工作,提醒他们不要迷信。他们表面应承,却依旧我行我素,既要入团,耶稣也要照旧信。老师偶尔家访,看到墙上的耶稣画像,只好一笑而过,老师拿他们也没办法。
听说有个女学生特别虔诚,立志长大后做修女,大家都以为是戏言。多少年后,同学们聚会,问起她们家姐妹俩,原来都去了上海修道院读书,真的做了修女。小刘村的男女老少都信奉天主教,他们白天种地,每天晚饭后,不约而同地奔到一户德高望重的老教徒家,伴着一盏孤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在他的带领下,念读经文。说是念,其实听起来更如同小合唱,声调抑扬顿挫,也许类似于唱圣歌吧!几乎每家的墙上都张贴着耶稣及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耶稣幼儿时幸福的一家,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等。
秋天的阳光,从前窗涌进,欢快的光,切断冀新芳对过去纷杂的回忆,夜晚想家时,独自对着微弱的灯火,手指触摸灯盏上的油渍的感觉,又在指尖上出现。把自己投入往昔的时光里,翻动日子的书页,寻找发生过的事情,听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的呼喊。记忆被凝固在时间里,有一天,一旦打开,它将洪水一般地滚涌出来,在现实中闯开一条河道,将人推入“五味”的水流。简陋的泥土房,没有富丽的装饰,在窄小的空间里,她做着美好的梦想,好好学习,到远方的城市中生活。她也通过幽幽的、柔柔的灯光,用生命读到了信仰。
她的讲述,使我对教堂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认识,一些怅然飘来,往事并不如烟,而是真实地存在于记忆中。情感照亮了回忆的道路,重新体验流逝过去的生活,很多消失的东西,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向外延伸。其实,它们保存得完好,只是人们在人生的路上匆匆地走着,来不及整理与思念。生命在记忆里一次次地醒来,又一次次地睡去。
我的记忆中有了这座教堂,教堂记忆中有了我的出现。
十月的鲁北平原,深秋的夜晚,要多披一件厚衣服,抵挡袭来的寒意,我回到遥远的地方,整理田野调查笔记和在场的感受,想着远方的教堂。时间长了,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去过小刘村教堂的人,永远不能忘记它朴素的样子,坐落在大地深处。
责任编辑 盖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