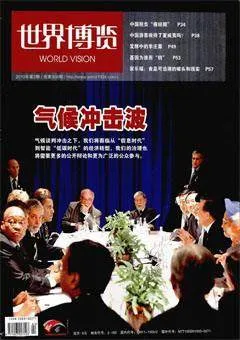波匈事件的中国版
2010-12-29行光
世界博览 2010年1期
1956年的中国,虽然出现退社、罢工、罢课、请愿与游行,但在处理-类似波匈事件的群众骚乱中,中共表现出了政策上的灵活性。行光
1956年6月上旬,波兰波兹南市来盖尔斯工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拉开了影响深远的波匈事件的序幕。在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武力干涉之下,到了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电逐渐平静下来。
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 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匈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知识分子反思社会主义制度
《内部参考》是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刊物,1949年创刊;1964年停刊。从其1956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列波匈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电出来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刚去波兰是否妥当?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
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 “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 “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 “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 “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 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 “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 “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 “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农民退社、工人罢工
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
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
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起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56年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
渡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
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中共的让步和安抚措施
195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人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 “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人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
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lO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 “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到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主张消减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是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在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 “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
(本文根据沈志华教授的文章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