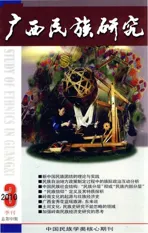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壮族经济史
——壮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2010-12-27覃乃昌
覃乃昌
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壮族经济史
——壮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覃乃昌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文明类型。岭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是稻作文明类型,这里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的先民适应岭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创造了稻作农业,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岭南早期文化是由这里的原住民族的先民创造的。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是壮族开始在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生存和发展的时期。但是,从秦到清中期,岭南壮族及其先民的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这一时期我们仍然把岭南视为壮族或壮族先民地区。清中期后直到民国时期岭南汉族人口增多,我们才将岭南的一部分壮族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称为壮族地区,并以此为依据来了解和研究壮族经济。一个纯粹的壮族经济是不存在的。
岭南文化;起源;稻作文明
一、岭南的民族构成
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一是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某一区域并形成村落、街道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世居民族。广西的世居民族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共12个民族。世居民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原住民族,即土著民族,另一部分是迁入民族。广西的原住民族有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5个。迁入民族有汉族、瑶族、苗族、回族、京族、彝族、仡佬族7个。
秦汉时期西瓯骆越形成,汉族迁入。
宋元时期壮族、侗族形成,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迁入。
明清时期仫佬族、毛南族形成,水族、京族、仡佬族迁入。
这样就形成了广西多民族聚居的格局。[1]
广西的原住民族——壮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为同源民族,或叫同根生的民族。按照语言谱系,他们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因此习惯上我们又称之为壮侗语民族。
在整个华南地区,与壮族同源的还有布依族、黎族、傣族,其中黎族、傣族是从珠江流域迁出去的。
整个华南珠江流域的民族构成,与广西相同,此仅以广西为例。
二、关于岭南文化的起源
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岭南历史地理研究的曾昭旋教授说:“地理环境不同也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在古代我国基本上可以划成三个民俗文化带。一是北面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带,它向西可连入青藏高原牧区,和国外的中亚草原游牧文化带连接。二是中原农业民俗文化带,本带西连藏南农业区,人们常说的巴蜀四川盆地文化区、齐鲁山东半岛文化区、荆楚两湖盆地文化区、关中平原秦陇文化区、三晋黄土地带文化区、长江三角洲的吴越文化区等,即在其中,东连日本、朝鲜。三是五岭以南的热带亲海越族民俗文化带。这一带西延是人类起源地的南亚区内云南省高原。……珠江水系即由云南高原流来岭南地区,故岭南文化渊源古远,南连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2]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文明类型。地理环境不同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华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这里的原住民族共同创造了这里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即稻作文化,使这里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包括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黎族的居住区虽然现在不在珠江流域,但黎族与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有密切的关系,是从它发展而来的,其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陆续迁入海南岛,最初居住在沿海和全岛各地,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生活。后来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羁縻征剿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军队的屠杀,大部分黎族人民被迫退居五指山及周围地区。其他民族,包括汉、瑶、苗、回、彝、京、仡佬等是秦汉以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方向逐步迁入这一地区的。
珠江流域即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它的西北部遍布着与云贵高原连为一体的崇山峻岭,北部有五岭山脉横亘,中部的两广丘陵和众多的弧形山脉时断时续绵延其间,山岭之间河流纵横,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左江、右江、柳江、漓江、桂江、西江并与北江相汇聚,形成珠江水系。珠江水系流域面积45.37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境内为44.2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6%(另有少量流域面积在越南境内)。珠江流域在我国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以及香港、澳门8省区 (含特别行政区)。
珠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春季多雨,雨热同季,有利于动植物的滋生繁殖以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从而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珠江流域是我国出土古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初步统计,我国华南已经发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和地点8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西江水系流域,所以西江是人类早期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1973年以来在田阳县百峰乡百峰村的赖奎屯、百色市四塘镇那炼村小梅屯、那柴乡大湾村百谷屯等地发现距今80.3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所出土的手斧等大型石器世界著名。到目前为止,广西发现并确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遗址有13处。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和1956年在来宾县麒麟山发现的“麒麟山人”化石,分别是距今5万年和距今2万—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1960年在邕江外缘发现“灵山人”;1961年在漓江发现“荔浦人”;1972年在柳州市郊发现“都乐人”,其后又在附近发现“九头山人”、“白莲洞人”、“甘前人”;1979年在右江发现“定模洞人”;1977年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发现“九楞山人”;1979年在桂林发现“宝积岩人”等。这些原始人类都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特别是柳江人的发现,是我国南方古人类的重大发现,为迄今我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新人的代表。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省境内,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坝人”遗址。在北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2.9万年。
距今1万年前后,珠江流域同其他大江大河流域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文化遗存,像天上的繁星,遍布珠江流域,据统计,在云南有300多处,广西有900多处,广东有500多处,在贵州境内也有不少,全流域大约有2000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独具特色,并基本形成了系统,构成了珠江流域独特风格的史前文化。
在广西境内,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这些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上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人类的特点,表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邕宁县顶蛳山遗址进行发掘,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将该遗址第二、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址命名为“顶蛳山文化”,时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七、八千年。这些遗址出土了大批石斧、石锛、石凿、石锤、石网坠等石器,蚌刀、骨锛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同时,在隆安、扶绥、南宁市郊等地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大石铲遗址。另外,还发现大批铜鼓、铜钺、铜钟、铜剑等青铜器和斧、锄、刀、剑、戈、矛、镞、铲、刮等铁制工具,是2000—3000年前的文化遗物,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将广西现代壮族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甑皮岩人、昙石山人、河宕人进行比较,指出甑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额宽、垂直颅面指数、面角、眶指数、鼻指数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属中眶型、阔鼻型,这意味着现代壮族很可能有甑皮岩人血统。壮族在头长、头长高指数、头宽高指数、颧宽、上面高、鼻根指数等项更接近于较甑皮岩人晚的河宕人,体现了这种渊源关系。而自甑皮岩人往前追溯,甑皮岩人在接近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阔鼻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突颌型的齿槽面角等方面,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恰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继承关系表明了生活在广西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另外,李富强、朱芳武在对柳江人等古人类骨骼及现代壮族活体测量获得大量数据并进行分析比较后也指出:“现代壮族在其体质形成过程中,与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某些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
另外,在甑皮岩洞穴遗址和其他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侗语民族至今仍沿用的捡骨葬 (二次葬)基本相同,其他许多生活习俗也与壮侗语民族相同、相近,这些都说明今天的壮侗语民族与这些古人类的承袭关系。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这些古人类 (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
总之,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资料表明,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再到青铜时代,地方特点、民族特点突出,而且前后相因,脉络清楚,一脉相承。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其他地区是十分少见的。
另外,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历史学考察,居住在华南珠江流域的壮侗语民族及其先民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近现代,都没有发生过整体性的迁移,至少是他们中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都生活在这一区域。壮侗语民族是稻作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和旱作民族不同的是,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守土性强,不轻易背井离乡的品格。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说的:“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粘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文化创造,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且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岭南文化的起源,曾昭旋先生指出:“总结上述,可知岭南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是自成一中心,有光辉的历史,起于当地,源远流长,与黄河、长江流域各文化中心相比,互有长短。本人在题赠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贺辞说:‘炎黄文化,从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即是此意。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促进了我国逐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有朋友称我们是‘文化的地理学派’,本人是承认的”。[3]
曾昭旋先生认为,因当时的越人分布于长江和中原,交通频繁,汉代“越人歌”今天还可用壮语译出,[4]即说明越族古代是有大致相近的语言的。岭南地区曾属吴,广州建有南武城,越灭吴,曾修南武城进行外贸。楚灭越,岭南才入楚,建有楚亭,并因岭南有犀角、象牙、明珠等宝货引起秦始皇的入侵。苦战三年,伏尸流血数十万,主将尉屠睢被杀。使秦始皇终生“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反映蒙古游牧民族和南方丛林的越族,均与中原为敌的事实。“秦亡后,赵陀和辑百越,王93年,这是汉、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使岭南文化来一次飞跃发展,也是越文化汉化的开始,今天的岭南文化,即以此汉化的南越文化为基底”。[5]曾昭旋先生认为,南越文化还表现在语言方面,即虽经过2000年的汉化,但语法和词汇在广州、潮汕、海南方言仍有南越特征 (如倒装语法、地名等)的残留。在边远地区,古代越族的椎髻、穿裙等风俗仍有保留,如吕田本地汉人每被误认为“少数民族”。[6]曾昭旋先生说,汉代杨雄《方言》中屡提及“南楚之南”的方言,表示已是和楚方言不同的语言了。“南楚之南”指的就是岭南越人地区。“今天称为台语,或称为‘壮侗语族’。即广州白话、壮话、傣话同一语源,今天广州话数目字如一、二、三、四……仍和云南傣语相同,即为一例。如南楚称美为‘娃’(见《说文》),白话即为‘威’(今称‘威水’);《方言》称:‘南楚谓目丐曰睇’,‘睇’亦白话;又称:‘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僖 (上吉下室),音“pok”,即广州话“博”(今称农民为“博佬”);又称“抱” (加草字头),“南楚人谓鸡抱”,今白话称“抱鸡仔”;“搴”,《说文》称:“拔取也,南楚语”,今广州话仍称“揭”;“振”(加竹字头),《方言》:“南楚谓之肖(加竹字头)”。从文法上,古越语亦与汉语不同。“番禺”按越语为“村咸”译成汉语为“咸村”。即多用倒装语法。如汉语称“人客”、“公鸡”、“干菜”,在广州语反过来称:“客人”、“鸡公”、“菜干”等等。广州话和壮话相似,口岩 (合适)、口旧 (即一块)、歪 (即不正)、口历 (能干)、郁 (移动)、谂 (即想)、子尽 (最后)都通壮语。
三、壮族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从人口的变化看壮族经济
秦汉以前自主发展阶段——秦汉以后在国家的统一治理下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阶段。
关于人口。人口较少民族史书上未见记载,一般只记载壮族和汉族的人口情况。
就整个广西来说,清中期以前,壮族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绝大多数。嘉庆七年 (1802年)《临桂县志》卷十二说:“广西之境大约亻良人半之,瑶僮三之,居民二之”。这里僮为同族异称,按此计算,当时壮族人口占广西人口60%以上,汉族人口仅占20%,瑶苗等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20%。但实际上瑶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可能达不到20%,因为明清时期,瑶、壮经常有混称的现象,在很多文献资料中皆把壮当作瑶看待。“如果以为‘瑶’都是指瑶族,‘僮’都是指壮族,‘瑶僮’连称都是指瑶族与壮族,那是不尽妥当的”。[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瑶壮往往混杂而居,使得汉族人士在指称时难以区别;二是由于民族歧视等原因,一些少数民族“每出掠,皆冒称为瑶”,因而在文献上也作为瑶记载;三是汉族对壮族、瑶族和分布在其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了解不够深入,从而难以进行正确识别,而往往把“僮”说成“瑶”的一种,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三九四说:“壮亦其 (按:指瑶)种类也”。至今广西壮族、汉族以外的民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左右,说明当时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占不到广西总人口的20%。由此看来,清中期广西壮族人口在当时广西总人口中的比例更高些,可能达到70%以上。
从上述壮族人口在广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壮族人口的分布情况看,明清时期,至少是明代到清代中期,广西全境均可视为壮族地区,广西经济,大体上可视为以壮族为主的经济。
清代以后,壮族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汉族人口在壮族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到清末民初,已成对半分之势。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个比例又发生变化。据陈正祥《广西地理》记载,1946年汉族“约占 (广西)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六十”。[8]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现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明清以后汉人入桂人数大幅度增加。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说:“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来者,约占十分之八”。明清以前,汉人入桂多为屯戍的兵士、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及被流放者,大多属被动的原因,因而数量相对较少。而明清以后,除上述者外,有大量的汉族人因从事开垦、经商、手工业等自觉入桂,他们不仅来的人数多,而且一旦立足便迅速发展,其人口也迅速增加。二是明清以后,岭南壮族融合于汉族的速度也有加大的趋势。当然,进入广西的汉族有不少融合于壮族,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影响,更多的是壮人融合于汉族,失去了本民族的特征。这仅是民族自然融合的一面,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历代政府强迫民族同化的事屡有发生,其主要手段之一是不让壮人讲壮话和强迫壮人改变民族习俗。
为此,我们在行文过程中,一般把明清以前 (含明清)的广西都称为壮族地区,而明清以后即民国时期,在描述时则尽可能把壮族聚居的县区别开来,一般指今天的百色、河池、南宁、柳州4市所辖的县,如以民国三十三年为例,取横县、永淳、宾阳、迁江、来宾、武宣、象州、柳江、忻城、宜山、柳城、洛容、中渡、百寿、三江、融县、罗城、宜北、天河、思恩、南丹、河池、东兰、都安、平治、那马、隆山、上林、武鸣、邕宁、扶南、绥禄、上思、思乐、崇善、明江、宁明、凭祥、龙津、上金、雷平、左县、同正、养利、万承、隆安、果德、镇结、龙敬、向都、天保、靖西、镇边、敬德、田阳、田东、万岗、百色、凌云、凤山、天峨、乐业、田西、西隆。这些县壮族占有相当的比例。
当然,我们不可能追求一个纯粹的民族经济,因为在当今世界,都不可能存在纯粹的一个民族独立生活在一个区域而没有受其他民族的任何影响,壮族也不例外。我们所说的壮族经济只是相对而言。
壮族是我国华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壮族居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壮族的经济文化特点。壮族是把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创造了稻作农业的民族之一,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壮族是稻作民族,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经济孕育了壮族早期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物质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等特征。
壮族经济发展经历了氏族部落时期的原始农业;西瓯骆越时期 (先秦至秦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俚僚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集市的形成;僮土时期 (宋元至民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矿冶业、交通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五个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冲击,使壮族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西部大开发为壮族经济的加快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壮族经济的这种纵向历时性发展变化,直接地影响着壮族的族体形态过程,其中包括由血缘民族向地缘民族转化及族体规模、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变化。
当壮族处在氏族部落时代,是她独自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地区纳入了祖国统一的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止,壮族由独立发展时代转入了统一的中央封建王朝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中生存和发展的时代。民族政治过程的这种转折和变化,对壮族的经济过程和族体形态过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壮族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秦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汉族移居岭南“与越杂处”,开始了壮汉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西瓯骆越人移居东南亚地区,他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泰国的泰、老挝的老、缅甸的掸、越南的岱、侬等民族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留在我国疆域上的西瓯骆越人则发展成为今天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其中壮族是人口最多的一支。壮族族体形态的这种巨大变化,基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而族体形态的变化又对壮族的经济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氏族部落时期,壮族处在潜民族状态;从先秦至隋唐时期,壮族处在自在民族状态。宋代,由于北方战乱,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岭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大批中原汉族继续移居岭南,瑶、苗、回等民族也陆续进入岭南。随着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增强了壮族“相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壮族自称“僮”的出现,标明壮族由自在民族进入了自觉民族状态。
壮族是稻作农耕民族,这是由她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壮族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同时又要使壮族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其发展。
[1]覃乃昌.广西世居民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2]曾昭施.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89.
[3]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璇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1.
[4]“越人歌”见刘向《说苑·善说》篇,记下春秋楚鄂君子不懂榜木世越人唱的一首歌。
[5]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2.
[6]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4.
[7]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179.
[8]陈正祥.广西地理[M].正中书局,1946.
The Origin of Lingnan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Zhuang——A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 on the Research of Zhuang Economic History
Qin Naichang
Natural environment determines the type of civilization.Natural environment of Lingnan region determined that its civilization was the civilization of rice cultivating.Indigenous people——ancestors of the Zhuang and Dong language family ethnics adapted Lingna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created a rice agriculture,ha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human.In short,Lingnan early culture was created by aboriginal settlers.After Emperor Qin Shihuang unified the Lingnan area,Zhuang was manag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tarted to settle with the Han and other minorities together.But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the population of Zhuang wa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in the Lingnan region.Therefore,we still regard the Lingnan region as Zhuang region in the period.From the middle of the Q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Han population increased,we started to regard a part of the Lingnan area Zhuang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s the Zhuang region,and as a basi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Zhuang economy.A pure Zhuang economy does not exist.
Lingnan culture;origin;civilization of rice cultivating
【作 者】覃乃昌,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宁,530028
C95-05
A
1004-454X(2010)03-0074-006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