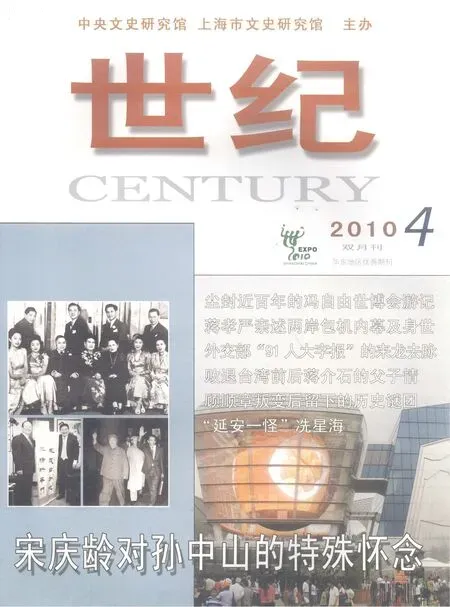吴永刚导演为何成为右派
2010-12-26萧镇
萧 镇
不久前看到《新民晚报》上刊载了周炳揆先生的文章《借书与回忆》,文中所述的吴茵和孟君谋影坛伉俪在反右和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孟君谋先生在后期遭遇,读来使人唏嘘和愤慨。由此引发出我的一些相关回忆,因为在文革中我曾从上影老导演吴永刚处得知了吴导本人和吴茵大姐之所以被划为右派而陷入灾难困境的确切原因。
吴永刚导演和我有过拍片的合作,同时我们又都是金焰先生的故友,所以就有了日后的交往。吴导看上去一直比较严肃,而且从不喜欢和人无事闲聊,交往中也从未从他的口中听到过丁点的牢骚和不满。在文革后期,他已“捱”过了被批斗的高潮,又可以自己适当的“自由”走动。于是,每天他都会外出步行两小时作为一项室外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是当时他的住房尚未解决,外出可以暂离那狭小、令人有些窒息的生活空间;二来可以藉此锻炼、恢复体力以舒缓疲惫而又憔悴不堪的身心并消磨些难耐的时光。那时,他离开家门后每当先步行至复兴西路金焰先生的家,然后又继续行进到我当时的住所华亭路时,都会将其作为一个临时歇脚点,进门小憩一番。那时我爱人还在干校,家中就我一个人。吴导每次进门坐定后,都会默默地手握着那个常年伴随着他的板烟斗,在烟雾氤氲中从不过多言辞,更不会谈论政事或发半点牢骚。一天,我突发奇问:“吴导,像您这样从无半点牢骚的人怎么也会像我一样被戴上右派大帽的?我是因为骂了一句当时所谓的苏联专家是‘瘪三’,就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毛主席,尽管1957年我还常年在外拍戏,从未参加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任何活动,但也在反右近尾声时,被硬性划为右派而就地改造。”听罢我的话,经过片刻沉寂后,吴导终于开口了:我和吴茵在反右前曾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上号召我们要在这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的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拆掉党群之间的那堵墙,回到上海后要起到带头作用,以不负党的重托。但回到上海后,因为我和吴茵平时就不喜欢多讲什么,所以在上影厂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们也从未发表过任何言论。后来,有关领导就做我们的工作,并再三言明这次整风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最后我们据此才对个别现象和个别人做了点拨、启迪性的发言。哪知到了整风后期,我们却因此被无端说成是是非不分,不但自己反党而且还动员别人反党。如此一来,我们就被顺理成章的定性为货真价实的右派,戴上了这顶帽子。
戴帽后的吴导被降五级,下放到上影美工科做一名资料员。吴茵被迫离开了心爱的银幕,此后长期瘫痪患病在床,直到1962年才在众多昔日老友的关爱下,给了她一次重上银幕的机会。记得那次是动用了众多的人力才将她抬到拍摄现场、在终于完成了没有一句台词才两个镜头的这最后一次拍摄后,她就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银幕形象,直到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