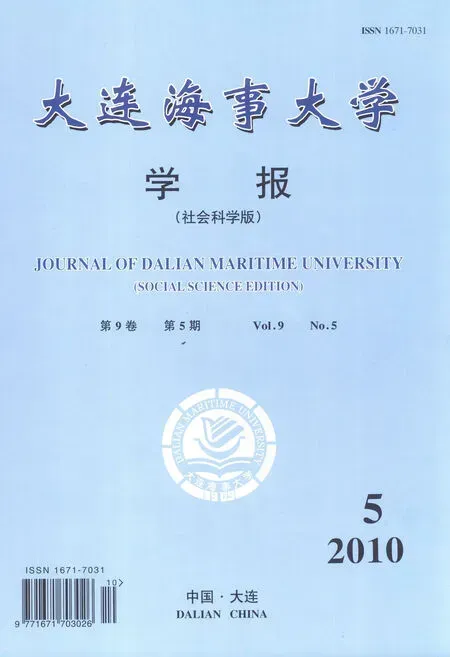社会资本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
2010-12-04于颖
于 颖
(东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社会资本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
于 颖
(东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社会资本虽然是近年来才形成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但其思想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中却源远流长。这些思想对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
社会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新的、影响广泛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但在中国,一般人比较容易将其理解为垄断领域之外的物质资本或马克思所研究的单个物质资本总和的社会总资本,也就是说,人们是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资本这一词语的。因此,追溯这一目前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比较流行的概念的思想渊源,可能会对正确理解其内涵有所助益。
早在1762年,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就论证了共同价值和社会契约的重要性,而托克维尔则注意到社群对于社会繁荣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回顾稍近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一、人类学来源
从源头上看,较早开展社会资本研究的当数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对于初民社会的经济社会活动、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的一些基本内涵。
1.布朗对于社会网的研究
作为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布郎(A. R. Brown,1881—1955)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研究南非初民社会中母舅之间的亲属关系,提示了南非人的社会结构。并率先使用社会网(network)这个概念,其含义是人与人交往中相对稳定的联系。
布朗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们“根据自身的生活方式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由此形成社会网络,进而形成了社会结构”[1]。第二,布朗认为,原始南非人当中,外甥对舅舅的称呼、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说明原始南非人之间的社会行动主要在亲属关系网络基础上加以规范。第三,布朗认为,个体之间所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是由文化、习俗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支配的,文化与习俗形成了某种社会规范系统,并对这种规范系统进行制约,使之符合于某种特定群体的需要。反过来,社会规范系统一旦形成以后也会作用于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而使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变动性特征。
布朗对于南非人亲属关系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早已存在于早期的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并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
2.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也非常重视社会关系的研究,他的社会关系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名的“库拉”交换的研究中。
第一,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田野调查认为,作为一种高等动物的人应当具有两个需要,一个是基本的需要,如吃喝繁衍、安全、健康等;同时,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类应当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建构适合自身生存的物质生活环境,这就是派生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两种需要,人就要建立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所以,社会关系是形成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
第二,马林诺夫斯基在其1922年发表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揭示了那里的居民的生产活动有一部分具有伦理价值色彩和社会关系交往色彩。例如卓布兰岛民并不纯粹把食物当做营养来源,“他们储存食物的目的不仅是准备他日之用,而且在于炫耀。他们建造的甘薯仓库,不仅可以炫耀食物的数量,也可以让人通过横梁的大缝隙看到食品的品质。他们堆甘薯时把最好的露在外面,特别粗壮的甘薯可达一二米长、数公斤重,用盒子装起来,漆上颜色,吊在仓库外面供人参观”[1]。
第三,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重点研究了存在于特洛布里恩德岛的土著居民中的“库拉”交换。他认为,从形式上来看,“库拉”是新几内亚特洛布里恩德岛马辛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性质的交换形式”[1]。“库拉”主要是围绕着红贝壳项圈(soulava)和白贝壳臂镯(mwali)的交换。这两种手工制品本身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在作为库拉交换的对象时才具有核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库拉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社会联系的加强方面;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还发现,库拉交换不是发生在任意的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固定的库拉伙伴之间,而一旦成为库拉伙伴,往往终身都是库拉交换的伙伴。库拉交换遵循着互惠原则,主要体现在送礼与回礼之间,而绝不是一般的物物交换,也就是说,库拉交换不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单纯的物物交换,而是一种关系交换、网络联结,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声望、展示人际关系的网络交换。
3.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库拉”交换促进了人们对主流经济学中单纯的利益最大化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反思,那么,法国人马塞尔·毛斯(M. Maus)写于1925的《礼物》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古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
毛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维系市场存在的力量主要是正式的契约以及法律制度,契约和法律以正式的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有强制性和正式性的特点;而古代社会尽管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市场,但维系市场交换的基础却主要是非正式的道德和习俗。并且,毛斯认为,古代社会中市场的力量或作用也是有条件的。首先,古代社会中交换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各个个体,而是“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呈现在契约中的人是道德的人,即氏族、部落或家庭”[1]。其次,他们所交换的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有用的物资和财富,有用性不是他们交换的根本目的。再次,尽管这种礼物的赠与回馈是一种严格的义务,甚至极易引发冲突,但是它却通过礼物的流动完成这个体系。也就是说,礼物之间的流动是一种义务性送礼、义务性受礼以及义务性回礼。毛斯将这种义务性而非商业性的、发生在古代社会毛利人部落中的礼物流动制度称为“总体呈现体系”。这就是说,“礼物已经成为互惠体系的一部分,而在这个体系中赠与者和接受者的荣誉和精神都得以充分地展现”[1]。毛斯认为,毛利人的“总体呈现体系”根本原因就是试图建立某种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可以发现,礼物的流动是形成毛利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和重要纽带,通过礼物的流动,使得毛斯笔下的初民社会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使得这样的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稳固的社会结构。
在人类学发展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卡尔·波兰尼,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帝国早期的贸易与市场》中指出,在早期的帝国社会,即在初民社会中,个人相对于集体而言仅仅是次要的因素,人们的经济活动往往是社会、文化及习俗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早期社会或者在整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是被嵌入于社会中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生活中的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意味着由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礼物馈赠等建立起来的人类行动中也蕴涵着经济功能。波兰尼说:“只是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中间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才有了经济……为了每一个人的自然生存,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财务与服务周而复始的供给。这乃是美国、苏联、特洛布里恩德岛都各有其经济的一个首要原因。”[1]在《帝国早期的贸易与市场》中,波兰尼还表述了“嵌入性”的思想。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嵌入在受价值支配而非受利润支配的社会关系之中,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嵌入性”将越来越弱,甚至消失。
二、经济学来源
经济学历来以其抽象、严格的“经济人”假设而著称,但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不乏将有关社会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中的现象。
1.亚当·斯密的双重贡献
提到亚当·斯密,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他在《国富论》中所传递出的“经济人假设”思想,然而多数人不了解,斯密早先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在出版《国富论》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这里,他论证了偏好在个体间的相互依赖性:“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有某些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虽然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时所感到的快乐外,他别的一无所获。”他还指出:“我们与相互共处和经常交往的那些人之间求得一致的意向……是对好朋友和坏朋友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的原因。”[2]这说明了个体间的社会联系对于人类欲望的满足以及人们行为的影响。同时,斯密还注意到这种依赖性取决于人们之间关系的强度:“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灵敏……而他自己的家庭的成员,那些通常和他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人,他的父母、他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自然是他那最热烈的感情所关心的仅次于他自己的对象。”而“表(堂)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因为更少联系,彼此的同情更不重要;随着亲属关系的逐渐疏远,感情也就逐渐淡薄”[3]。在这些论述中,甚至可以找到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弱关系或者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影子。但是,斯密并没有将社会因素与经济行为联系起来,而只是将个体行为置于社会结构中予以一般性的分析。比如他举例说道:“一个主要与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交往的人,虽然他自己既不(一定)会成为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有美德的人,但不能不对智慧或美德至少怀有一定的敬意,而主要同荒淫和放荡之徒打交道的人,虽然他自己不(一定)会成为荒淫和放荡的人,但至少必然很快会失去他原有的对荒淫和放荡行为的一切憎恶。”[3]并且,斯密也没有将自己的这些洞见融入他对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去,人们通常认为,正是斯密本人在其后来的鸿篇巨制《国富论》中奠定了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基石。
2.贝克尔的开创性研究
从社会资本的经济学理论渊源的发展历程来看,贝克尔无疑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他的开创性研究才使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得以重新对话、交流和融合。
人们通常将贝克尔看做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轫者,即将经济学研究方法侵略性应用到诸多社会问题分析的拓荒者,殊不知,贝克尔也是将社会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先驱者。他在对个体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中说道:“更一般的分析假定,效用函数中的每一项都要是(社会)环境因素和后天(个体)因素的结合体。”而同时“即使个体特性本身具有‘低的’收入弹性,但是对其他个体的特性的贡献却可能具有‘高的’收入弹性”[3]。这表明,贝克尔不仅仅认识到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分析包括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婚姻家庭与生育、犯罪、歧视等所有的“人类行为”,而且经济学的分析也应该融入社会因素。就个体收入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会收入”,个体的自身收入(个体的报酬)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有关特征(即“社会环境”)。所以,要对个体行为进行准确的分析,就必须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效用函数进行修正。由此,贝克尔在个体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了“社会环境”变量,以代表“会对该个体的商品产出产生影响的其他个体的个性”[3]。尽管贝克尔并没有准确地考虑“不同其他个体”对“该个体”商品产出的差异性影响,但这一修正无疑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主义效用函数的“社会因素”缺陷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贝克尔之后,主流经济学中有关社会因素的专门研究又沉寂了多年。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首次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以此来分析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
三、社会学方面的理论渊源
从社会学方面来看,社会资本的起源主要有4个方面。
一是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的“价值融合”观点。他们认为,道德价值观念往往先于契约以及个人目标而存在,道德价值观念起到影响及规范个人社会行动的功能,通过道德价值规范,就可以把相关的个人整合起来,组成一个群体或集体,进而可以整合为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实现社会目标。因此,群体联系可以有效防范混乱、自我崩溃等社会失范行为。
二是齐美尔的“互惠交易”思想。在《群体关系的网络》中齐美尔第一次使用了“网络”一词进行社会学研究,并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进行互惠交易的社会关系整体。在他看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来源于个人之间的交换,个人之间平等的相互交换必然会产生某种互惠交易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制约个人活动的客观存在,从而也就形成了社会关系网络。而霍曼斯和布劳则进一步分析了互惠的根源和动力机制。
三是马克思的“有限度的团结”的思想,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群体团结一致的动力,能够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的关系网络,或者为了实现其目标而把自身的资源让渡给他人,从而使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群体建立了某种社会关系网络。
四是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存在的那种正式的科层制度具有强制性作用,它能够把社会上的各个个体结合在一起,组成正式的社会网络结构,实现社会目标。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当欧洲的社会学家们在试图构建社会结构理论体系、努力从理论上解释形成社会结构的原因时,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们则试图展开小群体关系中整个社会关系的功能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成果就是“霍桑实验”。
20世纪20年代,位于美国芝加哥城郊外的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是一家制造电话机的专用工厂,其设备完善,福利优越,具有良好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但是工人仍然愤愤不平,生产效率也很不理想。为此,1924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包括各方面专家在内的研究小组,对该厂的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考察和实验,就此拉开了著名的霍桑实验的序幕。霍桑实验是指1924年至1936年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所属霍桑工厂进行的一连串实验,其结果表明:
第一,产量与生产条件(实验时为车间照明的强弱)及工资待遇、福利等没有必然的联系。以往人们总是以为产量与生产条件(车间照明强弱)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车间照明条件好一般会导致产量的增加。可是实验结果表明,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研究人员还从工作报酬(集体工资和个人计件工资)、休息时间、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长短等方面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些条件的变化与生产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相反,因为在实验时管理人员对工人态度较和蔼,工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工人能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工作,却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调动积极性、提高产量方面,人际关系是比福利措施更重要的因素。
第二,访谈实验表明,工作绩效与在组织中的身份和地位、人际关系有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梅奥等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态度调查,在职工中谈话人数达两万人次以上,结果在这次大规模的访问中,搜集了有关工人态度的大量资料。经过研究分析,了解到工人的工作绩效与他们在组织中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与其他同事的关系有密切联系。
第三,观察研究表明,“非正式群体”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霍桑实验的最后一项实验是观察研究,即继电器绕线组观察室实验。这项实验又称为群体实验。实验开始,研究者向工人说明:他们可以尽量卖力工作,报酬实行个人计件工资制。研究者原以为,这套奖励办法会使职工努力工作。但是结果出人所料,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工人绝不愿因超额而成为“快手”或因完不成定额而成为“慢手”。当达到定额产量时,他们就自动地松懈下来,因而小组的产量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原因何在?研究小组经过考察发现,组内存在一种默契,由此形成制约着每个人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的压力。当有人超过定额产量时,旁人就给他暗示:谁要是有意超过定额,便会受到冷遇、讽刺和打击,小组的压力就会指向他。那么工人为什么要自限产量?进一步调查发现,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了,管理部门会提高定额标准,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这一实验表明,工人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抵御物质利益的引诱。梅奥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
霍桑实验的重大贡献在于,它不同意泰勒把人只看成“会说话的机器”或人的活动只是受金钱的驱使,霍桑实验认为人是“社会人”。霍桑实验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它发现并证实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这种“非正式组织”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感情倾向,控制着每个成员的行为,甚至影响整个正式组织的活动。霍桑实验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经梅奥归纳、总结、整理,于1933年正式发表,即《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人际关系学说理论。
四、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
社会资本的概念早已有之,只是人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去使用它罢了。比如,在当今中国,人们也用社会资本指代那些垄断领域之外的资本,当你打开互联网,输入“社会资本”字样时,会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条目:“铁道部鼓励境内外社会资本投资中国铁路”“卫生部承诺打破公立医院垄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等。较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还有马克思,但他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那些独立执行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显然,这些都与所要研究的社会资本的内涵大相径庭。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一文和1920年发表的《社群的中心》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那些占据人们大部分日常生活的可感受的资产,即良好的愿望、友谊、同情,以及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个体和家庭间的社会交往。”[3]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粗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雅各布斯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3]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20世纪80年代,在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等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之下,社会资本才开始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广为研究、利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4]。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主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5]。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明的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同时,他还指出:“社会资本一般包括联系、惯例和信任,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转移。”[6]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困境的基础。
[1]高和荣.西方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2-190.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3]朱国宏.经济社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3-104.
[4]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5]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354.
[6]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9.
[7]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周小虎.企业社会资本与战略管理——基于网络结构观点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林 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 猛,李 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Mentaloriginandformationofconceptionofsocialcapital
YU 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Dongbei Univ.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Though social capital is a new and significant conception and research field that is formed in recent years, its ideas have been existing in fields such as sociolog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since long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social capital is under great influence of these ideas.
social capital; sociology; economics; anthropology
1671-7041(2010)05-0001-05
F091
A*
2010-06-23
于 颖(1964-),女,辽宁凤城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