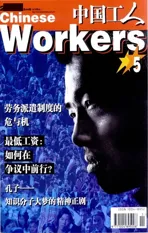跨越民族的母爱(二)
2010-11-22郝敬堂
郝敬堂
跨越民族的母爱(二)
郝敬堂
阿尼帕的小妹哈丽恰木评价说,姐夫阿比包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我们父母去世后,他收养了我们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毫无怨言,任劳任怨,没有打过人,没有骂过人,连句牢骚话也没有说过。虽然日子过得清苦,可全家人和和睦睦,虽苦也甜。
在阿尼帕的记忆里,他们两口子也翻过一次脸,而且是仅有的一次。
一次,供销社派阿比包到乌鲁木齐去卖羊,羊是集体财产,说起来算是出“公差”。那趟“公差”是趟“苦差”。从青河到乌鲁木齐,上千公里路程,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也不知道途中要翻多少山越多少岭蹚多少河,路上要走多少天有多少困难他没想过,只想着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做到“羊不能少,膘不能掉”。临出发前,细心的阿尼帕给丈夫收拾了一个大背囊,里面放了两套换洗衣服,两双布鞋和一块毛毯,又塞了几个锅盖大的烤馕。阿比包当过兵,行过军,打过仗,他知道长途行军最怕的是肩上的背囊,不管你多苦多累,那个死乞白赖的家伙始终趴在你的背上,没有缘由地折磨你,直到你彻底地抛弃它。这次出远门和当年行军不一样,行军有向导,有驿站,有宿营地,能提供休息,能补充供给,如今自己是单枪匹马走天涯,白天烈日晒,晚上秋风凉,吃不上,喝不上,身上再背着个大“包袱”,岂不成了累赘?阿比包谢绝了妻子的好意,只带上几块馕就匆匆上路了。阿尼帕想想也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吃的用的东西少带点,但钱要多带点,于是从抽屉里取出100块钱塞进他的行囊里。阿比包知道自己的家底,又给妻子留下了一半。
丈夫一去就是半年,回来后,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野人”,头发没理,胡须没剃,人也瘦了一圈。
“半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阿尼帕惊诧地问。
“别提了,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阿比包自我解嘲地回答。
“你一走就是大半年,连个音信也没有,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你一个人在外面倒是自在,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阿尼帕的话里带着责难。
“我一个人在外面自在?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吃苦受罪为了谁?”阿比包也来了气,反唇相讥。
“为了我?为了我们兄妹?是我们兄妹拖累了你……”阿尼帕的火气越来越大,这个敏感的话题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平心而论,在这样一个家家自顾不暇的灾荒年里,家里骤然多了6张嘴,而且个个都是只能吃不能干,没有博大的爱心,能作出收养的决定吗?对于阿比包的爱心情怀,阿尼帕心存感激。
“你不要再说了,再说……”阿比包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盛怒之下举起一根烧火棍。
“你想打人?来,我让你打……”阿尼帕边吵边迎面向阿比包扑来。
阿比包见势不妙,急忙放下手中的烧火棍,本想上前拦住情感失控的妻子,手忙脚乱的他却迟了一步。
嗵的一声闷响,阿尼帕一头撞在门框上。接下来出现的一幕是血色恐怖:殷红的血从她眼角处流了下来。
看到家里出现“流血事件”,看到姐姐满脸是血,兄妹们一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多久,“工宣队”来了,手臂上戴着红色袖标,上面赫然写着: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在当年,“工宣队”掌控政权和司法权。后来得知,是弟弟报的“官”。
本来是家庭矛盾,一经报“官”,性质就变得严重了。
“打人致伤,违反社会治安处罚条例,带走!”不由分说,阿比包被“工宣队”带走了。
看到这不该发生的一幕,阿尼帕深感内疚,他知道丈夫没有错,她头上的伤是自己撞出来的。
现在说起这段往事,多少有点滑稽。可那艰难岁月留下的记忆,总带有几分酸楚。
在7兄妹中,只有阿尼帕没有上过学。她是长女,从5岁那年就帮助妈妈照看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去世那一年,有4个弟弟妹妹在上学,爸爸妈妈不在了,他们还能继续上学吗?不上学,他们将来怎么成家立业?
阿尼帕虽然没有文化,可她不愿意看到弟弟妹妹们失学。当时家里穷,缺衣少食,兄妹几个穿一条裤子。因为没有衣服穿,上午是老大老二去上学,下午是老三老四去上学,缺的课回到家里来相互补。尽管学习条件如此艰苦,6兄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让姐姐感到由衷地欣慰。
现如今,当年由姐姐一手拉扯大的6兄妹没有一个是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有的读完初中,有了读了高中,有的读了中专,还有一个读了大学。完成学业后,他们全部找到了工作,有两个当老师,两个在医院工作,一个在地区歌舞团工作,最小的弟弟在县粮食局当司机。
岁月从苦难中走过,一年又一年,阿尼帕的家庭成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抚养6兄妹之后,阿尼帕接连生了9个孩子,又领养了10个孤儿。在阿尼帕家人口最多的时候,27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一口井里淘水。在这个家里,学生最多的时候不少于一个“班”。每天早上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学校,阵容浩浩荡荡,口里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学了,又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家,回家后各有分工,有的上山捡柴,有的择菜做饭,有的带孩子,有的拔草喂牛……孩子们都很懂事,很少让大人操心,由于孩子多,团结好,在外面很少受人欺负。
孩子们一拨一拨长大了,又一个个成家了,一个大家庭裂变成许多个小家庭,阿尼帕含辛茹苦,不就是为了看到这一天吗?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孩子们虽然离开了她的身边,可她依然牵挂着他们,她跟当地的汉族人学会织毛衣,做布鞋,送给孩子们的孩子。
大妹妹生了孩子后工作忙,把顾不上照顾的孩子推给了姐姐,阿尼帕毫无怨言,只要他们生活得好,她宁愿作出这种奉献和牺牲。在6兄妹的孩子中,有4个是吃阿尼帕的奶长大的。
小妹妹吾拉孜汗在伊犁上学,她每月给她寄去20元生活费,直到她毕业。学校里填写新生入学登记表,吾拉孜汗在家长一栏里填的阿比包和阿尼帕。这个“家长”的名分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刻在心上的,在她的心目中,姐姐和姐夫就是她们的再生父母。
家里人口多,常常是顾了吃的,顾不上穿的。那年冬天,阿尼帕发现她的第5个孩子走路腿脚不利落,就把他叫到身边,脱掉他脚上的那双毡靴才发现,他的脚上没穿袜子,鞋底也已经磨穿,两只脚冻肿了,肿得像烤面包,可他从来没吭过一声。这是母亲的失职啊!阿尼帕解开衣襟,心疼地把孩子冻伤的双脚塞进怀里,用母爱去温暖那个幼小的受伤的心灵。
供销社的会计刘世惠从内地探亲回来,买了一双红皮鞋送给阿尼帕,阿尼帕却把这双鞋给了小妹妹吾拉孜汗。吾拉孜汗欣喜若狂,那双鞋她舍不得穿在脚上,更多的是背在肩上,上学的路上赤脚走,到了学校才穿上……这童年苦涩的记忆一直保存在心灵的硬盘里。
家里人口多,阿尼帕实在是照顾不过来,可她心里始终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宁肯亏待了自己的孩子,也不亏待她领养的孩子。
吾拉孜汗回忆说:爸爸妈妈去世后,姐姐、姐夫对我们兄妹特别好,照顾我们比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还周到。多年后才发现,大家一起走过苦难,他们亲生的孩子身体大多有疾患,有两个已经不在人世,可他们养育的我们,不但身体好,而且都过上了好日子。这养育之恩终生难忘!
阿尼帕最小的儿子阿布都回忆说:我虽然是妈妈最小的儿子,可妈妈很少有时间照顾我,照顾我最多的是姐姐阿依古丽,她是妈妈的养女,汉语名字叫王淑花。王淑花姐姐白天陪我玩,晚上拍我睡,我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姐姐唱的睡眠曲,只有一句歌词:阿布都,不要哭!阿布都,不要哭……夜夜重复,年年重复,说不清重复了千遍还是万遍,最后姐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每天都要唱着这支歌才能睡去,一直到她后来结婚,还是那样唱着睡,起初姐夫误会了,以为她得了精神病。
在阿布都眼里,他们的家是一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兄弟姐妹特别多,相处得也不错。虽然日子过得苦了些,可依然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奉献最多的是阿尼帕妈妈,她用爱心创造了一个奇迹,她用勤劳创造了一番伟业,她用智慧破解了一个“1+1=19”的爱心方程。
66个民族一个家,1919个孩子一个妈
1963年春天,大青河刚刚解冻,绿草刚刚吐绿,草原的春天已经是蓬蓬勃勃了。牧民们经过大半年的休牧,把牛羊赶上了山,他们祈求山神保佑,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人畜平安。
哈萨克族邻居牙和甫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圈里的牛羊没人放养,灶台的烟囱断了炊烟,小院里传来阵阵哭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人心寒。这里正在举行穆斯林葬礼。一年之内父母双亡,巨大的不幸留给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叫吐尔达洪,老二叫托乎提,老三叫胡尔曼。老大16岁,老三只有6岁。
牙和甫夫妇去世的噩耗,打破了阿尼帕家庭生活的平静。参加完葬礼回来,阿尼帕仿佛从3个可怜的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命运是何等相似啊,吐尔达洪兄弟的今天正是自己的昨天。
共同的遭遇产生出情感的共鸣。起初,阿尼帕经常给3个可怜的孩子送吃的,送喝的,帮他们洗衣服、缝衣服,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建立了感情,于是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3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接到家里来住,这是件大事,必须征求丈夫阿比包的意见。
阿尼帕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一向做事果断的丈夫迟迟没有表态。阿比包当年也是孤儿,能理解吐尔达洪兄弟的处境,从道义上和感情上都能接纳他们。可接纳并不仅仅是融入,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份责任。自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家庭负担也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全国都在度荒年,家家都在愁吃饭,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家里再多3张嘴可怎么糊口?
慈为地,善为本。阿比包知道妻子是一个慈善之人,可她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生存之道:人法地,地法天。民以食为天啊!没有粮食人就会被饿死,这是最简单的生存法则,也是最现实的人生哲学。身边饿死的人还少吗?道听途说的不论,亲眼看到的也不少啊!
“你倒是说话啊,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这3个没爹没妈的孩子饿死吧?”见丈夫半天不表态,阿尼帕追问了一句。
“一块馕只够两个人分着吃,你把它掰成了十八块,怎么吃啊,这就是我们家的实际。”阿比包给妻子打了个恰如其分的比方。
“什么十八啊十九的,先不管这么多,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他们饿死。”阿尼帕态度坚决。
这是爱心作出的决定,这是善心作出的选择,没有功利,不图回报,这是人世间多么崇高的情感,又是多么崇高的人生境界啊!
这是阿尼帕夫妇收养的第一批孤儿——吐尔达洪和他的两个弟弟。
家里多了3口人,而且是毫无血缘关系且又是不同民族的“外来人”,本来并不宽裕的日子变得更加拮据了。
既然成了一家人,总要有个排行,有个称谓。吐尔达洪和阿尼帕的年龄相差无几,那时她还年轻,就在家里对孩子宣布:从现在起,吐尔达洪就是你们的大舅舅,还有二舅和三舅,你们不但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还要听舅舅们的话……这种称呼一直保持到今天,可在吐尔达洪兄弟眼中,他们称呼的“姐姐”,就是上帝派到自己身边来的母亲。
阿比包打心眼里喜欢吐尔达洪3兄弟,他们懂事、听话,个个像条男子汉,能帮助家里干重活。
家里的人口多了,住不下了,需要再扩建一间大房子。建房子需要的建筑材料是土块和麦草,从山下挖来泥土,掺上麦秸,浇上水,搅拌均匀之后,夯实了,晾干了,砌起来就是屋墙了。在当地建土房子用不着花钱,但需要的是力气。说实在的,在建房的那个秋天,小哥仨真的是出了很多力气。
房子建好了,眼看就到了冬天,小哥仨每天上山捡柴,把一冬天烧的都捡了回来。
家里人口多了,铺的盖的又成了新问题。这里是北中国最寒冷的地方,冬天的气温常常在零下40多度。当时家里13口人,11个孩子,只有两床被子,两个枕头和一条褥子,这些家当,还是当年他们在结婚时置办的。那被褥越盖越破,越盖越薄,被套里的棉絮已经无数次地被撕下,搓成灯捻,点了油灯。日久天长,被子里剩下的棉絮不多了,也不挡风寒了。
人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常常能产生超常的智慧。
那年,阿比包在供销社宰羊,后来他发现,那些残次的羊皮公家不要了,有的喂了狗,有的喂了狼。他灵机一动,就悄悄地卷回拿到家里来,积攒的多了,他跟当地一个皮匠学了一手“熟皮子”的手艺,大块的用来做被褥,小块的就给孩子们做些皮袜子、皮手套。阿尼帕亲手缝制的那床羊皮被子,少说也有十多斤重,超长,超厚,超暖。一条大被子全家13口人盖,阿比包和妻子睡中间,男女有别,孩子们则分睡左右。
有了新房,有了新被,有了热炕,那个冬天真的没觉得冷。如今,盖过那条羊皮大被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可每每想起当年,想起那条大被子,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当家过日子,离不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家里人口多了,锅也不够用了。阿比包便到供销社买回了一口直径1.2米的大铁锅。如今那口大铁锅在市面上很少见了,快成为文物了,平时很少用得上,可遇上葬礼或婚礼,招待亲朋好友也能派上用场,于是,这口大铁锅便在全县都出了名,经常有人会来借它。
阿尼帕当年收养的托乎提3兄弟,只有托乎提一人还健在。说起当年,时年64岁的托乎提依然很激动。我们之间不能用汉语直接交流,只能通过翻译和他对话。
他说:我没有文化,别人总是把自己故事写在纸上,我却把自己的故事记在心里。
他说:我的父亲是哈萨克族,3岁那年生父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改嫁到了继父家,继父是维族,不久又生了维族弟弟胡尔曼,于是,我们一个家就有了两个民族。继父是1962年去世的,他去世不到一年,母亲也离开人世,留下我们三兄弟。
他说:父母去世后,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安葬了父母,我又一次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父母去世不久,阿尼帕收养了我们,使我们重新找到了失落的母爱。如果没有阿尼帕,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她是一个伟大的姐姐,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他说:当时,阿尼帕的家并不富裕,当我们走进这个家时,他们家里已经有了10口人,可阿尼帕从来没把我们当外人,像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们,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带领我们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日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恩重如山的母爱。
他说:我的命运是不幸的,不幸中的大幸,是我遇上了好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在那个无比艰难的岁月,她自己不上学,却让弟弟妹妹们全部都上学,她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让孩子们吃饱饭,我会永远记住她的名字,永远为她祈福。
他说:阿尼帕一辈子养了许多许多孩子,现在只有她和小女儿在一起生活了,晚年的她很孤独,孩子们常回去看看她,可我眼睛不好,不方便,为此常常感到心里不安,她是能体谅的。
如今人到暮年的托乎提已经是儿孙满堂了,他最难忘的是当年自己成家的那段经历。
他回忆说:第一次相亲后,大舅哥捎回话来,不同意。理由一:我是孤儿;理由二:家里穷。阿尼帕通过媒婆去了趟女方家,跟他们说,托乎提过去曾经是孤儿,可现在不是了,他现在是我们家的成员,有户口本作证。我们是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家里人口多,穷是暂时的,一旦灾荒年过了,我们家会最快富起来。为了表达诚意,阿尼帕“姐姐”雇了一辆小四轮,给女方送去“彩礼”,锅碗瓢盆,床上用品,结婚用的东西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送去一只羊和200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彩礼”已是很耀眼很风光了。女方很快地就答应了婚事,热热闹闹地把媳妇娶回家来。
托乎提三兄弟的婚事和婚礼都是阿尼帕亲手操办的,都办得风风光光。
在阿尼帕家的户口簿上,登记着他们收养的孤儿名单,他们是:
吐尔达洪,养子,维吾尔族;
托乎提,养子,维吾尔族;
胡尔曼,养子,哈萨克族;
王作林,养子,回族;
王淑珍,养女,回族;
王淑英,养女,回族;
王淑花,养女,回族;
金海,养子,汉族;
金花,养女,汉族;
金雪莲,养女,汉族。
每一个进入这个家庭的孩子,阿尼帕都给他们取一个好听的且意味深长的维吾尔名字,在每一声呼唤中,都是在为他们祈福。
王淑珍的维族名字叫“哈比扎”,是“保护”的意思;
王作林的维族名字叫“切布”,含义是大树分出来的枝杈;
王淑英的维族名字叫“热孜亚”,含义是春天;
王淑花的维族名字叫“阿依古丽”,含义是美丽的月亮花;
金花的维族名字叫“玛丽亚”,含义是孝敬父母的女儿;
金海的维族名字叫“热马赞”,含义是阳光一样的男孩;
金雪莲的维族名字叫“索菲亚”,含义是清秀、鲜亮的花。
如今,很多孩子都成家了,并把自己的户口迁走了,可唯有哈比扎(王淑珍)没迁,人到中年结婚多年的她说,这里永远是她的家。
王淑珍是第二批走进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阿尼帕给她取名“哈比扎”,是因为这孩子太可怜,更需要“保护”。
往事不堪回首,说起当年的事情,王淑珍总是泪流满面。
王淑珍出生于1966年,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甘肃逃荒来到新疆,在青河萨尔托海乡落了户。父亲会种瓜种菜,勤俭持家,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凑合;父亲为人正派,邻里关系融洽,受人尊重。王淑珍两岁那年,一向安分守己的父亲突然被抓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苏联特务。冤枉啊冤枉!一个不识字、没文化、靠种地吃饭的农民,怎么能犯下如此“滔天之罪”啊?他无处申冤,自绝于世,以死抗争。
父亲含冤去世后,妈妈带着4个孩子改嫁到了金家,继父金建军是汉族,不久,妈妈又为金家生了3个孩子:金海、金花和金雪莲。母亲为金家生养3个孩子后,积劳成疾,撒手归西。继父身体也不好,他患的是哮喘病,已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怎么能养活这一大群孩子?他从此对生活失去信心,脾气也变得格外暴躁,动不动就冲孩子们发火。
那天,王淑珍又无缘无故地挨了继父一顿打,一气之下,她离家出走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家里这些人,哥哥王作林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亲人了。那年,哥哥在跃进公社上中学,是住校生,学校距家很远,又是山路,来去很不方便,哥哥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
她决定去找哥哥,在村口搭了一辆进山拉木头的拖拉机便上路了。第一次坐“铁牛”,那“铁牛”真的很“牛”,不用饮水,不用喂饲料,而且力大无比,上面坐了十多个人,跑得飞快。在她童年的记忆里,这次坐“铁牛”的经历让她引以为傲。
拖拉机停了,那地方叫红旗旅社,车上的人对她说,娃娃,你该下车了,我们要从这里进山了。她显然是没有坐过瘾,磨磨蹭蹭下了车。下了车一打听才知道,这里不是跃进公社,距跃进还远着哩。出来一整天了,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眼看天要黑了,到哪里去投宿?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面对这个无奈的处境,她哭了,边哭边喊:哥哥,你在哪里?哥哥,我饿!哥哥,我害怕!这凄厉的呼唤声传得很远,引来了一位好心人的脚步。
“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好心人边问边给她擦眼泪。
“我叫王淑珍。”她怯生生地回答。
“你一个人出来干什么?”
“找我哥。”
“找到了吗?”
“没有。”
“吃饭了吗?”
“没有。”
“想回家吗?”
“不想。”
通过简单聊天得知,这是一个失去母亲又没有父爱的孩子,从小没人照顾,生了一头癞疮,在家没有温暖,在外受人歧视,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地伤害。
好心人对她说,天这么晚了,今天哪里也去不成了,先跟我去吃顿饭,然后在这里住一夜,明天送你回家。
听说有饭吃,王淑珍喜出望外,庆幸遇上了好人。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她跟着好心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进去才知道那里是红旗公社卫生院,那个好心人是这个院里的医护士、阿尼帕的妹妹、她后来的小姨妈。
那天,王淑珍狼吞虎咽地吃了顿饱饭,吃完饭,小姨把她领进2号病房,这里刚好有一个病人出院,空着一张床,便让她在病床上住一夜。饱饱地吃了一顿,又美美地睡了一觉,王淑珍突然觉得此时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如果能天天吃饱饭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一大早,小姨带着一个年龄和她相差无几的女孩子进来,对她说:“孩子,这里是医院,只能临时住一个晚上,这是我女儿通萨古丽,你吃了早饭跟她去我们家,我姐姐会帮助你解决困难的。”
这顿早餐王淑珍吃得并不踏实,她觉得这“幸福”的日子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不知道这个好心人家在哪里?为什么不领她去找哥哥?带着一个又一个疑问,王淑珍迈进了这个她一生都离不开的家。
王淑珍刚刚走进大门,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喊:妈妈,那个女孩来了!听到禀报,阿尼帕出来迎接。远远的,王淑珍看到一张生动而又漂亮的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头上飘着一块丝织的头巾,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一种天然没有修饰的美,美得让人不敢接近又不肯离去,就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画中人”。
王淑珍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是自卑感使然。她觉得自己的衣服太脏太破,浑身是虱子,头上生满癞疮,那恶臭能拒人百米之外……她怕人嫌弃,有时自己也嫌弃自己。
“孩子,过来啊,走过来让我看看!”
王淑珍又往前挪了几步,还是停下了。严重的自卑,使她和这个世界有了距离感。
看到这个让人尴尬而又让人心酸的场面,阿尼帕紧走两步,来到王淑珍面前,一把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就在那个瞬间,王淑珍号啕大哭起来,那泪水像止不住的泉水向外喷涌。
“孩子,别哭,勇敢的孩子都不哭。”阿尼帕轻轻地劝慰说。
王淑珍够坚强的了,饥饿、疾病、歧视、谩骂、委屈……年仅10岁的她都经历了,她很少哭,可今天却实在忍不住了,这是感激的泪。
接下来,阿尼帕支起家里的那口大铁锅,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把王淑珍身上的衣服全部扒下来,扔进开水里烫了一遍,那上面长满了虱子,必须清除干净。接着又烧了一锅温水,痛痛快快地给她洗了一个澡,在王淑珍的记忆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洗澡,洗去的不仅是她身上的污垢,还有她心灵上的蒙尘。洗完澡,阿尼帕给她拿来一套干净衣服换上,接着走进厨房,又给她做了一大碗拌面。起初,王淑珍不好意思吃,因为她看到拌面只有一碗,周围还有那么多渴望的目光……王淑珍真的不敢相信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她经受了太多的苦难,看惯了世态炎凉。
王淑珍的头疮是阿尼帕最大的一块心病。一个女孩子家,没有秀发,一头脓疮,将来怎么办?哪里能治这种病?能不能治好?经多方打听,王淑珍的头疮并不是什么顽症,而是一种普通的皮肤病,因为家里穷,从没求过医,也没敷过药,这病整整折磨她10年,连爹妈也说这病是从胎里带来的,小朋友给她取了个外号叫“骚头”,久而久之,家里人也这样跟着叫。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
阿尼帕带着王淑珍到了县医院,医院说,这里没有皮肤科医生,推荐她们到兽医站,说兽医站有医生能治疗牛癣。有病乱投医,她们又去了兽医站。兽医站医生起初不肯接诊,理由很简单,她们看病走错了门。只要能治好病就行,经过她们再三恳求,一位兽医答应用一种治疗黄牛癣的药膏抹抹看,医生还交代说,治这种病,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保持头部清洁,天天要洗头,天天涂药膏。
第一次给王淑珍洗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满头的脓疮结了厚厚的一层痂,厚厚的痂要一层层揭掉,揭一层流的是脓,再揭一层流的是血。“孩子,疼吗?”“不疼!妈妈。”能不疼吗?孩子在说假话,她能感觉到坐在怀里的那个瘦小的身体在抖动。“孩子,要坚持!”她继续鼓励。
就这样每天坚持洗头,每天涂药,1个月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王淑珍头皮上出现了一层黄绒绒的头发。看到了希望之光,阿尼帕又按照医生的嘱咐,买来一把剃头刀,每周给王淑珍刮一次头皮。渐渐的,黄发变成黑发,黑发变成了长发。
半年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一天,阿尼帕递给王淑珍一面镜子对她说,娃娃,快去照照镜子。王淑珍突然变得不好意思起来,拿着镜子跑到屋里,还是没有勇气照,于是又拿着镜子跑到院子里。10年,她知道自己形象不佳,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啥模样。
王淑珍真正看到自己的模样不是在镜子里,而是在水桶里。那天帮妈妈做饭,从水井里打了一桶水,在弯腰提水的那个瞬间,她突然发现水面上浮现出一个满头黑发的漂亮面孔,看着看着,她发现水桶里的那个影子变得模糊了……
人们常说,发肤受之于父母。可王淑珍却说,父母给了我一头癞疮,阿尼帕妈妈给了我满头黑发。从她有了黑发的那天起,她就发愿说,这头黑发是阿尼帕妈妈给的,她永远不再剪头了,让这头黑发见证母爱的伟大。
人心就是一杆秤,能称得出情感的分量。仅有的一碗拌面王淑珍吃了,仅有的一条花裙子王淑珍穿了,王淑珍不知道该怎么回报这大恩大德,她思量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对阿尼帕说: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阿尼帕慈祥地笑笑,和蔼可亲地回答说:我早已经把你当女儿看待了,如果你愿意留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听了妈妈的许诺,王淑珍双膝跪地,虔诚地给妈妈磕了3个响头。
王淑珍离家出走找哥哥,没找到哥哥却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个妈,这是她一生的造化。

王淑珍离开家大半年了,最牵挂的是哥哥。妈妈最懂女儿心。一天,她把大儿子贾帕儿叫到身边说:“哈比扎有个哥哥在跃进上中学,你带妹妹去找哥哥,路途远,路上要把妹妹照顾好。”听说要去找哥哥,哈比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像一只快乐鸟,一路上唧唧喳喳地唱着、跳着。在她童年的记忆里,哥哥就是她的保护神,在她受人欺负的时候哥哥总是挺身而出保护她,这份兄妹之情常常让她感动。
站在学校门口等了许久,才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大半年不见了,哥哥又长高了一截,越发像个男子汉了。
“哥哥——”王淑珍放开嗓子在校门口呼唤。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哥哥王作林疾步跑出校门,兄妹相见的那个瞬间,四目相望,眼神里流露出的全是惊喜。
“你怎么来了?”哥哥惊喜地问。
“想来看看你。”
“跟谁来的?”
“是贾帕儿哥哥送我来的。”她边解释边指了指身边那个维族小伙子,同时给贾帕儿介绍说:“这是我哥哥王作林。”
这贾帕儿是谁?是哪来的哥哥?王作林一时陷入云里雾中。
更让王作林疑惑的是,他居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妹妹王淑珍吗?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一头黑发,一脸喜悦。她头上的癞疮呢?是谁给她买的花裙子?
“哥,我出来找你,迷了路,遇到一个好心人收养了我,给我治好了头疮,还给我买了花裙子……”王淑珍津津乐道地给哥哥讲述她的奇遇,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哥,我又有妈妈了,这个妈妈不但是好心人,而且很漂亮。不信?跟我回家看看。临来之前妈妈对我说,也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王淑珍给哥哥做动员工作,希望他也能走到这个家里来。
王作林真的跟着妹妹来了,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人,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事。连父母都抛弃的孩子,还有人收养?
带着审视的目光走进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首先看到的是凉棚下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和一群在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足有十多个,看上去,这里更像是个幼儿园。这是他的第一印象。
“妈,这是我哥王作林。”王淑珍介绍说。
阿尼帕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上前来,仔细地端详着眼前这个带有几分英气的中学生,夸赞道:“小伙子,漂亮的很嘛!来来来,我们聊聊,今天就在这里吃午饭。我们家人多,热闹得很嘛。”阿尼帕一边做饭,一边跟王作林聊天,聊学习,聊生活,聊家庭,聊未来……和阿尼帕聊天,初来乍到的王作林一点不觉得有陌生感,就像重新回到那阔别已久的家里。
从聊天中得知,王作林所在的学校学习环境很差,孩子们不愿意学,老师们也不愿意教,助学金不够吃饭,买不起学习用品,经常捡同学们扔掉的铅笔头做作业,看到的是白眼,受到的是奚落,他不想再上了。
“你还年轻,不上学不行,如果牧区的学校环境差,就到县城里来读书,吃住在我家,不用花钱,这样助学金就够用了。”听了这位有爱心的母亲给自己设计的前程,王作林心存感激。
阿尼帕没有食言,她以养子的名义把王作林的名字添加在自家的户口簿上,让他转到县城里来上学。
又是一个意想不到,面对人生这个幸运的拐点,王作林冰冷的心充满了暖意。
从迁户口那天起,王作林和妹妹一样真正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在编成员了。
王淑珍、王作林兄妹有了归宿,一奶同胞的王淑英、王淑花依然是两只孤雁。阿尼帕知道王作林兄妹的身世后,知道他们兄妹4人,牵着骨,连着肉,怎么能把他们分开呢?
“一起把她们也接过来吧,没有妈的孩子太可怜了。”放寒假了,阿尼帕打发王作林兄妹回老家,把两个妹妹一起接来住。
当王作林兄妹回到家时,家里又发生了变故,继父金学军去世了,留下了3个异父同母的孩子:金海、金花、金雪莲。
看到哥哥姐姐回来了,全家人团聚了,弟弟妹妹们脸上出现过彩虹般的笑容,可瞬间又消失了。听说哥哥姐姐要带王家姐妹走,金家3兄妹一脸的茫然。
“哥哥,姐姐,求求你们了,带我们一起去吧!”临走那天,金氏三兄妹突然抱住王作林和王淑珍的腿,哭诉着恳求,那哭声撕心裂肺。剪不断的血脉,扯不断的亲情,王作林无法拒绝,只好改变主意,带着全家7个孩子一起投奔了阿尼帕妈妈。
阿尼帕以菩萨般的爱心,接纳了王淑珍7兄妹。
(未完待续)
栏目主持:吕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