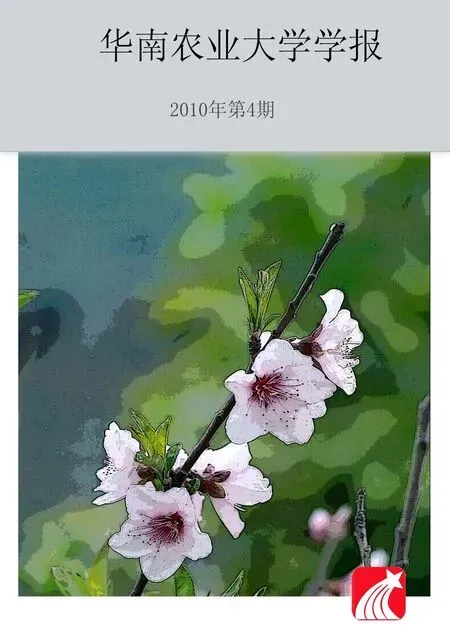财产制度制约县域金融的实证研究
2010-11-21周天芸
周天芸
(中山大学 a.国际商学院; b.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国县域经济的迅速增长必须有资金的支持,但目前我国的县域金融处于困境,表现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大规模撤出,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贷款数量减少,县域地区的资金大量外流。2007年农行、农发行、信用社、邮政储蓄四类机构在县域吸收的储蓄存款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以上,当年全部涉农贷款大约在5万亿元左右,农村资金净外流7万亿元左右。县级金融机构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平均乐观估计为56%,个别县接近30%左右的水平*《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60年》。虽然有学者认为资本的趋利属性使县域资金流向城市,但我国金融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市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性质和垄断地位决定资金流动无法完全依照效率原则;我国县域是“有城有乡、有工有农”的行政区;县域经济占全部GDP的50%,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表明,县域金融已非传统意义的农业金融或者农村金融,其金融困境无法破解的原因是未涉及我国目前县域的财产特性。
我们认为,导致中国县域资金外流的原因在于财产制度及县域财产的特性,在于县域财产的特性无法满足商业银行要求的抵押标准。但是,中国县域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除少数贫困县外,大多数县域的经济财产总量已经有巨大增长,这些财产正为当地居民创造着庞大的收入流,但这些财产目前无法获得银行信用的支持,原因在于这些财产既不合银行之“规”,也难符监管之“法”。由于商业银行对于抵押品的估价与借款人不同,导致商业银行无法根据县域经济所形成的财产发放贷款,从而无法实现县域的信贷交易。
一、抵押与银行信用的理论分析
金融问题与财产制度密切相关,财产制度是一系列法律法规体系与非正规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Besanko,D.& Thakor,A.V.[1]研究发现,在正规法律制度无法符合实际经济发展时,通常会出现大量不合“规”和不合“法”的财产,并且在不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充当抵押品。Clive Bell & Gerhard Clemenz[2]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财产通常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弱化的土地交易市场,农民只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因此土地成为农民的“非交易”财产,缺乏流动性。第二:法律法规倾向于运用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产权清晰的土地通常容易实现财产向信用的转化。Besanko,D.& Thakor,A.V.[3]发现,合乎现行法规体系的财产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最小化,因此金融机构通常依照现行法律法规选择银行信用的抵押资产;Chan,Y.S.& Kanatas,G.[4]则明确借贷双方对于抵押品的不同评价将直接影响交易是否实现。
中国县域的土地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县域经济中一些不合现行“法”和“规”的财产不仅流动性很好,而且为使用者或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收入流。但是,中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确立土地所有的国家和集体的分有制。《担保法》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中国《物权法》的城市化倾向严重,使农村金融交易面临制度障碍,贷款人权利保护遭遇产权制度的障碍。
由于县域财产无法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认证、登记,因此无法进入现行的金融体系获得信用,更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实现资本化。陈剑波[5]认为,大量财产无法获得信用支持引发两个后果,一是县域内绝大部分经济主体达不到信贷准入的条件;二是如果严格按照目前信贷管理和监管规定展开经营活动,国有商业银行县级机构必须争夺符合规定的客户资源,从而造成风险日益向单一客户集中的趋势,加大经营风险。因此,割裂的财产权利,如房产等农民私产无法资本化;城乡割裂、互不相融的二元物权权益体系造成县域“有财产而无信用”,缺乏保障的财产体系导致信用不足,农村财产制度成为扩大银行信用主要障碍。
周立[6]认为,中国农村并非没有抵押物,而是缺乏商业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物,农村也并非没有克服抵押物缺乏导致赖账风险的措施(比如声誉机制、担保机制等),但这些机制仅在社区内部有效,商业银行则无法利用这些措施。陈坚[7]认为,中国农村财产权利体系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土地、房屋既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是农民最为主要、也最有价值的财产,虽然这些财产在竞争性市场中是最容易资本化的财产,但却因为产权不明晰、市场发育程度过低而使其难以成为农村居民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有效保障。张宇[8]认为,县域的微观经济主体存在先天缺陷,由于自身资本原始积累不足,在申请贷款时,无法向银行提供抵、质押物作为担保,商业银行为规避风险,必然回避县域金融业务。综上,国内外学者已经发现制约县域金融的重要因素,而这个结论也可以在理论模型加以证明。
1.基本模型
假定县域经济中存在两类经济主体,借款人(县域经济中的企业与农户)和贷款人(县域经济中的金融机构),借款人拥有不可交易的资产,如拥有面积为A的土地,贷款人拥有数量为y的货币,通过选择安全的借款人、经营贷款而获取收益。借款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选择传统技术下的简单再生产,此时不需要外部融资,其结果是成功,获得货币表示的收益q,或者失败则收益为0;一是选择采用先进技术的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使用已有的土地资源外,需要数量为B的外部融资,其结果同样为成功,获得货币表示的收益f(B),或者失败则收益为0。我们构造单期模型,分析在借贷双方对抵押品估价不同时,是否存在双方都接受的借贷合约以实现信贷交易。
假设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是风险中性,两类人对于充当抵押的土地有各自的估价,借款人估价为V,而贷款人估价为v,同时假定借款人对自身所拥有的土地估价比贷款人要高,即V>v。
借款人实现收益的概率为π,其成本为c且随着实现收益概率的上升而单调递增,假定该函数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即c(0)=c(π),满足c(0)=c′(0)=0,以便该函数有内点解。
如果借款人选择简单再生产,则其保留效用为:Ω=ρ+V。其中,ρ是运用土地资源简单再生产的预期收益,按照前面的假设,ρ大于0且随q增加而增加。如果贷款人筛选安全的借款人并贷出资金,则其保留效用为:ω=Iy。其中I=1+i,i是利率。
在上述双方的保留效用中,需要考虑资产价值因素。无论是完全信息和无成本监督,还是非对称信息和有成本监督条件下,给定贷款人选择的贷款数量B,借款人仅可以选择实现收益的概率π,对于任何给定的贷款数量B,使得:π(B)=arg max[πf(B)-IB-c(π)]且集合S={B:π(B)f(B)-IB-c[π(B)]>ρ,B 2.模型的讨论与经济意义 完全信息和无监督成本情形中,假定π和B同时决定以最大化借贷双方的效用函数,表示为:max[(πf(B)-IB-c(π))]满足0≥B≥y,π∈[0,1]。 同时假定贷款人的贷款不受资金的限制和制约,即B≥y。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上式存在内点解,并求得其一阶导数:πf′-I=0和f(B)-c′(π)=0,前者说明最优条件下,融资的边际产出等于利息,而后者说明实现的收益等于借款人为实现收益而增加的成本。 假定借贷合约为(P,A),此时,借款人在合约(P,A)下的预期效用为: EΩf(P,A)=πf(B)-c(π)+I(p-B),B≤P。E表示借款人的选择,如果B*≤P,选择(B*,π*),如果B*>P,则选择B=P,且π满足f(P)=c′(π)。 上述模型结论表明,抵押估价对于信贷交易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借贷双方对抵押品的估价不同,则不可能存在借贷双方都接受的合约。 对于我国县域经济中的信贷交易,由于财产制度的规定,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与金融机构对土地的估价是不同的。在特定借贷数量和利率水平条件下,由于县域财产的属性特征,借贷双方对于最大的抵押资源——土地——的评价不同,因此,中国县域金融市场不存在借贷双方都接受的合约,从而无法实现县域经济范围内的信贷交易,这在理论上证明县域金融由于抵押制约造成的交易困境。 通常,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随抵押资源的增加而增加,由于中国目前的财产制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该结论在县域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根据《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年)有关广东区县的统计资料,运用广东78个区县2008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县域经济中土地抵押资源与信用脱节的状况。 1.数据的基本特征 根据《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年)的统计指标,使用的统计指标包括: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万元),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平方公里),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 基于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广东县域经济、金融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1 对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 从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广东大部分县域的资金呈现一定程度的资金净流出特征,贷款和储蓄两者均保持在低水平;县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银行贷款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缺口,一定程度反映金融机构货款主要流向和支持倾向,反映金融机构在县域贷款的特征。 2.实证结果与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基本模型为:Yt=β+∑βiXit+μt 使用统计软件Eviews 5进行OLS回归分析,因变量则选择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中非银行融资部分,解释变量选择可用于抵押的土地资源、产出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县域经济中实际创造国民收入的财产数量相比较于符合现行法律法规、通过抵押方式获得银行信用的财产非常有限。银行贷款由于对于抵押的估价,特别是县域经济中的土地的性质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使得银行贷款与土地资源缺乏相关性;考虑到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出具有充当抵押的性质,同时检验银行贷款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 表2 影响银行放贷因素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参数估计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1)银行贷款余额与土地资源没有统计显著关系,说明金融机构放款并不依据可用于抵押的县域土地面积;(2)银行贷款余额与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出存在统计显著关系,但是银行贷款余额与第一产业的产出负相关,与第二产业的产出正相关,以农业为主的县域无法获得相应的银行贷款,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主要选择工业企业;(3)银行贷款余额与居民储蓄存在显著统计关系,尽管其系数不大,但是储蓄反映县域的资金充裕程度,一定程度影响金融机构的放款。 如果我们将经济主体的固定资产总投资扣除银行贷款部分,则其差额反映经济主体的自我融资水平,我们以此作为应变量,检验其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3 影响自我融资水平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参数估计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1)县域的非银行资金来源与土地资源仍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意味县域经济非正式金融的运作同样不认可土地的抵押价值,原因可能是土地的非流通性和所有权的属性,导致县域的非正式金融更多依赖软性信息,特别重视借款人的年龄、学历、家庭类型、收入来源等还款保证信息[9],而对土地的抵押价值仍然缺乏认同。(2)非银行资金来源与第一产业的产出存在统计显著关系,且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说明县域的非银行信用可以农业产出作为抵押,虽然无法获得相应的银行贷款,但非银行类的信用由此可以增加,原因可能是借贷双方对于农业产出品作为抵押的认可[10];非银行资金来源与第二产业的产出不存在统计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正式金融机构主要据此发放信用。(3)非银行资金来源与居民储蓄存在显著的反向变动关系,意味着随着居民储蓄数量的增加,县域非银行资金来源的数量可能下降,一定程度反映非银行资金来源的现金特征。 通过广东县域的截面数据,我们初步验证县域金融交易的特征,证明由于县域土地的属性和特征,使得信贷交易脱离抵押资源,从而处于无法增加信贷交易数量的困境。 通过上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我们认为,我国县域经济中土地的经营者与金融机构对土地抵押估价不同,因此,不存在借贷双方都接受的合约,从而无法实现县域范围内的信贷交易,这在理论上证明县域金融由于抵押制约造成的交易困境;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机构放贷并没有依据土地资源,且贷款主要选择具有抵押的工业企业,县域的非正式金融同样不认可土地的抵押价值,说明县域的信贷双方缺乏共同的土地抵押价值。 因此,对于县域金融的“失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合乎市场经济逻辑的现象,县域资金外流部分是市场因素所致,但很大程度是由于法律、法规和体制因素所致,中国县域财产受到担保物权法律的制约,无法转化成为银行信用。 虽然基于国际经验,财产制度的演进是非常缓慢的,美国在1785—1890年中通过500多个土地法案,经历极其复杂的从不合法所有权制度向合法的所有权制度转变的过程,而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大量不符合现行法规或受到现行法规限制的僵化资本[11]。但是,经济的发展需要改革和创新,中国的县域金融需要推动制度创新,根据县域现有的财产特征,设计规范标准、为商业银行所接受的抵押,或者设计适合中国县域的抵押替代,以克服县域信贷交易的困境。 总之,中国县域信贷交易困境在于抵押资源及转化,通过动产抵押的创新设计和信用担保等形式的创新,能够拓宽解决农村信贷交易困境的思路,而财产制度及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对于突破县域金融的困境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BESANKO D,THAKOR A V.Collateral and rationing:Sorting Equilibria in monopolistic and competitive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7,(28):671-689. [2] CLIVE B,GERHARD C.Credit markets with moral hazard and heterogeneous valuations of collateral[J].Research in Economics,1998,52:285-309. [3] BESTER H.SCREENING V S.Rationing in credit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4). [4] CHAN Y S,KANATAS G.Asymmetric valuations and the role of collateral in loan agreement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85,(17):84-95. [5] 陈剑波.财产制度与银行信用[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7,(2):32-33. [6] 周 立.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及其演化逻辑[J].财贸经济,2007,(2):56-63. [7] 陈 坚.中国农村金融深化发展途径分析[J].上海金融,2009,(9):32-36. [8] 张 宇.论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支持——以四川省双流县为例[J].经济体制与改革,2010,(4):150-155. [9] KOCHAR A.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in Ind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532:339-371. [10]MAHMOUD S MOHIELDIN,PETER W W.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Egypt[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4):657-670. [11]黎和贵.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及经验借鉴[J].国际金融研究,2009,(1):36-41.


二、县域财产特性与银行信用的实证



三、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