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丧失母性的历史悲剧重演
2010-11-18汤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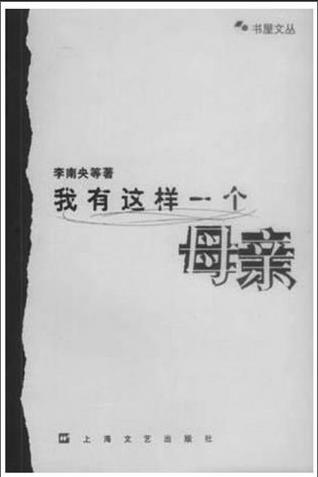
我们以前所接触的中外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歌颂性的、崇高而伟大的,如高尔基的《母亲》、朱德的《我的母亲》等。然而在海外看到李南央所著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老鬼所著的《我的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却明显感觉到是少有的塑造了负面母亲形象的两本书。
李南央,李锐与范元甄之女。李锐曾担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范元甄,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
李南央说: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
李南央在书中写道:小就未有享受到母爱,未尝过与母亲亲昵的滋味。不仅如此,子女还遭到过母亲的毒打。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由于阶级关系高于一切,人们无视家庭的价值,夫妻之间以及两代人之间可以随意反目。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发现:文革中自杀的很多知识分子,其陷入绝望并不是因为遭到批斗,而是在批斗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家庭的关爱,没有家庭的温暖使他们更绝望。在一个革命家庭中,母亲不愿意为子女花时间,为了革命可以牺牲要孩子,为了革命甚至可以大义灭亲。母性在那样的年代遭到彻底泯灭。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我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 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地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 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无独有偶。另一本书《母亲杨沫》的作者老鬼姓马名波,是作家杨沫的小儿子。老鬼说,在这本“概述母亲一生”的书里,他要“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
老鬼用相当多的笔墨,在书中写了母亲杨沫早年在烽火岁月中的革命经历,写了她创作、出版《青春之歌》前后的艰难曲折、声名鹊起以及几度风风雨雨,这些无疑是杨沫一生中的“华彩篇章”。 与此同时,老鬼又坦诚直率地写到了母亲杨沫的另一面。
“文革”中杨沫与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可以说是置之于死地、“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书中将这些揭发、交待材料都原文照录下来。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像马、杨这种夫妻反目的事,当然不是绝无仅有;但即使在当时那种“革命”、“专政”的高压之下,夫 妻之间、家人之间互相保护、相濡以沫的事情也不会没有。马、杨之间的互相揭发,给彼此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老鬼说:“这导致了两个人感情 上不可弥补的裂痕。”
然而使老鬼最感痛切的,是母亲杨沫身上母性、亲情的泯失,“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老鬼认为,这是母亲自小生活在缺乏母爱和亲情的冷酷环境中所造成的,杨沫虽然出生大户人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杨沫说过: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温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场所。但对她来说,却是个冰冷的,阴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杨沫对子女的冷漠也跟长期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氛围有关。老鬼在书中写道,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里,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老鬼那时从学校回到家里,经常吃不饱,而且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老鬼说:“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他的哥哥也是这样,有时甚至在家饿昏过去;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老鬼六岁时,有一次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母亲杨沫也不当一回事,过了几天眼看他奄奄一息了,才让十几岁的大儿子带他去医院,医生动完手术之后说:“再晚就没救了。”老鬼说:“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并不常见。”杨沫(及丈夫)还动辄跟子女“断绝来往”,有时还作出令人寒心的举动。1979年,正在北大读书的老鬼,与父母发生观点的冲突,杨沫便写信给北大中文系,对儿子的言行加以揭发和谴责,要求学校严加管教或给以必要的处分。老鬼说:“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痛切地刻画了母亲范元甄那扭曲的灵魂,及因她的乖戾暴虐给家人造成的伤害。这本书中的“这样一个”,看似指范元甄一人,实际上包含着“一类革命女干部”。
在“红色恐怖”降临己身时,范元甄不惜出卖丈夫以求解脱;为“表现”自己的“革命”,捏造事实,害得弟弟英年早逝;妹妹病危之际,在妹妹脆若游丝的生命上捅上最后一刀;至爱亲朋无不遭受过她的告密陷害,无不经受过她各种各样的伤害。用李南央的话说就是: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范元甄现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为了政治,不讲亲情。为了自保,为了自欺欺人的“原则”,对亲人落井下石、揭发告密;事过境迁,又极力卫护致使自己深受其害、又害别人的时代。她也只能通过这些无谓的挣扎,用自我欺骗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理籍慰,用此来反抗自己荒芜一生的空虚、众叛亲离的孤寂和良心回归的不安。
老鬼的《母亲杨沫》中不难看出杨沫身上范元甄的影子。
老鬼在谈《母亲杨沫》创作时,谈了母亲杨沫灵魂扭曲的过程:“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老鬼说:“困难时期在家里吃不饱,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却不给孩子吃。每逢我看到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那么和谐,彼此那么关心,就特别羡慕。”
李南央母亲范元甄在延安时,曾经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李南央写道:“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道:当年上海去延安的进步青年、电影明星李云鹤,艺名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非常显眼。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非常富有女性的魅力,给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最后她们这些美女的女性母性全为党性所取代。失去母性的女性最后自己异化成没有人类情感的“铁人”。岂止是女性,所有参加这场革命的人在革命中,都以革命的名义使得人情变得淡漠,人性渐渐失去。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而这些女性是文革这个荒唐无稽时代的最大受害者。文革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以牺牲家庭、以剥夺母性、将人们改造成只有阶级性的人,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有评论说:“这两本书之所以别具价值,就是它们以一种严酷又痛苦的真实,记录了两个特别的人物和两个特别家庭的悲情,又以这两个特别人物和特别家庭的悲情,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这两本书将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相连,是充满了血和泪的作品,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有力控诉。我们不能再让丧失母性的历史悲剧重演”。“这两本书,出于将自己的经历保存下来为他人日后所知的信念,秉笔直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亲形象。这两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很好的资料”。
有评论特别指出:作为经历了苦难的民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该将这些苦难尽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例如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都被他们转化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反观我们自己,还是在历史事实面前采取遗忘、甚至回避的态度。如果苦难不能转化成精神财富,灾难就会重新降临在同一土地上。曾几何时,我们中国把琴棋书画、四书五经以封建糟粕等罪名赶出了课堂。提倡人性和母性的作家如冰心,竟遭到无辜批判。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的道德规范被当作封建思想彻底扫除,代之以暴力论无神论。中国人在虚假、暴虐的文化氛围中成型,身上浸染积聚了过多的毒素,仁爱、宽容、谅解、尊重他人的成分稀少,而这些又恰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人类重大灾难,大多是由于人性恶的共振引起的自噬。遵守心中的道德定律,是遏制人类兽性萌动避免这些灾难发生的唯一办法。而守住心中道德定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恪守住真,真之所至善萌生焉,真是人类一切美好价值的基石。因为,幸福的社会必须有合乎人性的制度来保障,合乎人性的制度必须由正常人格的人去运作,正常人格的人必须有健康的人性,健康的人性有赖于真实向上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里恰恰缺少这些。文化重建——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对中国尤其显得重要。
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担任高管的章敏女士在谈及自己历经艰辛、在美国的成功之道时说的:具有优雅的魅力是女性驰骋商场职场的有力武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聪明才智、见多识广、反应敏捷、举止优雅的女性总是会受到欢迎,一个处处优雅具有魅力的人总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受到中国“文革”影响的一代中国女性,早已经失去了那种优雅,中国女性“灰头土脸”的打扮、大大咧咧的举止、不善交往的特征,严重影响了她们在美国职场的发展。章敏还专门提到《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一生不改高贵、优雅。在“文革”中即使落难牢狱,也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理念。人们从《上海生与死》一书中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面对野蛮和强权的侵犯时,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道德律。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能够行动,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雅。由于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 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六年的牢狱生活,虽然身陷囹圄,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布置那一块巴掌大的小天地,尽可能生活得有质量,为未来做好准备,这种面对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起敬!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郑念是一个美丽的、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章敏说:在美国女权主义思潮走向没落的今天,知性女人追求的应该是“成熟、理性、大器、智慧”,而不是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女强人形象。女性应该是感情丰富具有女人味,“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世故当中不失天真,张狂之中不失纯正”。女人要不忘自己的性别,具有内在和外在美的结合,才符合女性本身的规律。
汤伟,旅美学者,现居美国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