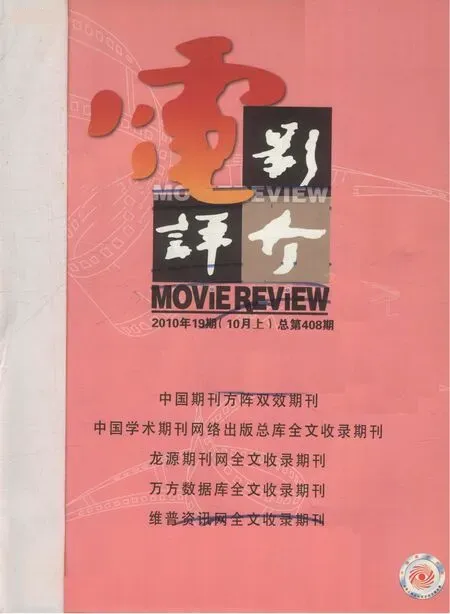浅谈艺术对宗法的穿越
2010-11-16单永军
引言
中国古代艺术根植于宗法社会,宗法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有深刻的影响。刘道广先生在《中国艺术思想史纲》前言中指出“……中国艺术思想受制于传统宗法意志和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思想也在挣脱宗法意识的制约中有所变化。”[1]笔者也认为,艺术虽然受制约于宗法,但是艺术毕竟是艺术,有自身追求独立寻求自由的渴望,因而穿越宗法显示自身。中国艺术无疑和宗法有密切的关联,但不仅仅是受其制约,而是在同宗法思想的博弈中体现独立性。艺术既在宗法之中,又能穿越宗法。当宗法性增强时,艺术性减弱;当宗法性减弱时,宗法思想强烈。那么,艺术是如何穿越宗法的呢?
一、 艺术与宗法
中国古代艺术在与宗法的交融、对照甚至批判中获得其合法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艺术与宗法的关系。
何谓宗法?宗法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在家庭、家族这个范围内,一个人的身份,主要决定于血缘关系。宗法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衍生出的。“身体流动的血,成了生命的符号,不仅仅是生命的基因,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基因。它可以繁衍,可以承传,构成了家族制的最为强大的纽带。”[2]“宗法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的演变过程,贯穿这一演变的主线是血缘的脉络。”[3]可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文明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特色。艺术和宗法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宗法思想是中国艺术思想的主流。中国古代艺术具有浓重的乡土意识、家国观念和情感血脉。歌曲《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小说《白鹿原》、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等都弥漫着浓重的宗法意识。其次,艺术思想并不等同于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主流但不是唯一。任何艺术思想的发现必然是从艺术形式本身出发,否则便是单纯的思想而非艺术思想。
在艺术与宗法思想的关系上,一方面艺术受宗法制度制约,另一方面艺术表现出与宗法思想的对照、疏离与超越,是在规范之中寻找自由。艺术其实是在不断见证宗法的束缚,同时又不断摆脱宗法走向自由。中国优秀的艺术既能生存于宗法的土壤,又能穿越于宗法。中国优秀的艺术一方面能对根深蒂固的宗法思想深度展示,另一方面又能穿越宗法,见证生命的魅力。
那么,中国艺术又是怎样依存于宗法,又摆脱宗法的呢?中国最优秀的艺术能够在宗法的两端上深入思考与体验,创造出艺术的化境。所谓执其两端即在两个原点来寻求超越,一个起点,一个是远点。艺术对宗法的穿越之路也是两个方向。一条是起点还原,即还原到宗法产生的人性基点上,即回到其来源处和艺术现象相互对照。一个是远点伸展,即在血缘关系最远的衍生点上来看,“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远点即是返回原点。归结为一点,还原即中国艺术对宗法的穿越之路。艺术的两端方向的伸展形成了中国艺术的张力和魅力。
这种还原主要体现为情感、自然、空性之维来实现的。
二、情感之维
世界的关系包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在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最源初的关系其实是血缘关系。血缘正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原点。
艺术是人的情感的显现。情感也有多种情感。情感产生于人伦之情。从宗法的角度看,血缘之亲情,如母子之爱、舐犊情深,兄弟姐妹之爱等最原初的情感。这种血缘之情是宗法制的原点。宗法制一步步由家到国到天下扩大的过程中,其实是一步步背离血缘之情的,悖于常情的。最初的血缘之情感,在宗法的演变、礼乐的束缚、理学的钳制中慢慢走向反面。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回家、还乡等主题即是回归还原至血缘之情的原点。如“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还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无论还乡、还是回家,其实都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存在,这是中国人生命的起点,也是最温暖的地方。中国似乎更喜欢叶落归根,余光中的《乡愁》道出的是一种普遍的乡土情节。
爱情是处于血缘之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情感。爱情是基于人之本性的需要而产生,具有普适的价值。人类自始有情根。正如《红楼梦》中讲那块补天的石头被置于青埂峰下,青埂即情根是也。补天的石头具有天地之灵性,不同于世间之浊物。同在天界的绛珠仙草也是如此。情感的萌生来源于天性,或者说具纯粹性、无功利性。不同于血缘之情,自然也不同于宗法。《红楼梦》以爱情穿越宗法,见证了宗法社会的虚伪、浑浊和腐烂。或者说,《红楼梦》以天缘取代血缘,以情感反思宗法。情与礼的冲突,情与法的冲突,始终是中国艺术一条重要的线索。中国四大民间传说都是爱情,皆流传千年,深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爱情是纯粹的情感,是人类的情根。纯粹爱情的书写无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血缘之情。但是,在许多时候,爱情已经弥漫了浓重的宗法气息,遭受了来自宗法社会的制度、规范以及意识控制的重重障碍。在《红楼梦》中,宝黛之情逐步剥离了现实功利的金玉良缘,指出了“文死谏,武死战”的名与利的虚伪。曹雪芹以纯粹的爱情穿越宗法的迷障,否定了其对人性的重压。中国许多爱情诗,其情感之炽热,之决绝,不是一个宗法所能涵盖的。“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与君绝。”中国艺术的魅力在于宗法,更在于情感在宗法之中穿行的婉转之美。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即在婉转、深情、缠绵悱恻的乐音中让人感动不已。
三、自然之维
道家让人回归于自然之中。道家精神也是最具有艺术气质的,道家哲学点染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不仅仅是现实的投身,人心的投射,更是“气”的产生。“气”才是艺术的真正本源。“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钟嵘在这里将艺术之源推向物、推向气。
受道家思想等的深远影响,中国艺术逐渐在摆脱宗法的规范中,拓展了艺术的宇宙意识与天地境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典型的例子。在那个月夜,彷佛回到了原初,回到最温暖、最澄澈的家园。人与物皆融化于宇宙之中。就绘画而言,中国绘画中人占据的空间很小,即丈山尺树,寸马分人。有时候都没有人,只有山水和花草树木,人已消散于、融化于自然风景中,但敞开的却是无边的心胸。这种思想却非宗法等所能涵盖的。
道家的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也还是一种还原之维。自然一方面是自然界,另一方面即自然而然。自然世界作为宗法社会的来源,作为宗法社会的一面镜子。以植物之心来映射人伦之心,在生命的起源处寻找意义。《红楼梦》中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说法。草木、石头本是自然之物之常态,而金玉则是人文雕琢之物。诗歌中也有“草木有本心”之说。这里的草木、石头、本心等皆具有还原的意义,即将人伦之情感还原为自然的草木之情,将宗法之血缘还原为自然之联系。《红楼梦》正是作为自然界的顽石被一僧一道带到了人间,成为玉,又从人间返回自然。石头的意义穿越了宗法,获得了生命的本源意义。陶渊明也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欣喜于“复得返自然”。从天境与人境之中来因正人伦、宗法的束缚,从而隐含着对宗法的批判之维。自然的另外之意在自然而然。对于人的自然而然来说,那就是保持一颗童心,保持本性。道家思想将宗法之原点往前推了一步,慢慢消解了宗法对艺术的钳制,获得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四、空性之维
除了情感的还原,艺术的还原还有一条哲学之路。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同时也为中国艺术迎来拓展其境界的大智慧。禅宗思维影响了艺术,也使艺术境界、艺术思想穿越宗法,从而获得更高的境界。
禅宗之于中国艺术的贡献主要在“空”的呈现。“因此,如果大体而论,说庄子是自然人,儒者是道德人,玄学家是准自然人,那么可以断言,禅者决不是自然人。不仅如此,以后的中国人中也不再有纯然庄子式的自然人了,看空成为中国思维的一种新的质素,它是一种精神品格,也是一种思维方法,这方面,王维、苏东坡都是绝好的个案。”[4]如果说儒家有所执,道家有所忘的话,那么禅宗更是彻底的消解。消解了宗法的血缘,也消解了道家的自然,还原世界一个空空荡荡。禅宗以心为本体,倡导万有皆空。 在禅宗看来,普通的心,因为有执著,要无念、无相、无住,期望身与心两空的境界。在日常生活中,“要行而行,要坐即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倡导“平常心是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在禅宗境界上,则有“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种意识层面的解放拓宽了艺术境界,直返生命的本源。“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5]禅宗的澄明之境界让世界万物成为自性的存在。禅宗的思维也是彻底的还原之维,“舍弃一切先入之见和一切有意识的目标,中止对某些功利的渴望,向未知、神秘的奇妙世界创造性的开拓,就是禅和艺术散发出的诱人魅力之一。”[6]他消解了宗法的两端,却真正敞开了艺术。
中国艺术家总能穿越宗法,寻找到一方自由的天地。如果说宗法是中国艺术家无法摆脱的生存的土壤的话,那么艺术与禅宗则是在这个土壤上为其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中国杰出的诗人、画家始终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徘徊。苏轼是其代表。“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在《前赤壁赋》中,更是独享清风明月,饮酒赋诗,纵论英雄。在水与月中领悟天地之变。“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时间、空间的延展和消解中,在生命本源的复现中,显现了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绘画汇入了禅宗意识。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提出‘三远’即高远、平远和深远”。三远的构图方式,把视觉转化到画面之外,引向远,引向画面的虚无。禅宗则通过“远”来向无限延伸,然后返归自心。马远的《寒江独钓》表现了那种玄远的禅宗意趣。在境界的拓展中还原自性。“唐代绘画实践的不断深入,引导着人们的绘画艺术思想的深入。更由于唐代佛学思想的兴盛,般若学思辨方式融入绘画的思想中,如前述之实相非相之论: 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悟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待到要寻个休息处,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这种思辨方式,在山水画创作中,即画家在山水面前的‘震动’、‘感悟’和‘立意’的艺术表现,往往有不同寻常的地方。”[7]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的雪中芭蕉感受到的不是主体心灵的失落,也不是超越精神的神明,而是一种独特的心灵领悟。魏晋的“以佛对山水”和唐代的“以法眼观之”的雪中芭蕉,形与神之间,神才真正成为心灵表现的主体。这也是禅宗中“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禅宗最宗超越于形式,也最终穿越宗法,成为个体心灵自性的表达,最终开拓了艺术的表现空间。
结语
宗法在社会历史中形成,并渗入中国人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是中国艺术的主脉。这在中国戏曲、年画、民间文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但是,中国艺术作为人最自由的情感形式,在宗法的基点上,寻找腾飞的翅膀。在原点追寻与外来给养的双重滋润下,从而穿越宗法,谱写出光辉而灵动的艺术篇章,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人的自由精神。
艺术当以生命为依托,中国艺术思想史是艺术与宗法博弈的历史。在生命的还原、澄明中,艺术成为自由、情性的艺术。
[1][7]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1,176.
[2][3]苏桂宁.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M].上海:三联书店.40.
[4]张节末.禅宗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4.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
[6]钱正坤.禅宗与艺术[J].美术研究.1986(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