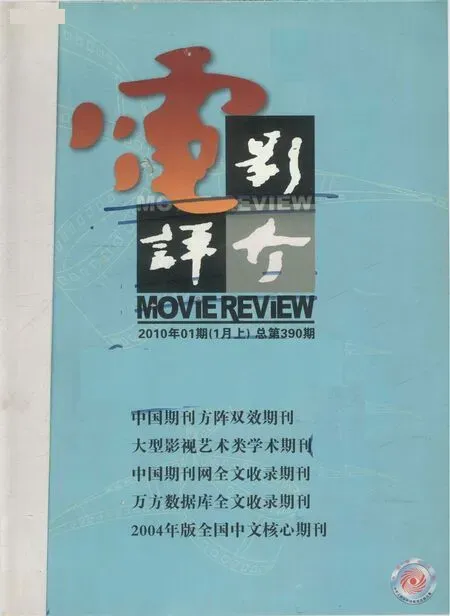黄嘉——略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一种基督教本土化的现象
2010-11-16刘芳
黄嘉略,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1679年,其父黄保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黄嘉略幼年跟随法国传教士李裴理和梁宏仁学习基督教教义和拉丁文,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1695年以后,黄就在各地游历,几乎走遍全国。1701年,法国外方传道会在华传教士推派梁宏仁赴罗马,向教皇汇报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情况。而黄又巧遇恩师梁宏仁,黄嘉略就追随着他,一起到罗马谒见教皇。后来他一直就居住在欧洲,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一、黄嘉略在礼仪之争的活动和态度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中一件重大事件,其延续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都堪称空前绝后。我在这里不打算对这个事件做全面的评述,只想简单的介绍一下,便于了解黄嘉略跟随梁宏仁去往欧洲谒见教皇时候的背景。
“礼仪之争”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有葡萄牙和法国在亚洲扩张上的对抗,也在天主教各个教会之间历来不和而造成的恩怨,更有在如何执行基督教教义认识上的差别,这些矛盾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中,称为“中国礼仪之争”。举行特定的仪式祭祀孔子,祖先和天地,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传统,这有着复杂的人文因素,就其内涵来说,是儒家思想的外化,早期的耶稣会在和中国民众的接触中,特别是在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往中,了解到敬孔和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组成部分,基督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就必须尊重中国人的这个习俗,否则难以争取信徒,葬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礼仪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中国信徒参加敬孔和祭祖的仪式。但是后来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认为允许中国人参加这些“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仪式,必然危及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因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场争论甚至到了罗马教廷,巴黎外方传教会梁宏仁神甫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派往罗马,处理礼仪之争事宜,争取教廷禁止中国“中国礼仪”。
黄嘉略跟随梁宏仁向教廷进行申述和交涉,在罗马度过了三年的时间,一直到1705年底才从罗马返回巴黎。关于黄嘉略在礼仪之争的活动也主要在这个时期。今天我们唯一依靠的史料就是他在罗马的日记。黄嘉略作为梁宏仁的随从,他们的活动当然和完全受到梁宏仁的支配,而梁宏仁来到罗马的使命就“礼仪之争”向教廷报告,争取教廷发布一项公告,谴责耶稣会,支持巴黎外方传教会。尽管由于身份和地位上的限制,黄嘉略只有帮助梁宏仁做一些杂事,并没有直接参与向教廷申诉和众多的教会人士接触磋商,然而对于每天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他还是很关心的,对于“礼仪之争”,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我们看来,他的这些看法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知道,黄嘉略从小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跟随李裴理和梁宏仁学习文化和教义,没有接受正规的中国传统教育,在很长的时间中甚至没有生活在中国人中间,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可想而知,何况跟随着的两位都是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他们的引导和教育下,很难指望黄嘉略能在“礼仪之争”中站在耶稣会的立场上,他在礼仪之争中,没有直接发表看法,但是在日记中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礼仪的鄙夷和不屑。
1705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将西方的基督教圣徒和中国的圣人做了比较,并依据基督教教义,指责中国的圣贤只知道追求今世的虚荣和欢乐,丝毫不考虑死后是否享受天福,不懂得万物的真原,把父母和祖先当作天地的主宰来崇拜。他说“吾天主圣教之圣人,生平何其修德、谦让、爱人、识天地万物之主,导人行天国之路,明于众有死后天福永祸之赏罚,劝众居世宜轻世,而践一切世荣乐于足下,惟向身后天国之永福永业者也。岂同中国所谓之圣者,且不识天地万物之真原,又无道及身后之永报,及为善者之所由来,而为善之能力乃从谁乎,惟向今世虚荣暂乐,以父母祖先犹如天地万物之大主祀之。彼岂知吾天主圣教首钦爱上主,次孝爱父母之正理哉。”
1704年11月8日,他参观圣额我略堂,事后写下一段感想,通过中西追思亡人的对比,批评和嘲笑中国人祭祖习俗,言辞相当尖刻:“祈祷为已亡之父母亲戚等,追思教中先亡之瞻礼,乃西国上坟之日期。其瞻礼之前后日子,西国之大小男女老幼,皆往圣堂中祈祷,或点灯点腊之人往来不绝,极是好看,而乃正礼。非同吾中国,而两块禽兽之肉,呼神叫鬼祭之,亦不知其祖先归于何处,来于何处,祝祷又何人受人。呜呼!尚敢笑西国之人不知祖先,不敬神明祖先,不敬神明。以余见之,真可羞死。”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死既是永远,死不过是个转变,我们固然可以追述先人的德行,但是不能加以祭祀,偶像崇拜。看黄嘉略的几句话,反映了他在“礼仪之争”的态度和倾向,作为中国人,如此尖刻的批评中国的礼仪,使人了解到“礼仪之争”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基督教传行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和中国的基督化
从宗教传播来看,中国“礼仪之争”的爆发有着必然性,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本质上涉及一种宗教对外传播时,是如何对待本土文化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礼仪之争”有着和其他传教过程中的冲突的共同性。但是它又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卷入中国礼仪之争的传教士都试图认识了解中国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宗教还是伦理?另一方面这个又不是纯粹学术上的争论,里面还有世俗之争,利益之争,毫不宽容,争论的双方都希望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为自己的传教策略辩护。
中国传统是家本位的社会,一切的德行是以孝为根本的,祭祖、祀天、尊孔是中国文化最深层最主要的文化素质,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和宗教碰到这个根本问题必然产生冲突,基督教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强迫信徒放弃信仰和习俗,带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把东方看成蒙昧的地方,蔑视并粗暴对待中国文化,反对祭祖、祀天、尊孔,把这样的仪式当成异端和邪教,必然伤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试图和本土文化相适应,是传教士们一直探索的难题。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下,一方面宗教要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原味不变,但是宣传的同时,又要考虑如何把这个信仰传达到对方,又是一个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笔者认为中国化的问题,其一就是传教士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使得传教的方式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逐渐放弃原先所有的文化信仰,遵从基督教教义的过程,就是中国的基督化。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培养中国神职人员是在华欧洲传教士的主要工作。虽然大多数来华传教士都刻苦学习当地语言和习俗,研读中国经典,努力接近当地民众,但他们比较来自遥远的西方,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与中国人差别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习俗往往格格不入,面对森严的文化壁垒,传教士们认识到培养中国一批理解基督教教义精神,又在中国教徒中成长,讲流利的中国话,有着和当地人一样的面孔,熟悉工作地的文化和社会准则,对于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为主要的是,中国神职人员的存在的象征意义则更大,表明了中国是可以从内心上接受基督教的教义的。
黄嘉略就是之所以被梁宏仁所辛苦教育,当然也是希望他成为中国当地的神职人员,梁宏仁把黄嘉略带到欧洲,一方面是自己工作需要助手,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为了把他培养成合格的神职人员,以便他将来为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发展做努力,这一点黄嘉略自己也是非常清楚的,在《汉语语法》的序言谈到李裴理“把他托付给几位学识渊博的文人,让我学习各种知识,以便将来为传教事业服务”,其实在中国,黄嘉略就曾经为一个遭到丢弃的女婴临死前做了告解,履行神职义务。他谈到“那天我就在路边见一个被穷苦人家遗弃的女孩,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当我碰巧经过那里时,从她那微弱的哭声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连一刻都没有耽搁,立即跑去找水,给她擦洗干净。当我做好这一切,她便闭上了眼睛,平静地在上帝的怀里安睡了。”他完完全全是一个已经基督教化的中国人,他自小离家,四处闯荡,跟随传教士各地传教,可以说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传教事业。“礼仪之争”中站在基督教上的立场看中国礼仪,他的宗教感情远远高出他对自己的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黄嘉略和法国早期汉学》 许明龙 中华书局2004
[2]《中国天主教简史》 晏可佳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3]《中国宗教和基督教》秦思懿 孔汉思 三联书店1990
[4]《基督教教育和中国知识分子》 史静寰 王立新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5]《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 王志远主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6]《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赵殿红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7]《文化争议后的权利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 吴莉苇 《世界历史》 2004年第3期
[8]《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意]柯毅霖 《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9]《略论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冲突和适应》 陈建明 《宗教学研究》 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