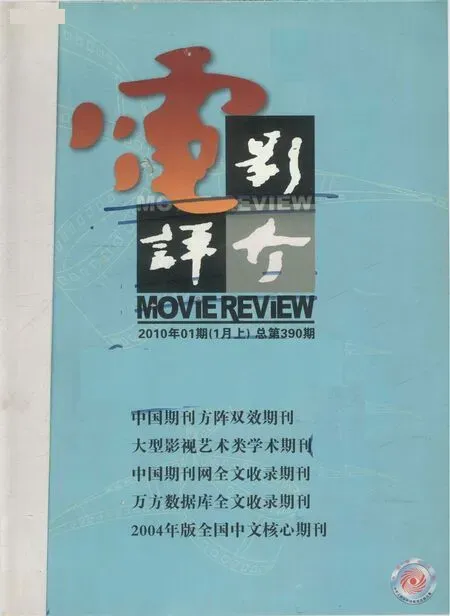诗经式的外交辞令
2010-11-16周晓伟
春秋之际,尽管礼崩乐坏,诸侯并起,但周王朝时期的道德、等级观念,特别是以《诗经》为典范的崇尚礼仪,忠君爱民的风尚仍然广泛影响着列国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反映在诸侯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语言上就张扬着《诗经》和谐典雅的特点。不仅引用《诗经》的数量和规模是先秦其他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而且承继诗教传统,温柔敦厚,在外交场合有时责之以大义,让对方知难而退,有时败不馁志,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同时又掌握分寸,婉转陈词,折服对方。
一、诗经式外交辞令的目的
1.对群体利益的维护
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使个人完全脱离集体,对群体利益的认同仍然作为一种道德层面的规范,指导着人们的言行要不偏离自己的本心和本性,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复杂化,各诸侯之间的外交活动也不再是一种仪式,而成了外交手段、政治头脑、说辩能力的综合运用,说服对方,使自己的国家转危为安,正因为如此在《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中渗透着一种恪尽职守,对国家忠贞的责任感,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诗》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到了流行的地步,如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七日不绝,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表现了为了国家利益舍生取义,不图名利的精神,又如宣公十五年,楚宋交兵,宋国外交使臣华元在国家危亡之际夜入楚营和子反讲和,言辞沉痛坦然,反映了先秦士人爱国忠君,把社稷兴盛视为己任,言谈辞令不仅引用了《诗》,还将《诗》承载的远古先民朴素爱国的精神加以申发。
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外交斗争异常激烈的春秋时代,外交士人面对的大多是君王、诸侯一类的权势角色,但是他们为了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经常引用《诗经》中的章句来明礼法仁义,提供立论根据,凭借卓越的辩才、文采,创造了中国修辞史上最为精彩的外交辞令艺术。
2.对德政的尊崇
《左传》中对“德”的认识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信仰、道德、行政诸方面的内容[1],内涵包括两部分,一是使人各得所需,各得其位[2],二是做事做得合适,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3]。这与《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观一脉相承,并在《左传》的外交辞令中辐射扩张为善政重教、尊贤爱民、明德慎罚等施政观。所谓“古之王者知命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4],因此在外交事务中有的体现为善政重教,如昭公七年楚国孟僖子大夫引用仲尼和《诗经》对简公的答对,阐发如果只依靠制度律令来行事,人就会变得狡诈,只有用美好的品德来感染人,用教化来引导人才能避免这种情况;有的体现为公平正义,办事讲究准则,如僖公九年齐侯伐晋,晋派使臣赂秦以求入,郤芮在回答秦伯时就阐释了安邦靠的是准则和标准并非国君。
二、诗经式外交辞令的语言特色
春秋士人在尚德崇礼的艺术化战争中,一面驾驭车马在战场上冲杀征讨,一面又保持着贵族的优雅风范,《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大义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各诸侯在外交场合的辞令大多以引诗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的外交场合贵族士人并没有引诗,但通过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诗”意,展现出士人们在诗意的外交活动中运用自己的智慧,展示着文质彬彬的风采和高雅淡远的艺术学养。
1.外交辞令的显性诗经味
据统计《左传》引《诗》数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达到了260多次,开创了著述引诗的先河,其中有100余处是外交辞令对《诗》的引用,共涉及《诗》篇目110多篇,涵盖了风雅颂的许多篇章,《假乐》、《荡》、《文王》等篇目词条还被多次引用,显示了“诗”风顽强的生命力。在引诗以微言相感的实践中,“歌诗必类”是最主要的原则,《左传•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对此杨伯峻先生的注解是:“必类者,一则须与舞相配,而尤重表达本人思想。”政治是一把双刃剑,要想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思想,首先必须非常清楚形势,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庄公六年,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由于不懂诗云:“本枝百世”的道理,没有考虑好“本”、“枝”的关系,不能因人成事,被卫侯杀害,为天下笑;其次还要具有良好的口才,处理外交事务,引诗譬喻,言谈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襄公三十一年就有一段叔向赞扬子产口才的话,所谓:“《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汉书•艺文志》也有:“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职,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可见在外交活动中,适当地引用《诗》对于完成使命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引诗的外交活动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主要的方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齐庄封好田而耆酒……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
在外交活动中,外交使臣们正如卢蒲葵所说巧妙地选取《诗》中和自己要求相合的诗句和对方沟通,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成公八年晋景公派韩穿赴鲁,命归还汶阳之田给齐国,季文子当即向韩穿指出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牺牲鲁国去取悦齐国的行为有失大国形象,并引《诗经•卫风•氓》加以佐证,不但让韩穿更加重视自己的话,而且不会损害对方的面子,讲究策略最终劝谏成功。类似更有趣的外交辞令发生在昭公元年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赋《瓠叶》、穆叔赋《鹊巢》、赵孟又赋《采蘩》、子皮赋《野有死麇》、赵孟赋《常棣》……士人们将赋诗作为外交手段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堪称礼乐文化下的一种外交典范。
2.外交辞令的隐性诗经影
春秋各国处于对外交事务的重视,纷纷选派优秀的人士来担任外交官,因此《左传》中的外交人物主要是王室、诸侯、卿大夫、士为代表的贵族,这些人学识渊博,擅长辞令,在外交场合代表着本国的形象,较之显性的引诗外交,他们的辞令一般“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 [5]含蓄委婉、和谐蕴藉,与《诗经》尚礼崇文的诗教传统如影随形,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左氏笔下的外交人物大都尚礼故文,称对方君主为“君”,称对方臣子为“子”,称对方的国家为“上国”、“大国”,称己方的对应称谓则为“寡君”、“下臣”、“外臣”、“小国”、“鄙邑”等,还使用诸如“敢”、“辱”、“惠”、“贱”、“不腆”等副词极大地显示了对对方尊重。同时言辞委婉含蓄,在忠实于本意的前提下把有很强的挑衅刺激的语词换成婉转的讳饰性词语,减少禁忌和莽撞,如成公二年齐侯来请战用“释憾”,昭公五年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用“息师”,昭公七年子产与韩宣子的对话中将公孙段的死说成“无禄”,有如哀公十七年会齐侯,只行拜见之礼,并解释为“非天子,无所稽首”来避免尴尬,让对方知难而退。这样的外交辞令不仅委婉谦恭、得体和谐,而且刚柔相济、寓意深刻,是《左传》外交辞令诗经式特征的明显例证。
葛洪曾经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6],这番评价反映了《诗》语言自然浑成、清水芙蓉而又脍炙人口的特点,而《左传》外交辞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对其中的优秀诗句进行加工,形成稳定且合韵的四字固定词组,音韵和谐又朗朗上口,如行将就木、呼庚呼癸、食毛践土、割臂之盟、敬谢不敏等,另外从杨伯峻和徐提《〈左传〉词典》里检索到与外交辞令有关的四字成语也有余条。从语言的外在形式来看,《左传》的语言如出一辙的使用了很多叠音字和连绵词,或描写容状,或增强语气[7],把语言的音乐性和形象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融融、穆穆、庸庸、祗祗、仇雠、魍魉等,同时《左传》外交辞令还将《诗经》语言中的多种修辞方式综合运用,诸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比、对偶、衬托、排比、层叠、反问和设问、反语、摹状、拟声等,交错使用,互相衬补,浑然一体,如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这些四字穷理,一言穷形的外交辞令,以传神的笔墨把当时精彩的外交言语记录了下来,连孔子也大加赞赏:“……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逻辑谨严、道理明晰、辞采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
三、结语:
春秋虽处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时期,但是贵族士人们仍然保留着先秦时期精致、优雅、细腻的文化底蕴,在危机四伏、变化莫测的外交舞台上,各国名士指点江山,在互相揖让进退之间,在言谈举止的细微之中,显示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熏陶下的优雅和谐,在这种特殊的场合,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维护国家利益的博弈被演绎得如梦如幻,透辟如利镞穿胄,凛冽如惊沙入面,在文学与艺术上大大胜出《战国策》,高踞于先秦散文的顶峰,使人闻之则思慕不已。
[1]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8
[2]南怀瑾,历史的经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67
[3]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4
[4]左丘明,《左传•文公六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7月
[6]诸子集成之抱朴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7]沈祥源。古代汉语[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