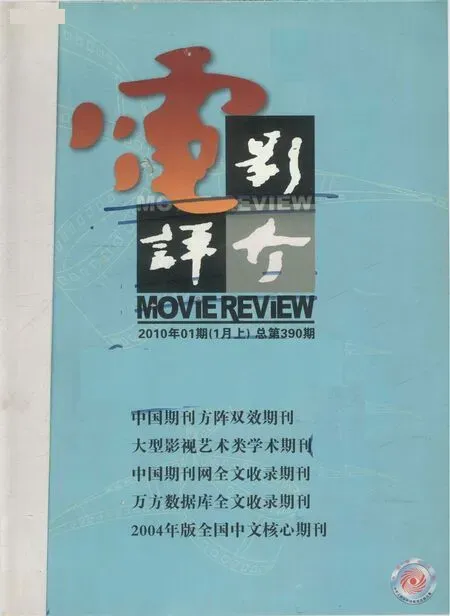虽美非秀:中国动画角色形象塑造的当代遗落
2010-11-16曹汝平
虚拟的角色形象是动画艺术中有生命的“演员”。一部动画影片可以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不能缺少生动的角色形象,它决定着动画艺术的成败。“秀”美的动画角色是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优秀动画影片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在动画艺术中的现代表述。“秀”美观强调心物、情理、刚柔之间相济相成的关系,更强调中和、温柔敦厚的诗学精神。
一
在词源学中,“秀”意味着成熟,指植物开花、抽穗与结果。徐锴《说文解字》曰:“禾实也,有实之象下垂也。”《尔雅•释草》中云:“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从“秀”的原意上,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引申出两层意思。一是“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独拔”,即卓绝、超越一般,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能“动心惊耳,逸响笙匏”;二是“譬卉木之耀英华”,或“英华曜树”,言艺术形象之秀丽或伟丽。[1]
从《文心雕龙•隐秀》[2]之秀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另外两层意思。其一,“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该句以形象的语言阐释“秀”之旨意,对人的视觉与心灵都有比较强烈的冲击力,是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进行的直观而动态地描写。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作品《神奈川巨浪》中高扬的浪涛给“波起辞间”以很好的视觉参照和精神比拟。其二,是“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的“自然会妙”。《隐秀》篇崇尚自然本体的美,主张“思合而自逢”,不刻意苛求;但并非全然否定人工美,“雕削取巧”固不可取,“润色取美”还是必要的,只要体现出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又不显露太过的人工痕迹,艺术作品依旧是自然本色。
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出“秀”的审美内涵及其意义。“秀”是美的,是别于一般的“自然会妙”的美;有时它还涵括了“丑”的意味,如郑板桥在论石时说:“丑而雄,丑而秀”[3]。但“美”不一定“秀”,华而不实,漂亮而缺乏涵养的人就不“秀”。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秀重在艺术的想象与内涵,除指涉形象自然、灵韵外,还指喻人之品德美好。《文心雕龙•原道》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礼记•礼运》亦曰:“五行之秀气也”;段玉裁则将其与“采”联系起来,引申为“俊秀、秀杰”[4]。可见,秀源于美,但又修饰并深化着美。
概言之,“秀”有三重意义。首先,从本义上看,由“秀”而生的优秀、卓越之意,是文艺创作者源始的内蕴存在,既是说,民族的审美积淀是创作者再创造的源泉。刘勰譬之为“英华曜树”,生动而形象。其次,“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上一个波谷积蓄着下一个波峰生成的力量,“秀”只有在动态中达到巅峰状态才能获得其价值。因此“秀”并非只是静态的外在美,而且还是一种动态的意蕴美,其中暗含着推动审美生成的力量。《诗经•卫风》中的名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就是写人物的形象美,但后两句是由静态转向动态,效果迥殊。再者,“秀”的审美价值还表现为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需要人们以美的意识来揣度。《易》中有“贲文穷白,贵乎反本”之语,《文心雕龙•情采》亦有“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贲”就是修饰,贲的卦象从文饰发展到顶点,又返回到本色。这是由人工美再趋于“自然会妙”后的境界,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艺术创作方面的理想表达。
二
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动画影片塑造出来的“秀”美角色形象,与创作主体及角色价值的动态生成密切关联。
首先,“秀”美的动画角色的实现,与创作主体在艺术及人格上的涵养相关。创作主体承继的文化精神作用于心灵,又映射到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去。中国文艺创作的传统根植于儒家礼乐思想,又以道、禅精神为策应与辅助,并从生活中逐渐融入到民族的血液里,规定着人们的外部行为。总体来看,以“中国学派”为标志的中国动画之所以能够取得曾经的辉煌,在于动画艺术家们能够以“淳厚和淡”为心胸,以“淡漠功利”为基质,以“情真意切”为本性,以“风致神韵”为趣尚,在于“致力于从审美意识上来把握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在影片中渗透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神韵”[5]。显然,这些民族的文化基因造就了艺术家的人格,也成就了“中国学派”的灿烂。民族的审美底蕴,表现在动画艺术创作者的身上,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很“中国”的动画艺术。具体到角色形象,虽然其造型或精致,或巧丽,或清美,要皆疏朗明快,令人悦目赏心,“呈现‘中国学派’造型上的意象特征”[6],但是它们的精神和气质是一致的,显出“秀”美的本质特征。
其次,“秀”美的角色形象是动画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在动画创作中,艺术性的想象力往往天马行空,人们的思维并不局限于常理之中。围绕着艺术性,动画艺术家们动足了脑筋,进行了大胆地想象和夸张。《天书奇谭》中的袁公为了能将“天书”授之于人并造福天下,用八卦炉将天鹅蛋炼成一枚孕育着人之胚胎的蛋。这一过程将袁公的“才秀”点染出来,为角色最后舍己为人的人格形象做好了铺垫。在《有求必应》中,土地公公居然能够将月亮用拐杖勾下来,然后当洒水壶使用。这样的设定充分显示了动画创作者卓越、智慧的想象力。
艺术性的创造力也显而易见。当哪咤重生并与师父相见时,为了达到特殊的效果与神奇的气氛,更好地渲染强烈的悲愤色彩,影片采用了高难度的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圈来处理。这样的处理使得哪吒这一小英雄的形象更加“立体化”,而动画艺术家们挑战技术高峰的创造力也铸就了哪咤正义而坚强的完美形象。进言之,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圈象征着一个“圆”,它首先意味着哪咤的“回归”——冲决礼与情的约束,“凤凰涅磐”后重新回到人性的自由状态,一种角色的能力与品格都已成长了的境界。至此,哪吒由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与邪恶势力斗争的真正的战士。其次表现出一种“‘主观的’运动——要求观众来参与完成的运动——经常跟客观的运动同时并存。每当摄影机或俯或仰,或环视或推拉,以引起观众对活动中的和不动的物象的注意时,观众便不得不与摄影机化为一体,随同起止。[7]”观众与摄影机化为一体后的“主观的”运动,就是动画艺术家们以观众为中心的创造性的表现。他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还原着观众的眼睛,还原着观众成长的心灵。
第三,中国动画角色的“秀”美不是一种纯然现成的价值存在,它总是要从剧情发展的状态中脱颖而出,将人类的情感通过虚拟的角色形象和情景传达给观众,或意味深长,或诙谐幽默。《山水情》中的老琴师如风飘去,少年登高寻觅,斯人渐行渐远终不见,心生无限离愁,遂抚琴弹奏。这是一首优美的、如诉如泣的“山水情”,是少年此时心境的写照:渡口边,老琴师疾病突发,少年倾力相助;秋去夏又来,一年中,师生情谊似山高如水长;临别离,山呜咽,水哭泣,琴有声,情无涯,此生何时再相逢?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动画艺术家以小观大,虽然描写的是师生情谊,但折射出的是人与人之间心无间隙的伟大。渡口少年有一颗助人与感恩的心,而老琴师有一颗感恩与惜才的心,当这两种心灵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时,就成为最宝贵的财富。又如《三个和尚》,虽然在挑水的问题上有过矛盾,但在危险来临时,大伙还是能够摈弃前嫌,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在冲突中,小和尚的本性尤为真实。当与大和尚为抬水意见不合时,小和尚还不忘回头对大和尚做个鬼脸,加上声效,让人对他的动作忍俊不禁,妙趣横生。可见,真实善良的心灵是“秀”美价值形成的主导因素,而人性之“秀”还需要在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才能最终完成并见出价值。这是“秀”美的角色本身及其属性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
最后,“秀”美的动画角色作为一种审美的客体存在,其价值的实现还需要表现为与观众之间产生的新的价值关系。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8]。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画角色,还是创作者,单方面都不能构成价值关系。对角色而言,其价值大小,除决定于创作者的塑造外,还要依赖于观众的需要。“英锐者抱秀而心悦”,对喜欢中国动画艺术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从民族艺术中生发的、具有超凡想象力的角色形象。当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哪咤闹海》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后,座无虚席的大厅内掌声雷动,观众报以长时间的欢呼。影片以鲜明的角色形象、独特的民族风格、严谨的叙事结构、丰富的电影手法取得了艺术性和娱乐性双丰收的巨大成功,成为中国动画艺术史上“既叫好又叫座”的动画影片。迪斯尼说:“无论善和恶,所有伟大戏剧作品中的各类角色,都必须具有可信的人性。[9]”哪咤虽然集人、神、孩子、英雄的完美形象于一身,但在褪去神的外衣后,他正义、坚强、舍己为人的人性光辉更让观众为之动容。
三
以上述“秀”美的动画角色为参照,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今天的角色形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动画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在于中国动画只有艺术性,缺少应有的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商业化、产业化。诚然,中国动画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动画长片,众多的艺术动画短片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口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并仿效美、日动画商业运作模式提出了“后期市场开发”、“衍生产品”等概念。但这种观点也造成了一种后果:将动画首先当作市场中的商品而不是艺术,导致动画影片艺术性的严重缺失;最关键的是,导致动画创作者失去了一颗平常心,人们心中的那杆艺术与金钱之秤失去了平衡,从而丧失了原本独特、丰富而真挚的情感。《宝莲灯》的导演常光希客观地承认:“如果说影片取得成功的话,应该说首先是市场运作的成功,该片市场运作的价值比影片本身的艺术性更大一些。我们在这部影片中尽可能的将现代观众所喜欢的创作手段都运用进去了,而谈艺术功力确实与《大闹天宫》那样的经典之作有相当的距离。《宝莲灯》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人文精神的表现上都比较肤浅。[10]”相应的,角色形象因为要“将现代观众所喜欢的”东西塑造进去,而多出许多模仿美、日动画角色的痕迹,原本充满东方神韵的动画角色不复存在。所谓“现代观众所喜欢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和思考的话题,可想而知,由此萌生的角色形象的审美价值又有几何。这一类“模仿秀”,从一般的欣赏角度看,够“酷”、“帅呆了”、很“Q”,但是,美则美矣,非秀也!笔者以为,它们的出现本非常光希等动画导演内心深处理想的角色形象,这是急促的“产业化”呼声迫使他们“随大流”仓促上阵的结果。
具体来说,在上述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动画角色至少存在以下三点问题:
第一,原创精神的遗落。动画角色是创作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物化成果,角色应具备“独拔”而“英华曜树”的特征。“源始的内蕴存在”强调的就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创造出有特色的艺术作品。反观今天的中国动画,人们从影片中看到的多是洋娃娃,仅从造型上看,观众无法一眼看出其中的差异,如果是外语配音,动画角色就是迪斯尼或日式动画人物的翻版,整个动画影片也就是一部地道的国外动画。有人认为当代动画观众的审美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民族化”已经过时了,中国动画应该跟上时代潮流,走“国际化”的路子。其实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批判过,“可是有人说:‘民族形式体现在古代题材、古代人物身上当然容易,现代题材、现代人物就不好办;动物就更难了。因为外国的小白兔和中国的小白兔到底没有多大区别。’这也难,那也难,说来说去,就是搞外国形式不难,外国东西脑子里有的是,要啥有啥。个别同志甚至把外国的某些作品当成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模仿,因袭。[11]”笔者并非厚古薄今,也不排斥国际风格,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泥古不化有之,融会贯通亦有之。有价值的模仿是艺术成长阶段的必经之路,但是“艺术应当力求形似的是对象的某些东西而非全部”[12],全盘模仿就是抄袭。在特定时期我们尚可接受洋娃娃式的动画角色,但在产业化阶段,即动画艺术的成熟阶段还能接受吗?
第二,角色底蕴的遗落。就动画艺术的本性而言,其中的角色性格并不需要很复杂,相反,单纯、执著并让角色具备可信的人性就足够了。至于角色“秀”美形象的最终显现,如前所言,是故事发展到高潮、与其他角色乃至观众建立关系后才实现的目标。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协助下,民族的、身边的、有亲和力的故事让人们对真挚、友爱的人性情感更加专注、向往。但被商业武装起来的头脑容不得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浅薄的、不着边际的、专以噱头、搞怪、贫嘴、打斗为首要效果的当代中国动画频繁的出现在观众面前。从蓝猫、喜羊羊到麦兜,也还只停留在商业的运作上,蓝猫、喜羊羊、麦兜能给人们特别是人们留下什么?无疑,这仍然在重蹈汉代《淮南子•说山训》中所说的覆辙:“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也许,《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导演丹尼•博伊尔的话对今天中国动画角色的内涵塑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说:“艺术家必须对怎样做简单的电影心中有数。比如在中国,只要找到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有人性的故事,拍出大变革环境中小人物的命运,就是有价值的电影。[13]”现在看来,民族的、生活的“内蕴存在”是中国动画艺术及其角色“传神写照”的根本。我们只能乐观地看待今天的中国动画,前进的旅途中总有风和雨。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第三,自然美的遗落。动画角色,不管是正面抑或反面,都应该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在角色造型及性格塑造上都不应该做作。刘勰说:“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遵循这样的思想,“秀”美的动画角色形象才能呈现出如清水芙蓉般天然去雕饰的美。观众很容易发现,当代中国动画中的角色形象都在刻意模仿所谓的“时尚美”,要么浓眉大眼,动则一米八几,要么大眼睛、瓜子脸,魔鬼身材,且一律成人套路,扮酷、性感、嗲声嗲气几成通病,角色塑造陷入模式化的“雕削取巧”的地步。找寻不到中国人自己的本色,将永远走不出刻意模仿的怪圈。以《我为歌狂》为代表的大部分动画影片,角色形象“美”吗?产业化成形了吗?可见,一味地迎合市场,急功近利,所丢失的不只是“秀”美的动画角色,反倒连市场也有失去的可能。与其如此,还不如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并展示它的美。席勒说:“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14]”用童稚天真的心灵去感悟世界,用童心和童趣去描绘世界,心态年轻些,想象丰富些,多些童心、灵气、锐气,多些悠游与妙趣精神,少些人云亦云,少些做作,少些深沉,总之少些成人化的色彩。这样,即使角色个性十足,游走于正、邪两极,也能让人感觉他的可爱;即使是一个单纯而有趣的人物,他不甘寂寞的形象,本身就能演绎许多愉人性情的故事。
本文所论的“秀”美角色及其塑造源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种从外在形貌到内在的精神气质、从矛盾冲突到形象的生命力中彰显出的民族审美意识。毋庸讳言,“秀”美远不能涵盖中国动画艺术中优秀的动画角色形象,本文所列举的部分“秀”美的角色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未必合乎今天动画观众的欣赏口味,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并把握的是“秀”美的美学内涵与民族认同。或许,古典的诗学精神更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当代动画问题的思考。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奇秀和美—中国动画艺术的基本美学问题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70736)阶段性成果。
[1]詹锳.《文心雕龙》的“隐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24-36.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篇、句均出自该书.
[3](清)郑板桥.吴泽顺编注.郑板桥集•题画.长沙:岳麓书社.2002.345.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20.
[5]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2.
[6]尹岩.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当代电影.1988(6):71-79.
[7](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4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06.
[9]转引自:周鲒.动画电影分析.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267.
[10]马欣.对中国动画片民族化的反思.美术.2003(7):120-124.
[11]特伟.创造民族的美术电影.美术.1960(3):50-52.
[12](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
[13]宁波日报•文体新闻.2009年6月19日.A8版.
[14]席勒.信仰的话.转引自: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1872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