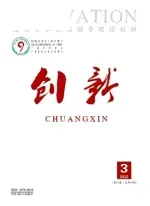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2010-11-12李国璋谢艳丽
李国璋 , 谢艳丽
(1.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 兰州 730000)
(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00)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李国璋1, 谢艳丽2
(1.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 兰州 730000)
(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00)
分阶段考察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首先利用传统的份额—转换法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考察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接着引入资本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充分考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又进一步考察在Verdoorn效应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劳动转移和资本转移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劳动转移一直存在“结构红利”现象,资本转移效应在近些年才开始出现“结构红利”现象;与结构效应相比,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产业结构变动;生产率增长;结构红利假说;Verdoorn效应
生产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①经济学中,早期人们主要研究单要素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后期主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克拉克以及库茨涅茨等早期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进行研究,得出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库茨涅茨(1979)认为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流动,不可能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以及生产率增长速度,当要素由低生产率水平向高生产率水平的部门或者由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流动时候,就会促进经济总体生产率的提高(Peneder,2002)这种基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即是“结构红利假说”。
针对这一假说,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
然而,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效应的研究中,有的没有考虑资本要素转移的效应,有的没有考虑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Verdoorn弹性值而低估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了弥补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分阶段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首先利用传统的份额—转换法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考察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接着引入资本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充分考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在Verdoorn效应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一、理论框架
(一)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模型
份额—转换法(Shifte-share Analysis)常被用来研究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该方法最早由Fabricant(1942)提出,这种方法最先认为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由两部分原因引起的: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的流动。


根据公式(1),可以推知T时期总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于0期的增长率为:

公式(2)分解成如下三项:
(2)式第一项被称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static shift effect),它度量的是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即由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生产率的提升。如果初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的行业吸收了更多的劳动,提高了自身的劳动份额,则该项符号为正,这种情况称为结构红利假说:

第二项表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dynamic shift effect),衡量的是劳动向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快的部门转移对总体生产率的影响。如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份额同时增加,该项为正;反之,如果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劳动份额减少,或者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的份额劳动份额减少,此时的情况为结构负利假说:

第三项表示生产率增长效应(within-growth effect),它是由各部门自身由于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引起的劳动生生产率的增长。
(二)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由于劳动生产率只涉及到劳动要素,因此采用传统的份额—转移方法只反映了劳动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为了同时反映劳动和资本要素转移对生产率的影响,在这部分利用Syrquin(1984)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基本方法是对照总量水平的TFP增长率和部门水平的TFP增长率的差异。利用C-D函数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和技术进步中性的可微函数,部门产出的增长率表示为:

总产出增长率也可以用部门的变量来表示:

A表示总量水平的TFP,按照Syrquin(1984)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总量水平的TFP增长率减去部门水平的TFP增长率加权值,得到为总体结构变迁效应(Total Reallocation Effect),具体表示如下:

Timmer和Szirmal认为常用的份额—转换方法在估算结构变动时候没有考虑不同部门的Verdoorn效应,即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当要素流向具有更高的Verdoorn值的部门时候,会促进生产率的增加,反之,则相反。因此,忽略Verdoorn效应的话会低估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Timmer和Szirmal将额外生产率的增长归结为结构变动,考虑Verdoorn效应对传统的份额—转换方法进行修正如下:

首先,为了同时考察资本和劳动要素,采用TFP代替劳动生产率来分析:


由方程(12)和(11)看出,方程两边都含有产出变量,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伪回归问题,Mccombie和De Ridder(1984)建议用以下回归模型:


然后,为了得到各个部门的Verdoorn弹性值构建以下模型:我们分别对三次产业利用(13)模型回归求出各自的Verdoorn弹性值。
二、数据说明及其处理
本文样本是1978~200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情况,三次产业的产值换算为1978年可比的GDP表示、就业人数采用三次产业年末就业人数,数据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产业的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数据来源于干春晖、郑若谷(2009)①。
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可以通过统计回归的方法直接估算,也可以通过产出弹性的公式计算(是资本产出弹性,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得到(刘伟、张辉,2008)。要素产出弹性的方法各有利弊,我们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估算弹性系数,采用传统的索罗余值方法测算出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方法最早由索罗(1957)提出,基本思想是用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称为生产函数法。这种方法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技术中性技术进步。我们采用常用的C-D函数:

Y为产出,Kt、Lt分别为t期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分别为平均劳动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产出份额。A是我们所需要的全要素生产率。
对式(14)取对自然对数,生产函数可以变形为:

根据(15)式可以计算出我国以及各产业的1978~20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三、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按照Peneder(2002)的解释,结构红利假说成立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部门之间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存在差异和由此导致的投入要素在部门之间发生转移,由此存在要素份额的相对变动。
因此,我们先考察我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
从图1看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最明显,第一产业比较缓慢。同期相比,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最小。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自1991年以后变得明显,特别是最近几年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

图1 1978~200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从图2看出,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呈现不同的变动状况,第一产业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呈现上升的趋势。相对第二产业来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于1995年超过第二产业,对比说明从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主要进入到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图2 1978~2006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从以上分析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生产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及劳动力要素不断的发生转移,满足结构红利假说的前提条件。那么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否就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如果存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的影响有多大?下面首先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考察结构变动的影响,然后加入资本要素的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解,考虑劳动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进一步考察在Verdoorn效应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四、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为了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阶段特征,我们根据(3)式分时期计算出我国三次产业变动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以及内部生产率增长效应(见表1)。

表1 我国1978~2006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解
从表1看出,总体上结构变迁效应都大于0,一方面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即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带动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动态转移效应都大于0,表明劳动要素在向生产率水平高的部门转移的同时,也向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转移。纵向来看,不同阶段上结构变迁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静态转移效应逐渐减弱,而动态转移效应微弱增强至第三个阶段超过静态转移效应,内部增长效应一直呈现明显的增强的趋势。横向对比来看,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小于同期的内部增长效应。以上说明了结构变迁效应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的贡献,小于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而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的。

表2 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①结构变迁的贡献率为结构变迁效应值占劳动生产率的比例。
表2是对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的分解。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的计算,同样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依赖于产业内部增长效应,即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分析
我们通过(14)和(15)式计算出我国以及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然后利用(8)式计算出结构变迁效应即TRE的值(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同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一样,产业结构变动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不同时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同。纵向对比,结构变迁的影响在增强,其中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增强之后在第三个阶段减弱,而资本转移效应与其相反,由前两个阶段的“结构负利”现象在第三个阶段消失,开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干春晖、郑若谷(2009)研究一致。横向对比来看,总体来看,各阶段结构变迁效应均小于同期产业内部增长效应,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

表3 1978~2006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
在产业结构变迁内部,从劳动力转移效应和资本转移效应对比分析来看,前两个阶段劳动力转移效应大于同期资本转移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存在“结构负利”现象,与第三个阶段,资本转移效应才出现“结构红利”现象并超过劳动力转移效应。针对此现象干春晖、郑若谷(2009)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远远强于资本的流动性。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跨部门跨地区流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率,而资本要素受政府的管治,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在市场制度确立前,外商直接投资很少,缺少资本,抑制了生产率的提高。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建立后,引进大量的外资,但政府对低行业进行了更大力度的扶持(蔡红艳等,2004),对生产率的提高不明显但较以前有所改善,也就降低了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随着加入WTO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资本转移效应对生产率的提高会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考虑Verdoorn效应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分解
根据Timmer和Szirmal的研究思路,我们分析包含Verdoorn效应时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为劳动生产率只包含劳动要素,所以我们选择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转移的影响。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前首先利用(13)式求出三次产业的Verdoorn弹性值(见表4)。

表4 三次产业Verdoorn弹性值
根据以上的三次产业Verdoorn弹性值,我们利用(10)式求出修正的结构效应值,如表5所示:

表5 考虑Verdoorn效应与未考虑Verdoorn效应下对TFP影响对比
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Verdoorn效应,产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影响都在增强,横向对比来看,在考虑Verdoorn效应下,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贡献均大于同期没有考虑Verdoorn效应下的贡献,例如1994~2006年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由1.5%增大为10.9%。这是因为不同产业的产出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同,要素转移对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度来看,结构变迁效应仍然占很小的比重,说明Verdoorn效应影响不大。
七、结 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间存在差别,并呈现加大的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小。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不断地变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逐渐上升。
第二,我国三次产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即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提高了总体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也向生产率增长率快的部门转移,共同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另外,与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比来看,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劳动要素转移在各阶段仍然存在“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要素转移在经历了“结构负利”现象后于第三个阶段开始出现“结构红利”现象。
第四,在考虑Verdoorn效应情况下,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未考虑Verdoorn效应下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但是与产业内部增长贡献相比,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产业内部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的变化。
此外,相比产业内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虽然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小,但仍然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因此,促进要素自由合理地流动显得颇为重要,而政府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国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本自由地合理的流动。
[1]M.Timmer,A.Szirmai.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Examined[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438-459.
[2]Michael Peneder.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14):427-448.
[3]Fagerberg.TechnologicalProgress,Structural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Compararative Study[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1).
[4]L.sing.Technological Progress,Progress,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South Korea[R].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2004.
[5]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10-11.
[6]干春晖,郑若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2):63.
[7]李小平,陈勇.劳动力流动、资本转移和生产率增长[J].统计研究,2007,(7):23-24.
[8]李小平,卢现祥.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J].世界经济,2007,(5):53-55.
[9]蔡红艳,阎庆民.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J].管理世界.2004,(10):79-80.
[10]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3):31-39.
[11]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62-68.
Effect Analysis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 Structure Chang in China
LI Guo-zhang XIE Yan-li
The article examined the contribution which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effect makes f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 phased.First of all,to use shift-share method to decompo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examining the elements of the shift o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follow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capital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the capital element of full study,as well as elements of the shift o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Further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Verdoorn effect.The articl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transfer of labor and capital transfer,“Structural-bonus hypothesis”phenomenon has always existed in the transfer of labor,while the“structural bonus”phenomenon in the effect of capital transfers began to appear in recent years;And compared with structural effects,the growth effects of intra-industry is the main sourc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structure change;productivity growth;structure—bonus hypothesis;verdoorn-effects
F121.3
A
1673-8616(2010)20-0029-05
2010-01-26
[责任编校:李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