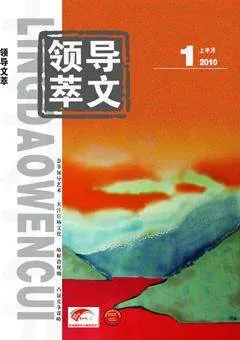醉眼看李白
2010-09-13车延高
□车延高
醉眼看李白
□车延高

李白对自己家世和出身很不负责,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作为生于其身后的研究者们,在文献不足,谱牒难求的境况下,当然只能以执著为针,靠想象作线,通过猜测和推断把相关的断点和印痕尽意地联补了。陈寅恪先生算一位高手,他于本世纪初一别常论地提出:李白“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因而“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詹英先生随之唱和,摆出了数则旁证。此论倘得成立,定是一轮冲击波。因为就此之后,李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名人中唯一的“归国华侨”和“混血儿”了。
堂堂“诗仙”居然也“出口转内销”,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种残酷和严峻。于是首先有杨宪益先生提出疑异,然后迭列一大堆的论据把李白定为“氐人”。其后有史学权威郭沫若先生开炮,出语几近于批判:“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文化?”“陈氏不加深思,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有意思的是郭老在对陈寅恪先生作了言词凿凿地否定之后,自己却未就此作出任何结论,这不知是权威的疏忽,还是权威的高明?
比如我吧,就认准了李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孙。我是从生存条件去联想和推断的。李白从25岁(开元十三年)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直到62岁(宝应元年)去世。将近40年间没回过故乡。此间李白如闲云野鹤一般漫游,不打工,不倒买倒卖商品,也不是签约作家,这儿“斗酒十千恣欢谑”;那儿“吴姬压酒劝客尝”,如此高消费,没有富厚的靠山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是难以支撑的。
那么靠山是谁?实力何来?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其父李客和坐庄于九江、三峡的兄弟。不错,李白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大富商,以其资产养上几十个闲人绝没问题。但李白不是闲人,而是“仙人”,他云游四方,一倾千觞。自从别家到辞世,再没回去过。再浓的亲情也疏远了,凭李白的傲骨,是绝不肯向家人伸手的。另外,限于当时的交通、邮递和货币流通条件,“五岳归来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家乡这根脐带。
那就要问了,李白到底倚靠什么打发了自己的一生呢?我想就是靠太宗曾侄孙和翰林待诏这两块金字招牌。之所以有此推断,是因为现实遇到的人和事给了我产生联想的土壤:而今确有这样的人,三杯酒下肚,吐出其姑父或姨父的大名,马上让人刮目相看。从此“一片明月照姑苏”,会有很多趋炎附势的新朋好友相邀,“一日三餐有鱼虾”,还有顾问、名誉董事长、兼职公关主任等有职无责的头衔和可观的灰色收入,倘若不赴,不吃、不受还是不给面子。您想想,封建王朝倒了已近百年,尚有遗风残存。那么在皇权至上,“相府丫环七品官”的年代里,自称是皇上“赐金放还”的李白游到哪里,打出太宗曾侄孙和翰林待诏的大旗,再有人从旁边添油加醋地随声附和,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威赫!另外,但凡能和诗仙李白接近的人一般也非等闲之辈,作为出类拔萃的人尖子,大都城府过人,目光长远,深谋远虑。他们知道官场有时就是赌场,政治这东西朝秦暮楚,变幻莫测,“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你今天看他虎落平阳被犬欺,说不定睡了一觉,皇帝想转了,龙颜大悦,能“赐金放还”,也能诏令即刻进京。那时人家就是东山再起别样天。这样想,现在破点财,摊入些许成本养一个闲人,既可以落下乐善好施的美名,又可以在两人之间奠定患难与共的友谊基础。到了他枯木逢春之时,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是有资格说说的。这种普遍性心态蔓延开来,就为落难不落架的李太白营造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的特定生存空间。这是李白的无形资产,是能产金子的金字招牌,是李白受用终身却未进工资档案的“声名禄”,李白生时,它比“诗仙”这顶桂冠有价值得多。作为书法和诗赋均有造诣的李白,既是书法名人,又是名人书法,出手一对条幅,或一篇碑颂,同样的尺幅,笔润可能就要高于别人很多倍,当中自然有隐性价值。
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懂得借用,却从不将此视为真正的财富,他仅只以此作为支撑生活和实现艺术创造的一种可用资本,一俟使命完成,他便委托历史,让有价值的永存,让无价值的毁灭。这既是李白安排的结局,也是李白对后人最清楚的交代。
(摘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