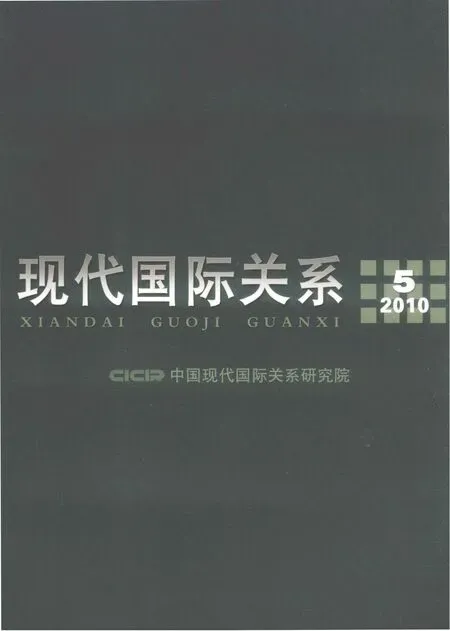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应
2010-09-08王石山
王石山 祖 强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应
王石山 祖 强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件大事就是对这场危机做出反应。随着危机已近探底,学者们对其反应的高潮已经过去,回顾、总结这一学术性事件有重要意义。本文评估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研究的反应速度、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学者们集中关注的问题领域、所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达成的共识和争论焦点,旨在揭示学界对这次危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以增强学界自我反思的自觉性。
中国 国际政治学界 国际金融危机 反应
[作者介绍]王石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祖强,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金融研究。
一、文献分析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件大事就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反应。笔者检索了2008年1月到2009年12月的国际政治学类核心期刊,发现13种期刊发表了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其累计发表论文101篇,其中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97篇,参与的学者82位。另外,有两种期刊举行了专题研讨会,五种期刊开设了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专题。①2008年11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3月《现代国际关系》等期刊分别组织国内著名学者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国际问题研究》在2009年第3期开设了“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问题专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专门设栏目讨论了“世界金融危机与俄罗斯”;《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设“金融危机与欧洲经济”研究专题。

表1 2008-2009年国际政治学类核心期刊关于金融危机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按照文章的性质,这101篇文章分为四类:(1)经验研究类,描述、介绍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现象,如利用既有的理论工具分析危机的原因、传导机制、各国的政策反应;(2)策论类,判断、预测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提出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3)理论分析类,对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学理性分析,旨在检讨既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工具的效用或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4)会议综述类,介绍学者对金融危机的基本观点、看法以及成果与不足。

表2 文献分类明细表
在上述四类文章中,经验研究类和策论类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达到84%,而理论分析类文章只占约5%。其原因可能是:第一,对策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危机的性质需要学者做出及时反应,来不及作更多的理论思考。第三,国内主流学者主要以参与研讨会的形式介入到本次反应中来(会议文章有31篇之多),而研讨会偏重于经验和策论研究。
从研究的反应速度来看,迅速、及时是其特点。在美国次贷危机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第4期的《现代国际关系》刊发了第一篇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的文章,即乔卫兵的《美国次贷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危机全面爆发两个月后即2008年11月——《世界经济与政治》首先组织了国内著名学者召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影响及其对策”专题研讨会。
从研究的广度来看,涉及到危机的不同方面,至少分析了39个议题①判断“集中”的标准是,至少有5位学者关注同一个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传导机制;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危机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危机对美国(国内政治、战略、霸权)的影响;中国与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与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的政策建议);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等等。

表3 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议题
从研究深度来看,理论分析类文章只有5篇,占5%,虽并不令人满意,但学者们却应用了多种理论分析工具。如:权力转移理论、币缘政治理论、霸权稳定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等。特别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对既有的理论工具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质疑,这典型地体现在保建云对“霸权稳定论”和罗小军对“权力转移”理论的实证分析②保建云认为,“霸权与国际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必然关系,霸权并不必然导致稳定,也不会必然导致非稳定”,从而修正了“霸权稳定论”。参见保建云:“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基于霸权收益计算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17-27页。罗小军反驳了权力转移必然导致战争的传统观点,提出通过“适应性变革”,权力可以和平转移的观点。见罗小军:“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金融危机与中国道路选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与中美关系”,《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31-55页。。而对本次金融危机反应的最大亮点就是王湘穗提出了“币缘政治”理论①王湘穗是少数几位持续研究本次金融危机的学者,并提出了“币缘政治”的新概念。见王湘穗的三篇文章:“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币缘秩序的解体与重构——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币权:世界政治的当代枢纽”,分别刊载在《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2009年第3期和第7期。。
根据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与危机相关议题的关注程度、危机与国际政治学本身的关系程度,笔者将具体分析最受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两大议题——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进一步评估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金融危机研究的质量。
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显然不仅仅一是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危机的政治责任和后危机时代的治理问题,因此它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爆发了一场王湘穗所称的“话语权的争夺”②王湘穗:“币缘秩序的解体与重构——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焦点”,《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第5-12页。。事实上,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热烈地参与到了这个议题的讨论中来——有12篇文章(占12%)直接或间接论述了金融危机的原因。学者们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危机的国际政治根源、危机的经济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揭露西方转嫁危机责任的企图。
第一,关于危机的国际政治根源,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美国霸权。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即“霸权透支说”和“霸权腐败说”。“霸权透支说”的逻辑是帝国过度扩张③[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叶自成认为,“美国霸权的过度透支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霸权泡沫助长了金融泡沫,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④叶自成:“金融危机的政治学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7-79页。“霸权腐败说”的逻辑是阿克顿式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不受约束的美元霸权是这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尚鸿认为,“美元霸权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祸首”,“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美元信用被无限放大,成为引爆此次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⑤尚鸿:“金融危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2-33页。同样,王湘穗也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国际政治原因是美元币权缺少制衡”⑥王湘穗:“币权:世界政治的当代枢纽”,《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7期,第1-8页。。
第二,关于危机的经济根源。学者们开列出的原因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资本主义模式说;资本家贪婪说;世界经济失衡说;监管不力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张世鹏认为,金融资本家的贪婪助长了危机的爆发(即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而“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是导致目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⑦张世鹏:“关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若干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80-93页。但是,张世鹏没有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金融危机首先发生在美国而没有发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此,余永定的回答是:“美国当前的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⑧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当代亚太》,2008年第5期,第14-32页。同样,王友明也认为,“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金融危机的根源”⑨王友明:“从金融危机看美式资本主义”,《国际问题研究》, 2009年第5期,第46-51页。。张明在分析美式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指出本次危机发生的三个具体原因:低利率造就的高房价、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监管缺位下的无节制金融创新⑩。
第三,对西方推卸责任的揭露。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就将危机归因于世界经济的失衡,欲将危机责任转嫁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2009年1月2日《金融时报》上专门发文,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中国的高顺差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美国新财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本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对此,彭龙和任康钰专门论述了“全球经济不平衡在次贷危机的发生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在分析了世界经济失衡长期存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他们明确指出,“世纪初以来存在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不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此次危机也有类似于历史上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缘于市场体系自身信用的崩溃,也是正常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而不应该归咎于国际收支问题”。①彭龙、任康钰:“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思考”,《国际论坛》,2009年第6期,第55-59页。
然而,确认谁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绝非最终目的。中国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等主要国际体系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②李杰:“从金融危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动向”,《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51页。,而“现存国际秩序没能充分反映新兴力量崛起的现实”③傅梦孜:“大危机催生新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19-21页。,因而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被排除在金融体系决策圈之外的现状,就成为中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关切。因此,学者们对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界定的作用,就不仅体现在治理危机的实用价值上,还体现在支持中国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上。总体而言,学界的话语辩护是成功的: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将中国的投票权从2.77%增加到4.42%,使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
三、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体系理论仍然是国际政治学最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本文将体系的单元和进程层次等因素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内,以便较全面地评估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因此,根据学者们对金融危机议题的关注程度,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行为体、国际合作与冲突、国际权力、国际格局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影响。国际政治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就这个议题而言,学者们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危机对两类不同行为体的影响上。一种观点认为,危机的爆发证明和加强了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地位的提升增加了国际治理的难度,因此应重申国家的作用。
王湘穗认为,世界正在进入“币缘政治”时代,国际政治行为体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全球化时代“币权”的诞生。“币权是核心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去控制及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权力。”这意味着,国家与金融机构是享有“币权”的两类不同主体。据此,王湘穗提出了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中枢——“金融-政治联合体”或叫“金融衍生品联合体”。在王湘穗看来,“作为币权的主体,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制衡力量”。④王湘穗:“币权:世界政治的当代枢纽”,《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7期,第1-8页。王雷、王公龙也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力图获取权力资源,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型权力单元。⑤王雷:“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100-110页;王公龙:“权力转移及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国际论坛》,2009年第4期,第1-5页。但是,朱锋从危机治理的角度质疑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金融危机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张,即认为在全球治理的模式下国家主权不再重要、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应该受到削弱”。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到来以及国际关系中再度严峻化的经济挑战并非因为非国家行为体,而是在于国家行为体。朱锋坚持认为,“促进世界繁荣与稳定的本质,还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如何推动国家职能与国际制度职能的相互协调”。⑥朱锋:“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年第12期,第15-19页。
表面上看,学者们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以王湘穗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了金融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更大作用,而以朱锋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国家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挑战。学者们对“危机背景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主要体现在,一些新概念、新视角的提出(如“币权”、“币缘政治”)和对既有理论解释力的质疑(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论证)。
第二,金融危机对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危机会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约而同地将G20的诞生看成是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如崔立如、陶坚等学者认为,“‘同舟共济’现已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共同应对当前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标志性语言”①崔立如:“全球化时代与国际秩序转变”,《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4期,第1-2页。陶坚:“观察当前国际危机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几个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7-8页。。事实上,“同舟共济”一词也是学者们在危机进行时分析问题的高频词汇(至少有三篇文章直接将该词作为标题,而在行文中,使用该词的作者至少有11位)。一些学者更是直接呼吁国际合作,以应对危机。②吕克俭:“中日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第153-156页。总体而言,更多的学者相信,在相互依赖时代和危机时期,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大于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其理由正如朱锋所说的:“大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和政治关系的相对成熟为合作解决危机提供了可能性……相互依赖所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为各国共度金融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真正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走向复苏和新的繁荣。”③朱锋:“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年第12期,第15-19页。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担心,危机会催生一些新的冲突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危机成本的转嫁问题④余维彬:“美国金融模式的不稳定性:基于次贷危机的反思”,《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92-108页。、发展模式之争⑤冯仲平:“欧洲借金融危机推动国际制度变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3-35页。、权力分配的变化要求改革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争议⑥王雷:“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100-110页。,等等。
第三,金融危机对国际权力分配的影响。在国际体系理论的视野下,讨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权力分配的影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了(如果衰落了,衰落的程度如何);(2)其他强国或国家集团(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的相对力量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增强或减弱的程度是否导致体系中的大国数目发生了变化。但是,学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质量、深度有限。
首先,学者们对各国力量变化的评估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在所有101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是对各国权力对比进行实证研究的,对各国权力变化的讨论主要分布在策论类文章中。这意味着,学者们对这个议题的反应主要出自主观的判断,因此有相当的不科学性。比如,以学者们普遍关心的两个议题⑦至少有7篇文章直接或间接讨论了美国衰落问题,11篇文章直接或间接讨论了“中国实力相对增强”问题。——“美国衰落”和“中国相对实力增强”——为例,大家对“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了,但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至多只是进入“衰弱时刻”,而非“衰弱时期”;中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增强了。然而,学者们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力参数支持上述结论,多数判断美国和中国实力的论点并非出自细致的经验实证研究类文章,而是出自主观性更强的策论类文章。因而,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基于具体数据的细致分析,不如说是基于主观直觉。这也意味着,关于美国衰落的争论和中国实力增强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因此,学界对“权力分配变化”的研究很难深入进行下去。
其次,因为学者们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的实力,因此他们的很多讨论在逻辑上也是不严密的,这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美国霸权的判断上。尽管学者们在美国金融霸权衰落⑧张世鹏:“关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若干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80-93页。陈文力:“金融危机视角下的世界经济版图”,《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第53-57页。和软实力受损⑨彭光谦:“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6-28页。这两点上达成了共识,但这些共识对于理解美国霸权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道理在于,美国权力是综合性的,并且就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而言,金融权力与软权力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美国权力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权力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军力差距仍在扩大。由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和软实力的衰落并不一定能得出“美国霸权衰落”的结论。这种逻辑上的归谬也典型地体现在对中国实力增强的判断上。
最后,学者们对国际权力分配的范围的关注不充分。大多数学者过于集中讨论中美实力的消长,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欧盟和日本的实力地位的影响”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得到学者们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在所有文章中,没有一篇讨论俄罗斯、欧盟和日本实力变化的专门文章。
由于学者们对“国际权力分配的变化”关注并未建立在严谨的经验实证分析之上,因此,对这个议题的研究也只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即学者们在“中美实力此消彼长”上达成了共识。这一结论直接关涉到学者怎样判断和分析“金融危机对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第四,金融危机对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关注的最重要的议题,以“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作为标题的文章就有15篇之多(占总量的15%)。从逻辑上讲,要分析“金融危机对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当下的权力转移是否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2)如果金融危机对权力转移产生了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从时间上看,当下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是肇始于本次金融危机。正如陈玉刚指出,“当前一轮关于国际权力转移的讨论并非完全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或者说在进入21世纪时就已经开始”①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28-34页。。罗小军也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权力转移的趋势”②罗小军:“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金融危机与中国道路选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与中美关系”,《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31-55页。。
从危机本身的性质看,这并不是一次能够摧毁现存国际体系的非常危机。赵晓春认为,“从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考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场危机究竟是一次性危机还是周期性危机”。他在辨析了两种不同性质危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是一场不足以导致国际体系发生根本转型的周期性危机。”③赵晓春:“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1-23页。朱锋则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了本次危机的性质。他认为,此次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性质截然不同,并且金融危机本身“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进程因素’,而不是‘结构因素’。‘进程因素’的演变可以造成结构性的、体系性的变化,但它不可能单独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体系发挥重大作用。”因此,“从中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将难以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造成实质性影响。”④朱锋:“金融危机与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4-26页。
综合分析学者们的判断,笔者认为,大多数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本次金融危机只是冷战后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一个干扰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对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一判断直接影响到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和分析。
尽管大多数学者在危机的性质和危机对国际格局冲击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危机本身并没有终结学界关于国际格局性质的分歧。事实上,金融危机加深了学者们的固有分歧——学者们对危机前国际格局的判断并不相同:他们分别以单极、多极化或一超多强定位当前的国际格局。由于对危机前国际格局的判断不同,因此,当学者们说“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大国数目未变、国际政治的组织原则未变)”时,他们谈论的“国际格局”的含义本身是不同的。如当李长久判断“国际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他实际上是指“‘一超多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⑤李长久:“国际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11-13页。。楚树龙也认为,“从国际格局的视角观察,金融危机没有、也不大可能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基本格局”⑥楚树龙:“金融危机与世界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9-11页。。这一观点得到了邵峰、徐进等学者的支持。⑦邵峰:“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程度到底有多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23-26页;徐进:“金融危机难以颠覆‘一超多强’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26-27页。同样是持“国际格局稳定论”,朱锋则坚持他的一贯观点,“美国的单极霸权仍然是稳定的”。显然,这两种“稳定”的含义不同。
与“国际格局稳定论”者相反的是“国际格局渐变论”,即金融危机加强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这种观点以崔立如为代表。他认为,“大危机造成多极格局不期而然”,新兴经济体成为一体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多极格局开始生成”①崔立如:“全球化时代与国际秩序转变”,《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4期,第1-2页。。王在邦也认为,“危机将促使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化,即发达国家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而新兴大国实力地位相对上升”②王在邦:“对金融危机催生世界新秩序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17-19页。这一观点得到了秦亚青、赵晓春、王湘穗的支持。③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赵晓春:“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1-23页;王湘穗:“未来趋向:多元货币体系与多强政治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8-30页。
与上述两种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国际格局质变论”。李永辉认为,“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④李永辉:“金融危机、国际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7-38页。。陈玉刚比李永辉走得更远,他在介绍了美国新近两种关于国际格局的代表性观点——无极时代与后美国时代⑤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 Vol.87,Issue 3,2008;[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之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所谓“国际格局扁平化”。他认为,国际关系扁平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国际组织和制度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中小国家通过建立区域联盟或一体化在国际制度中分享大国权力,“权力分配在大国和一些国家组成的集团间差距缩小了”。因此,国际关系由以往的垂直分布变成扁平化,是“国际格局与国际关系经历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性的结构性变化。”⑥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28-34页。
四、结论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仍在继续。2008-2009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总体而言是迅速的、广泛的,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币缘政治”理论、对“霸权稳定论”的检验和“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等等。但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深度上并非令人满意。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的单向性。中国国际政治学者集中关注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现实的关系,没有能够深入考察危机对国际政治学本身的影响。这从理论分析类文章仅占5%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实际上,重大危机往往不仅是现实的危机,还可能引发一个学科的理论危机。面对这次金融危机,一些重要的理论范式或者无法解释危机引发的新现象,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既有的国际制度没能防止危机的发生;或者在这场危机中彻底失语,如建构主义范式完全没有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没有一篇运用建构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章),这与它在国际政治学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尚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二,研究的科学性不足。唐永胜和彭云提醒:“切不可根据感性经验和主观愿望进行假设和推理。”⑦唐永胜、彭云:“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但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来看,大量的分析仍停留在主观判断层次上,而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研究深度不足的重要原因。相当数量的非经验实证研究文章的存在说明,科学研究确实是中国国际政治学急需恶补的功课。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的表面化。利用理论工具的目的在于深刻地分析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理论工具(如对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中心-边缘”理论的使用大多是一笔带过),而非在分析的意义上进行问题分析,对既有的理论工具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更少了。
检视国际政治学界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旨在增强国际政治学界自我反思的自觉性,从而尽力避免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遇到的尴尬——为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向公众致歉⑧2009年7月25日,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家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道歉。。如果我们不反思研究中暴露出的问题,类似的尴尬也许某一天同样会降临到国际政治学者身上。○
(责任编辑:何桂全)
book=5,ebook=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