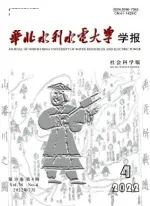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2010-08-15刘术永
刘术永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刘术永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乡约;保甲;乡治
《泰泉乡礼》由明代学者黄佐所作,成书于明嘉靖年间,被后世辑为典范礼书之一。它共分六卷,依次为乡礼纲领、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其中卷二《乡约》与卷六《保甲》的记述内容虽无法详尽描述明代乡治的全景,但它较有代表性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作为“乡村”①本文的“乡村”主要指社区意义上的概念,依于建嵘在《岳村政治》中的观点,“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而不可避免地所产生的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乡村社区的特点则是地域性、封闭性及家庭性。存在的国家政权底层的治理情况。
一、《乡约》卷中体现出来的明代乡约制度的基本特征
《乡约》记:“凡乡之约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以上四条,本出朱子损益《蓝田吕氏乡约》。”这里提到的《蓝田吕氏乡约》,便是于北宋熙宁九年由陕西蓝田之吕氏兄弟创立,后来朱熹修订成《朱子损益吕氏乡约》。有学者指出,《蓝田吕氏乡约》(包括《朱子损益吕氏乡约》)是明清各地方乡约关系和乡约制度的范本。[1]可见,乡约作为一种自约、相约的规范,于宋代即有之。对于明代来讲,乡约制度在各地方普遍存在,这从各地方志及文献中可以看出,而从《泰泉乡礼》所记的乡约制度来看,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
一是乡绅倡行乡约并成为组织的主要人员或主事人员的“背景”。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指两种人:一种是致仕、卸任甚至坐废的归乡官员,以及现任官员在乡的亲戚子弟;一种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监生、乡试及第的举人以及会试及第的进士中少数未任官者。不管是“有司”聘请的“教读”,还是“乡人自推”的“约正”、“约副”,都必须是德才兼备,堪为表率之人,而一乡之中最具此资格的便是乡绅。“凡乡礼纲领。在士大夫,表率宗族乡人,申明四礼而力行之。以赞成司教化。”“凡约正、约副正本如士大夫之教、明伦、敬身,以为乡人取法。”
二是乡约组织有具体明确的行为准则和活动准则及程序。四条乡约是组织成员自约、互久的行为准则,如“德业相劝”一约中谓:“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
三是乡约组织主要功能在于教化,并且乡约组织中的主管人员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权”。明代洪武年间,有人直接向明太祖指出:“古者善恶乡邻必记。今虽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痒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四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2](P428)乡约制度的本义就是乡民相约以保障共同生活与共同进步,设立乡约组织则意在于乡中形成扬善抑恶的良好民俗。通过乡约组织的活动,推行一种以自我教育为主、主事人员训诫为辅的教化方式。《乡约》中有记:“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又记:“命执事者以记过籍遍呈在坐,各默观一过,三犯不改,待他日誓于里社,鸣鼓罚之,毋得辄扬其过。过者不服,听其出籍。有大恶,则言于有司惩之。”可以看出,在组织成员作为教化对象犯有过错时,首先总是努力使之知错就改,或“密规”,或“众戒”,若其“不听”,则“约正”出面“诲谕”,并“书于籍”,待到其“三犯”就“行罚”,而底线则是“出约”甚或“言于有司”。从中可发现,若是将行政权力的概念泛化,乡约组织的“约正”、“约副”及“直月”有组织中都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前面“过失相规”的描述中,“约正”行使了申戒罚(“诲谕”)行为罚(“谢过请改”)、“直月”则行使了行政处罚中的声誉罚(“书于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尽管乡约组织的主事人员处于朝廷官制体制之外,但其仍然行使对于本组织成员而言的“治权”。
二、《保甲》卷中体现出来的明代保甲制度的基本特征
《泰泉乡礼》卷六为《保甲》,记录了专为“保安良善、消弭盗贼”而设的保甲制度之规定。事实上,保甲制度的历史可追溯到秦商鞅的“什伍连坐法”,而后各朝沿用,名称各异。定名保甲,首见于宋,为王安石所行新法之一。《保甲》所记的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
一是通过对人口、户籍的严密控制,专制皇权的触角得以伸入乡村。《保甲》中规定:“凡一社之内,一家为一牌,十牌为一家,甲有总。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为保长者,专一倡率甲总防御盗贼,不许因而武断乡曲。”“长联乎总,总联乎牌,牌联乎家,大小相维,善恶相核,一社之内,恶少自无所容。”从中可以看到,“牌”、“甲”、“保”为乡村控制的三级建制。另外,《保甲》中有记:“凡立牌有三:一曰戒谕,二曰沿们,三曰十家。”可以说,“戒谕牌”就是直接向乡民灌输统治阶级意志的象征。
二是借重刑罚手段,建立官府权威。《保甲》规定“十家牌”时有记:“日轮一家当甲总,沿门晓谕,因而审察各家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及违条约不听劝谕者,即行报官究治。或有隐匿,十家连罪。”又谓:“凡遇警窃,即于此辈中挨查。但有隐匿,甲内坐以知情重罪。”这些都表明保甲制度中有“连坐之法”的规定。其目的则是以重刑威慑乡民,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在《保甲》对“纠察在社之民”的八个方面事务加以规定时,都提到违反规定的人要受到官府“罚治”或“重加罚治”、“明正典刑”。刑罚的比重加大,突出表现了保甲制为官府所用、督办皇权的实质。
三是保甲制度的职能具有地域性。《保甲》中有记:“凡立十家甲牌,专为止息盗贼。另使每甲各自纠察甲内之人,不得容留盗贼,上甲如此,下甲复如此,城郭乡村莫过如此,以至此县如此,毕县如此,远近州县无不如此,则盗贼亦何自而生?”保甲制度以社会治安为重要职能,针对乡村分散的居住情况,从家庭为单位入手实现地域上层层有效的控制。
四是保长拥有一定的司法处断权。如“甲内但有平日习以为奸盗,及窝通贼党,容寄贼赃者…其稔恶不改者,即使捕送官司,明正典型”。又如“其不行旅止宿者,决是盗贼,量行擒捕,送官惩治”。对于“送官”这种做法,应可视作保长或充当保长的约正在协办官府事务时所持有的司法权力。
三、由乡约制度与保甲制度看明代乡治
从前面论述可以看出,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而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并且两者之间也有联系可察。
首先,两者皆具备独立的规范内容,同时规范之间却不无共同之处。乡约制度中有“乡约”可循,保甲制度中有“保甲之法”可依,都为成文规范。若以一种法律多元的观点视之,“乡约”亦是一种“民间法”,“保甲之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国家法”或称之为传统的“官府之法”。就其性质而言,前者温和,后者严峻;前者贴近乡俗,后者趋向官制。“乡约”中讲求“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保甲之法”则多讲同家互监,动辄“举告官司”、“禀官惩治”。另一方面,也可发现“乡约”与“保甲之法”中有相似之处。如《乡约》中对乡约四条之四“患难相恤”的规定:“患难之事。一曰水火。小则使人救之,甚则亲往,多率人救且吊之。二曰盗贼。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为告之官司,其家贫,则为之助出募赏。三曰疾病。小则遣人问之,甚则为访医药,忿则助其养疾之费。四曰死丧……五曰孤寡……七曰贫乏。”在《保甲》对“纠察八事”的规定中亦有:“七曰怋困穷。保内如有残疾病弱及贫薄无倚之人,各责令宗党收养,毋令所失。如无宗党,许编入有财力之家社丁内夹带。如一牌夫下有四丁,强壮者即夹带残弱一人与内。凡守望备警,仍量存之,不得需索帮补。”
其次,两者皆为乡治即乡村治理的制度形态,而“治权”的真实主体不尽相同。《乡礼纲领》中有记:“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为众人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保甲》中有记:“(保长)推选才行为众所信服者充之,或即以约正带管。”上文已经提到,出社“约正、约副”或“保长”角色之人为乡绅。尽管“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俱毋的差人点差稽考,以致纷扰”,然而在乡约制与保甲制的具体运作中依然表现出不同情况。
乡约制中的“约正、约副”是相对更加独立的乡村组织领袖。作为一种治理权力的“治权”,乡约组织中的乡绅应该是治权的主体,行使有“乡约”赋予的权力,负责组织内各项事物。“约正、约副”即非朝廷命官,也就无向官府、皇帝负责之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有乡绅充当的“教读”则可视为“约正、约副”与官府之间的纽带任务,但终究“约正、约副”不会与县官之间发生任何权属关系。
保甲制度中的“保长”虽“为民自推”,但与“保甲之法”属于管家法权体系之内相适应,他们无法避免成为基层督办皇权实施、协办官府事务的一类角色。由于被赋予古代政府历来认为事关重大的治安职能,“保长”的权柄有司法后盾,甚至“保长”本身也不得不时时面临“连做”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保甲制中的“保长”对乡村的治理更多的是皇权的体现,也是政府统治权的体现。“治权”的主体与其说是“保长”,不如说是隐藏幕后的官府乃至最高的皇帝。
四、结 语
费正清曾称中国古代政府为“自私自利的政府”,意指政府自身统治能力强,而社会管理能力弱。凡是维护专制皇权最需要的权力,则由自上而下的一个官僚系统来分配,另一些对统治权不那么重要的权力则由一个自下而上的乡绅系统来分配。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3](10)。就乡治而言,国家政权对乡村尽可能地采取“不扰民”的“无为”态度,与推行教化、实行公益救济相比较,以“官府之法”为代表的国家法权体系更关注“弥盗防奸”的社区事务。由此造成了官僚体系有意识地放权,使得乡村的治理事实上成为一种“官绅共治”的格局。
《泰泉乡礼》中反映出来的乡约制和保甲制可以用来描绘明代乡治的若干特点,而同时它无法脱离中国政治史的整体线索。依韦伯理论的“科层制”控制型治理,显然不能用来解读明代的乡治方式;而另一方面又无法将明代乡治视为理想型的“自治型治理”。原因在于乡治的“治权”从来不是由乡民个人掌握,而总是由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或者乡绅所把持。粱漱溟曾言:“古人的乡约(治乡之约),只是一种精神,是空虚的,故必以事实来充实它。”似乎是种客观的言说,表明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1]毅夫.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M].台湾研究集刊,2002,(4).
[2]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Abstract:The two volumes Village Agreement and Pao-chia of Tai quan Village Ceremony record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orms in the Ming Dynasty.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village agreement is that it is a self-enlightened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squire and the villagers.Pao-Jia system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rural security system under imperial power.For rural communities.These two systems,closely related,have their own functions.They reflect the wandering fe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t gonernance between the virtual power and illusory autonomy.
Key words:village agreement;Pao-chia;Rur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宋孝忠)
O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Ming Dynasty——Reading the two Volumes The village Agreement and Pao-chia of Taiquan Village Cenemony
LIU Shu-yo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450011,China)
DF09
A
1008—4444(2010)02—0092—03
2010-03-09
刘术永(1976—),男,河北唐山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