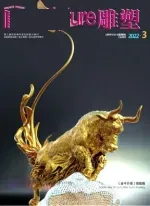艺术消费与经济伦理六题
2010-08-15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bySunZhenhua
■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 by Sun Zhenhua
艺术消费与经济伦理六题
■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 by Sun Zhenhua
Six Pieces about Ar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Ethics
[批评栏目]
本期主题:艺术与消费文化
编者按:上一期关于“艺术消费文化专题”的文章从艺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消费时代的文化形态等问题,本期文章将从艺术消费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消费文化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This issue's theme:Culture of Art and Consumption
Editor'snote: In the discussion of “Art and Consume Culture”, we talked about the cultural profits in
consume era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 and capital in last edition, now, the following articles will probe it from the angle of ar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ethics.
一、艺术按揭
资本的脚步离艺术越来越近了。在金融资本的热情注视下,将艺术品开发成为金融产品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新的生长点,目前正被人们热议的艺术按揭就是其中之一。
艺术品按揭的方式,与楼市按揭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买了楼市按揭,客户可以先行入住,产权证抵押在银行,还清贷款后赎回;而艺术品按揭针对的是拍卖公司的拍品,买家先交一半钱,但作品仍由拍卖行保管,还清贷款后,艺术品才真正归买者所有。
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为资金不足,而又酷爱艺术的人们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在目前纯粹是为了个人的欣赏收藏,不惜贷款来买艺术品的人,应该不多。这项金融产品,仍然是为那些希望让个人财产保值和增值的人们所开辟的新的投资渠道。
这是资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当投资股市、基金、房地产都可能有风险的时候,人们很想尝试一下艺术品。何况,在国外,艺术品的贷款、抵押、投资已有相当成熟的先例,当人们为手头剩余资本寻找出路的时候,何不在艺术品上一试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品的金融化,可以视作是资本保值战的一种方式。
不过,从社会对艺术品按揭的反应看,似乎并不够热烈。最核心的问题是,如果艺术品是有价值的,那么这种价值如何评定?这个前提不解决,何来保值、增值?
这跟楼市不一样。买楼买的是物质实体,它的地价,它的一砖一瓦,它的人工成本都是可以计算的。买艺术品不同,人们不是买画布、宣纸、金属、石头,买的是它的精神价值。房地产有估价师,他们相互之间就算有差别,根据市场行情,也差不到哪里去。而艺术品价值的认定,向来都是见仁见智的,就是那些有定评的经典艺术家,人们的评价常常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面对像艺术品这种起伏很大,把握不定的“金融产品”,如何让人放心,是个大问题。房地产也炒楼,但是再怎么炒,一个“高层”也炒不成“连排”,更炒不成“独栋”;对于艺术品就比较难说了,一个母猪可以炒成貂蝉,一个普通画家很容易就成了“中国的梵高”……
退一步说,知道了艺术的价值是“说”出来的,而且是动态的,变化的;那我们都认了,我们就不拿它当一般的金融产品,而把它当成特殊的金融产品行不行呢?这当然也是可以的,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问题是,怎么“说”应该也要有个规矩,有个制度。例如,不能自说自话,不能花钱买好话,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公正,能够独立于利益之外的评价机制。例如真正的独立策展人,独立的艺术批评家,独立的艺术媒体;相对公开透明的艺术评审制度以及博物馆收藏制度等等。
有了这些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矛盾,没有分歧,没有恶意炒作;只是,它强调阳光下的评论,强调平等的话语权利,强调话语监督……艺术价值就是在这种众说纷纭中的动态的平均值。
正是鉴于艺术制度的众多缺失,尽管艺术按揭的推广并不十分顺畅,但是仍需要艺术界的支持。支持的目的未必是为了金融本身,而是从一个经济的动机出发,最后也许会得到一个相对完善的艺术生态的结果。若能如此,善莫大焉!
二、你好了,我才能好
“无商不奸”,这是中国的民间思维,也是好多老百姓为商人设想的原罪。这个说法很情绪化、也很片面。正确的说法是,有的商人奸,而大多数的商人是不奸的,我们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篙子打一船人。如果大多数的商人都在互相欺诈,那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
真正的商人,是那种抱负远大,客观上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赚到钱。如果商人赚钱取之有道,我们老百姓就不能因为人家赚了钱就说人家“奸”,那样说是“红眼病”。
市场经济就是商人经济,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商人?怎样建立基本的商业伦理?这些问题远远不是引入市场机制就完了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强调了经商的那种功利性,认为所谓商人就是唯利是图的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说法如果仅仅从“在商言商”的角度,从工具性、技术性的角度,也许没错;但从终极目标来看,则未必如此。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美国新教徒经商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更不是为了享乐挥霍而赚钱,在新教伦理中,赚钱是为了侍奉上帝,一种向上帝的自我证明。自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决定将财产捐给基金会后,我开始对这些有“共产”精神的商人充满了敬意。当然,经商不是学雷锋,但是他们的最终结果是比雷锋还雷锋,至少他们比雷锋更有能力,能帮助更多的人。
是互利互惠,还是巧取豪夺,这是商人和土匪的根本区别。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商人与经商对象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合作的、以“双赢”为目的的常和博弈,它的意思是说,商人并不以伤害对方为获取自己利益的必要条件,他的赚钱不以让对方亏损为基础,尽管他们双方的得益可能是不平均的,有多有少,但至少是各取所需,相互满足。
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的关系是“非合作博弈”,即以“损人利己”为前提,那他们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根本就无法成立,所谓的商业和商品经济也根本就走不到这一天。
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敢于冒险的俄罗斯商人会追寻着鄂伦春人在深山老林留下的足迹,拿弹药、盐巴、日用品换取他们的鹿茸、兽皮。从交易的结果看,俄罗斯商人利润肯定丰厚,但是他们的前提是首先满足鄂伦春猎人的需要,然后才能在下一步的延伸交易中实现自己的利润。尽管俄罗斯商人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得利,但客观上,是冒着危险先满足别人,只有你好了,我才能好。
真正的商人应该永远把交易对象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且要立足长远。中国传统商业讲老字号,也就是今天说的品牌。老百姓也信任老字号,这是因为老字号讲究诚信,讲究“童叟无欺”。这并不是商人的天生善良,而是利益使然,老字号要获取自己的更大利益,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奸”字当头,坑人,蒙人,只要赚到钱,哪怕天塌地陷,这些都不是正经商道,只能说是骗子,或者强盗。三鹿奶粉的教训告诉人们,你欺骗客户,不让客户好,最终自己也好不了。
你好了,我才能好,这是商业逻辑的起点,如果推而广之,其意义当然不会仅仅只局限在商业的领域内。
三、价格是怎样涨成的
几近疯狂!法国佳士得所拍卖圆明园兔首、鼠首,价格每件拍到了1400万欧元,几乎所有的文物专家和收藏家都被这个价格所震撼。除非发疯,这个价格是不可理喻的。
虽然文物拍卖的价格和文物的价值不能划等号,但是,价格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指数。如此高价格的恶劣作用在哪里?它将混淆世人的视野,干扰我们对中国文物的价值判断,为中国文物在将来理性地回归制造障碍。
1985年,当一位美国古董商在加州的一处私人住宅内偶然发现三尊圆明园兽首的时候,牛首在主人浴室里挂毛巾,马首和虎首则在露天花园里做摆设,这位古董商仅仅以每尊1500美元的价格就把它们全部买走了。
1989年,当那件马首在苏富比拍卖行现身的时候,被台湾一位蔡姓收藏家以25万美元高价拍到。后来几经转手,待这尊马首2007年再次出现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时候,估价已经到了6000万港币,后来经澳门何鸿燊先生斡旋,在拍卖前以6910万港币购回,捐给了国家。比较起来,这尊马首比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花1500多万拍下来的虎首,价格又高出了好几倍。
就这样,圆明园兽首的价格从1500元美金到1400万欧元,其变化幅度之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在整整二十年圆明园兽首价格飞涨的历史中,我们从中读出了什么?
这个荒唐价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能读出一些投机者的贪婪、狡猾和利欲熏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也读出了一些国人的盲目、冲动和非理性。这说明,兽首价格的暴涨不是单方面的,它也是一些国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或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终,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可好,几个兽首风头出尽的同时,等于给境外中国文物的持有者、倒卖者上了一堂启蒙课,原来中国文物这么有利可图,于是他们更知道了奇货可居,更知道了以后该怎么吊起“爱国主义者”的胃口,从文物经营中赚到大钱;也许,其中一些人还会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从中国偷运文物,谋取暴利。
说到圆明园海晏堂12生肖兽首,它的价值主要在于记载了一段民族屈辱和伤心的历史,它的象征性远远高于它的艺术性。从雕塑史的角度看,中国明清时期,雕塑在走下坡路,它的成就远远不如过去。这些兽首的特殊之处,不是因为它的“国粹”身份,相反,是它中西合璧的风格。
12生肖的说法,起于东汉,我们目前所看到最早的雕塑形象,是隋唐墓葬中的“12生肖俑”。所以,12生肖雕塑并不是新东西。只是,在建圆明园的时候,12生肖雕塑的首席设计师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朗士宁;它的监制人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蒋友仁。所以,圆明园的12生肖铜像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手法,比较明显的是虎首、猪首,呲牙咧嘴,而中国传统雕塑手法不这样,它们要概括、含蓄、传神得多。
如果我们不是死盯着圆明园兽首,过分地渲染它们是何等“国宝”,如何应志在必得;而是立足长远,有效地推介和宣传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样有利于在追索流失文物的时候,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我们还应该和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行动,整体部署,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条约”和利益格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不一样的收藏
眼下的中国,收藏大热。
隔三岔五,就会收到各种关于收藏的杂志、报纸和宣传品。我是一个缺乏收藏意识的人,曾经有过一些现在看来很值钱的字画,当时价格还没有上来的时候,就随手送给了喜欢的朋友,至今也不觉得后悔。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朋友是真喜欢,一般而言,他们的收藏不是为了进入市场流通,敛财获利,而是自己玩赏。既然如此,放到哪里都一样。我发现,对于喜欢收藏的人,什么时候提出要观看他的藏品,都会非常高兴,再忙,也会兴致勃勃拿出来和你一起品鉴讨论;何况,他们还保管得特别好。
我的导师史岩先生,出生于江苏宜兴世家,毕生喜好收藏,遗憾的是,抗战西迁,藏品散失大半;文化革命,又遭一次浩劫。四十年代初他到敦煌考察,在河边拣到了一只很小的木质菩萨手臂,上面彩绘犹在,根据风格造型判断,当属唐朝遗物。后来上课的时候,他拿给我们看,并说,只要是找到了这只手臂的出处,随时愿意交出来,拼接上去。
我们系还有一个前辈王伯敏先生,书斋名号“半唐斋”,当年参观他的藏品时,他也说,里面任何器物残片,只要有人能指出原作所在,都愿意无条件奉还。
史岩、王伯敏先生这种属于学者收藏,他们心里由衷地喜欢传统文化,而且这种喜欢远远超出了一己私利和占有欲望。史岩先生的藏品还发挥了独特的教具作用。当年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把藏品拿出来让我们摸一摸,他说,学美术史,不摸东西是学不好的,没有收藏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1994年,史岩先生以90高龄辞世,他的藏品捐给了学校,希望学校将来建艺术博物馆,他认为,一个大学没有艺术博物馆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他们而言,藏品是生命的一个部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一生心血的散失,而传给后代,未必能避免这种结局。史先生常说,过去见得太多了,许多大家庭时运不济,都是零零星星地变卖藏品。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最好的归宿是整体打包,捐给国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能善待它们,并且发挥作用。
由史岩先生的收藏故事,想到了前不久在上海的一次经历。
那是参加一个会议,好客的主人专门安排了一个自助晚餐,在某个私人会所的花园举行。虽然是很普通的自助餐,但价格却是外面的好几倍,组织者说,到这里主要是“吃环境”。的确,在上海闹市拥有一个园林式会所已属不易,何况主人又以收藏闻名。
让人惊讶的是,花园里几段墙都是从外地购买、拆卸,重新拼装出来的。一段是徽式建筑的院墙;一段是北方的门楼,朱漆大门、铺首、石柱;一段竟是藏式建筑的墙壁……
其实,不止是私人,就是一些园林文物部门,为了营造历史气氛,也有从外地买一个古宅回来重新拼装的做法。
活生生地割断历史、地缘、环境,把文物从原生地买回来,变成自己的藏品,这种掠夺式的做法,是“收藏”吗?
史岩、王伯敏这些老先生想的是让残存、零碎的文物回到它的原生地,维护文物自身的完整,而这些人则是破坏历史的完整,满足自己的炫耀心理;二者在境界上,相差何其遥远!
收藏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世态人心的变化!
五、草根经济学
最近又有一些好心的朋友给我上经济学课了。一旦金融形势风云变幻,波谲云诡,就会有一些好心的朋友自告奋勇地来对我进行投资理财的指导。
近30年,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涌现出了无数的草根经济学家。这些人除了一部分奋战在私企,更多的人是在为个人理财而战。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之类的话,让每个跟财富没有仇的人听了怦然心动。什么时候该抄底了,什么时候该买楼了,什么时候该买黄金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小型关于投资理财研讨随时都可能发生,各种建议、提醒不绝于耳;这些理论都是一套一套的,言之凿凿,有高瞻远瞩的分析,还有典型个案的启示。
我属于那种经常被草根经济学家拿来启蒙、训导的对象,尽管没有积极投身到个人投资理财具体实践中去,对这种草根经济学的现象倒是感兴趣的,对这种现象,如果要往高处说,往大处说,甚至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
“人人都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它体现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重视的程度。如果对个人的财产毫不关心,谈何个人权益?没有一个个拥有独立人格和私有财产的个人,何谈公民社会,何谈共同利益?
一个人凭诚实的劳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他希望通过个人的理财行为,让利益最大化,让钱生更多的钱,至少,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币”在那里贬值、缩水,这种努力无可厚非。金融危机一来,危机意识加剧,国家有国家的对策,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招数,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轻视人民群众的经济学热情,轻视他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积极作为,将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应该理解的是在他们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例如,在经济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楼价反而在非理性的疯涨,这是许多人盲目跟风的结果;但是,这种“盲目”的背后仍然是有着相对理性的思考。是的,人们竞相买楼保值,预防通涨,最后的结果的确可能造成楼市泡沫,连带产生出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整体的非理性,“买涨不买跌”,对每个个体而言,又是在可能的选择中,比较合理的一种选择。
想想在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几乎无财可理,清闲倒是很清闲,按时拿工资就是了。比较惨的是农民,没人发工资不说,他们与生俱来的经济才能还受到限制。上面总是有无数的指示,告诉农民要种什么,种几季,种多密;还要告诉农民施什么肥,养什么家畜;甚至连吃饭都有指导,什么时候吃干的,什么时候吃稀的……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群众的经济学热情是空前高涨起来了,但是在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和老百姓的微观经济选择之间;在专业经济学家的高头讲章和草根经济学家的街谈巷语之间,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我注意到,很多时候,民间的草根经济学家常常会跟主流媒体反着来。
总之,草根经济学的兴旺并非是一件坏事,然而,他们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那些投资理财的秘诀究竟有没有道理,谁也说不准。真正的经济学智慧在哪里呢?看看那些经济学的精英们,他们也是在各说各的。
六、反经济学生存
现在是一个聪明人的时代,这种聪明首先体现在如何掌握“经济学生存”的技巧,合法地将个人的经济收益最大化。
有不少这样的人,在打理个人财产方面,总是能够占尽先机,在条件、背景大致相同的情况下,通过业余的投资理财活动,把自己经营得很好。例如,当一般人勉勉强强混到一套房的时候,他已经都有了三套、五套房了。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经济学生存”有没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按照同一种“正确”的投资理财模式,是否都具有成功的必然?
以我的看法,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理由,假定每个人的投资选择都是正确的,那么无数个正确的答案的总和,可能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某人买了一只正确的股票,大家都来效仿,买着买着就变成了“击鼓传花”,再好的股票也经不起众人追捧,到崩盘的时候,正确变成了错误,只有那些改弦更张,预先抛售了这只股票的人才是赢家。
所以,“经济学生存”通常玩的是一种“正正得负”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大家也许同时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然后一个突然的时机出现,让大多数人变得不正确。而最终正确的,只是少数在这个神秘的时机前中止了游戏的人。那这个时机可不可以准确预测呢?很难,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既是原因,又都是答案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谁知道上帝在怎么时候掷骰子呢?
“经济学生存”由于有很强的“运气”成分,因而难以找到普遍正确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个游戏中,大多数人都只能当陪衬,真正成功获利的,永远是少数人。
人人都向往过好生活,此乃天经地义,但是,你凭什么就坚信,那片幸运的树叶就正好会落在你头上呢?
我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好生活,在根本上,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和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的经济形势下,炒与不炒,博与不博之间,肯定会产生差异。这样就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经济学生存”,投入到炒股、炒楼的博弈中;另一种是“反经济学生存”,不炒、不博,让自己的生活随大流,随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的上升而水涨船高。
地产界任志刚有句话,说这么多年来,房价其实没有涨。细想想,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购房能力和住房价格总是维持在一个大致相当的比率上。眼下的高房价让低收入群体望而生畏;在低房价的80年代,面对低价商品房,低收入人群同样望而生畏。所以,低收入人群完全靠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商品房,从来都是不现实的。过去靠公家分,现在只能依赖公共福利政策,通过福利房、廉租房、安居房来解决。
个人的聪明,始终是小聪明,最重要的是整体的经济大势。有人说,现在赶紧花银行的钱,贷款买房,以防货币贬值。试想,如果人人都按这种聪明的想法干,假设那天银行真垮了,经济崩溃,你纵有再多豪宅,又有何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韩国人,泰国人纷纷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捐给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倾巢之下,安得完卵的道理。个人解囊,支持国家,明明是件吃亏的事,但他们还要这么做,可见这些人跳出了小聪明,懂得了救大势其实也就是在救自己。方方面面,成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界和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