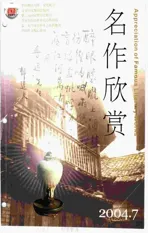超越时代阅读能力的《黑骏马》
2010-08-15陈福民
/陈福民
作 者: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张承志在中国文坛有很多身份。他是“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创始人,1968年写了血书跑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是个会骑马放牧说地道蒙语的知青;他是个专业知识分子,在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亚史方面造诣深厚;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在小说、随笔等领域都有独到建树,他几乎是第一个辞去公职脱离体制的自由写作者,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文化领域的“抵抗者”,被认为是“一面不倒的旗”(郜元宝)……但所有这些,为他自己所看重的只有一个身份:有信的人。当然,就文学而言,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底层”这一概念最早的倡导者、使用者和身体力行者: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着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老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
这段著名的“后记”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张承志对自己的“红卫兵生涯”乃至“文革”历史的辩解回护,因此表现了一种拒绝与过去时代划清界限的顽固姿态。尽管张承志的表述在试图建立起个人生存和历史运动之辩证关系方面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但他所强调的“得天独厚”与“幸福”这类感性字眼,难免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并因此质疑他的历史清白。于是,有关“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作为文学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就被当做一种姿态而轻轻地放逐了。这种与那个时代共生的轻率肤浅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得对张承志《黑骏马》的理解评说长久以来不得要领。
《黑骏马》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悲剧性爱情故事,小说线索简洁单一,就情节而言与所有的爱情悲剧并无二致。“我”——少年白音宝力格被父亲托付给伯勒根草原上的老额吉抚养,而少女索米娅也被老额吉收养。老额吉抚养着两个孩子,盼望他们结为终身伴侣。但白音宝力格不甘心做一个无知识的传统牧民,一心想到外面读书。终于,在接到参加兽医培训班的通知后“我”兴奋上路,索米娅则搭上运送羊毛的货车一路送行。夜色中,两个年轻恋人依偎在货箱的羊毛堆里海誓山盟,约定“我”培训结束后就回家结婚。故事到这里一切平常。但当白音宝力格学成归来回到伯勒根草原,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发现索米娅总是躲着他,并以异样的目光惊惶地注视他。原来,在白音宝力格走后不久,索米娅就被一个叫黄毛希拉的草原恶棍玷污并怀了孩子。更令白音宝力格精神崩溃的是,额吉和索米娅并没有像他那样愤怒,而是默然承受了这些。在巨大的打击下,他意识到了自己与草原生活的隔阂,决定出走。
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又回到了家乡伯勒根草原。他决定去寻找索米娅,经过寻访得知,此时额吉早已过世,索米娅带着孩子其其格孤苦艰辛,被迫远嫁到诺盖淖尔湖畔的异乡。当我辗转找到索米娅和其其格时,生活改变了一切也谅解了一切,无论是索米娅的不幸遭遇还是“我”的隔膜、背弃。小说结尾,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离开了诺盖淖尔,唱起了《钢嘎·哈拉》——《黑骏马》:“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终于悄然逝去的一霎间,我滚鞍下马,猛的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朝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我悄悄地哭了,就像古歌中那个骑着黑骏马的牧人一样。”
《黑骏马》一经问世立刻好评如潮,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并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然而,这部小说表面单纯老套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相当丰富晦暗的多重含义,人们对作品的激赏也始终伴随着疑惑和分歧,这情形完全不似后来大名鼎鼎的《北方的河》那么明朗。
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张承志通过“我”——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所表现的内省、忏悔意识和出人意料的道德姿态。
张承志是个被公认的具有理想主义气质与情怀的作家,一般来说,鲜明的立场与强烈的道德爱憎感是这类作家的天然禀赋。《黑骏马》告诉读者,“我”与索米娅的童话一般美丽的爱情,遭遇了草原恶棍黄毛希拉的侵犯。无论在小说提供情节层面还是在世俗生活的理解中,“我”——白音宝力格都不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相反,他是个“受害者”。按照常理来推论,对于这个传统的“三角”爱情悲剧,张承志本该有相对清晰并不困难的判断。也许是由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太强烈的缘故,人们在阅读时经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混淆写作者与他所描写刻画的生活、人物之间的差异甚至画上等号,善意的读者也许是见惯了民间“惩恶扬善”的大团圆故事,于是很容易向作者直接索取简明或者简单的道德立场。然而,张承志非但拒绝谴责,还让“我”——白音宝力格对爱情悲剧及其后果承担了深刻的内疚、自责:
我宁愿去死也不能继续在这沉寂中煎熬。我哧哧喘着,对着黑暗大声说:
“索米娅!不,沙娜!你……你说点什么吧!”说罢我就使劲闭上眼睛,死命咬着嘴唇。过了好久,索米娅开口了。她低声说道:“奶奶死了。”
又是沉默。我明白,该我对那湮没的质问回答了。
“奶奶死了”,这四个字字字千钧,直逼张承志内心,使他深刻怀疑着所有简明的道德“真理”。从这里,他带着读者涉过伯勒根河,走上了一条体验生存复杂性与人物内心复杂性的道路。《黑骏马》强烈的内省气质妨碍和嘲弄了人们的道德满足感。
事实上,这种“内省”早在《黑骏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短篇小说《绿夜》也写了一个“寻找”与失落的故事,当“他”八年后重返故地找到了魂牵梦绕的小奥云娜时,这个象征并且寄托着“他”的青春、生命、理想的昔日天使,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想象出现。相反,她变得“皮肤粗糙,眼神冷淡”,甚至毫无顾忌地跟醉鬼乔洛调情。不是人改变了生活,而是现实生活的深刻轨迹改变了一切,这迫使张承志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内心,因此“他”也不能不意识到,“哦,岁月不会因为你而停止流淌,小奥云娜也不会为你永远是八岁”,“表弟错了。侉乙己错了。他自己也错了,只有奥云娜是对的”。
道德善恶在此被转换成了“对与错”的生活是非问题,这让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立场不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澄澈透明。对这种色彩斑驳、自我贬抑的道德姿态,曾镇南显得很难理解也很痛心:
当白音宝力格要求索米娅忏悔但听到的却是索米娅为婴儿缝制小鞋发出的欢悦天真的声音而毅然出走时,这个有了文化的年青人,已经被写成多少有点像普希金的《茨冈》里描写的那个文明人阿乐哥的味儿了。那是一种狭隘的和自私的味儿。也许,这里隐藏这一点作者对草原人民的淳朴、质直、厚重生活力量的肯定和对城市文明的鄙俗、狭隘的一面的批评;但是,对于把爱情看成草原日出一样绚美的纯粹的白音宝力格来说,让他进行这样的自责,是不是太严峻一点了?应该赞许他对爱情的严肃态度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追求,他不是才有十九岁吗?(《〈黑骏马〉及其他》,《读书》,1983年第3期)
今天看来,曾镇南的批评尽管委婉温和,但显然没有深入触及到张承志及其《黑骏马》的要旨,这种执著于小说故事情节、细腻体贴人物感受并真诚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而歌哭的批评习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当中并不少见。比曾镇南更严厉、同时距离作品主旨也更远的批评,来自署名李福亮的《不能把丑当作美》。在李福亮看来,张承志的《黑骏马》完全混淆和颠倒了美丑关系:
作者没有以足够的笔力去鞭笞使索米娅失去贞操的淫棍黄毛希拉,没有鞭辟入里地去批判造成悲剧的古老的社会习俗,反倒毫无保留地尽情讴歌容忍姑息这卑污的习俗的老奶奶和索米娅,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不肯入乡随俗的白音宝力格身上!(《不能把丑当作美》,《书林》,1983年第6期)
进而,这位严厉的批评者甚至做了诛心之论以推测起索米娅的受辱是否出于自身无可救药的堕落:
索米娅呢?作品没有写清楚她是怎样和希拉搞上的(让人疑心到她也是无可无不可),但却清楚地写到她的眼光使白音宝力格“感到陌生”、“含着敌意和警惕”……
多么残酷,多么没有廉耻和良心呵!(《〈黑骏马〉及其他》,《读书》,1983年第3期)
不能不说,这样的批判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但如果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要求“向前看”的整体时代氛围,对《黑骏马》出现诸如此类的批评就是不难理解的。刚刚被催促着从“伤痕文学”中挣脱出来的文学写作,似乎应该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而张承志从《绿夜》《黑骏马》到《老桥》,却对这种肤浅的时代要求置若罔闻——这时他还没有写出令他有拼搏奋斗标签感的《北方的河》——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回望内心、自我挣扎、自我说服的精神姿态。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再次上路出发的心理能量,而这一点,在相当的程度上无法被那个时代所谅解。
《黑骏马》对草原牧人生活方式中的民族性格和古老习俗的深深涉入以及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也让很多读者感到陌生。比照中国当代文学积累的经验,“我”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完全是别开生面的,没有涉及社会政治、时代背景等因素。除了白音宝力格的父亲是“人民公社社长”这一信息透露了大致的年代轮廓之外,其他的一概空缺。这导致了人们对小说中爱情悲剧的读解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现成经验,最后不得不将讨论的视点转向“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前述李福亮对《黑骏马》的愤怒声讨,也正是这个层面上展开论断的。在李文看来,孰美孰丑是一目了然不容置辩的,而这“美丑”则分别对应着文明/愚昧、进步/落后等范畴。但是对于一个在草原深处生活多年潜心体悟的人来说,问题远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如真理那般简单。这里真正用得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而正是在这里,隐藏着张承志与现代主义的线性启蒙观、进步观乃至文明观分道扬镳的种子。不明就里的人们经常指责张承志的“道德理想主义”,却很少愿意去看看他为这个所谓的主义付出过怎样的代价,尤其不愿意去看见张承志赋予这主义的现实形态。
毫无疑问,张承志属于那种感受力特别发达、也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在他后来为自己塑造的坚强男人形象的内里,分明横亘着一个细腻、纤敏的精神世界。在《黑骏马》中,这个世界被投射成大草原的壮美、纯净与大爱包容。那些大段大段、精彩绝伦的景物描写,那种对人物极尽想象开掘且略嫌过度的刻画,那种灌注着连绵不绝饱满丰沛的浪漫情感……这所有一切被视为张承志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因素,其实都与他对线性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怀疑深刻相关。在《黑骏马》问世之后,有数量颇巨的论者都被张承志的“诗意”所吸引,不遗余力地予以称颂。殊不知,如果不能体会写作者最为核心的文学理念及其所由形成的现实思想根据,抽象地讨论艺术风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构成张承志文学信念的最核心的要素,是“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的存在。这个存在,也被称为“人民”。还是在《老桥·后记》中,他宣布:“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是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动着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这个信念,他从来没有修改过,也给他招来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为人民”这个提法的确过于概念化,且“人民”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演进,是不断变换着其内涵的,张承志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为人民”就很难避免在历史的淘洗中被误读误解。就《黑骏马》来看,小说中那些丰富生动、复杂晦暗的含义都能从这个文学信念得到解释。生活的真实与丰富多义本身就是反概念的,“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决定着张承志这部作品坚实厚重的现实品质,根本无法用主观概念来做抒情化处理。徐亮就此指出:
从上述意义上,《黑骏马》既不是浪漫主义的,也不是表现主义的,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张承志达到了狄更斯、福楼拜某些作品中显露出来的那种未经解释的真实性。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致公认《黑骏马》
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水平,而且作品始终具有
可解读性的原因。(《惊人的偏执 惊人的真实》,
《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
在张承志的小说创作生涯中,《黑骏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作为一个主观情志异常强烈又极端自信的作家,张承志留给中国当代文学太多的震撼和启示。可惜的是,从《北方的河》之后,他以一个“骑上激流”的勇士面貌开始“胡涂乱抹”,尽情抒发和挥洒着他强烈的信仰之情,再也无心于《黑骏马》式的文学。相对于现在这个简洁明快、激烈决绝的“有信的”张承志来说,《黑骏马》的温暖丰厚、复杂多义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不经意创造的,无论就艺术水准的超拔还是思想认知的先锋而言,它都大大领先于它所诞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