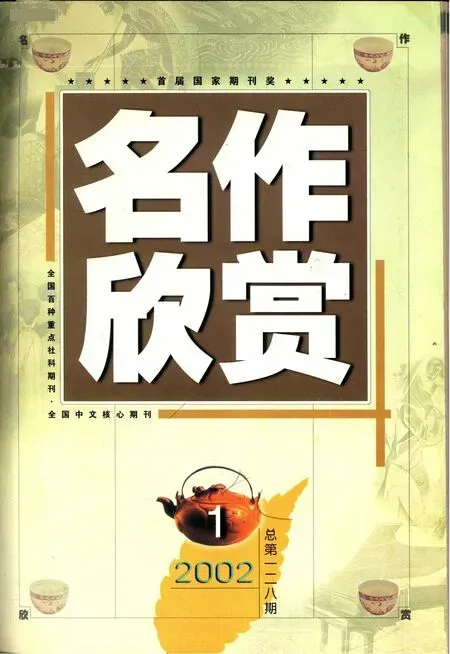心爱的孙犁的书(外一篇)
2010-08-15苗得雨
/苗得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文讲所学习时,除了必读的书,还有机会读了其他一些书。当时出版的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长篇,都读了。读之中,觉得孙犁的《风云初记》更叫人喜爱。好像在众多漂亮姑娘中,分外看中了其中的一位。而这喜爱,越来越浓。从那,可以说,我便成了孙犁作品的迷恋者。今天说,叫“粉丝”。
《风云初记》开头没有惊人之语,很平常:“1937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但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孙犁的作品,是这样的特点,即在朴素的描写中,自然流露出纯真、诚挚的情感,让人不由自主地受着吸引,受着感染。读后,像童年时或初恋中那些情景一样久久难以忘怀。
作品中的人物,只读了第一遍,就永远地记住了.如同家乡友伴们那样熟悉,就在身边,秋分、春儿、芒种……。作品中一些细节,也久久记得,以至因此逢人便说,那词句几乎和书上的一样。像作品写姐姐秋分送丈夫参军走时的情景:
秋分没有说话,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雨过来了,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打得河水啪啪的响,西北风吹送着小船,一个亮闪,接着一声暴雷。亮闪照得清清楚楚,她卷起裤脚,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一直遮到大腿。跟着小船跑了十几里路。
再如下面这一段,丈夫离家后,“秋分……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
这里应用“亲人”二字,却用的“行人”,可是,让人觉得比“亲人”还亲。亲人走了,奔波在远方,一个“行”字含意更深远。我第一次读时,读到这里,眼里涌出了泪水。
作品中的战斗场面,全篇的故事,也有不少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但都是这样朴素、自然地写,这样的“原汁原味”地告诉给读者。朴素、自然到像未下过功夫,其实正是一种大功夫,是不以惊人而以感人取胜的大手笔艺术。那年孙犁作品讨论会时,老诗人魏巍说孙犁的作品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孙犁的老友徐光耀说他是把思想包藏在美里。孙犁自己说作品“如实”地写,“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从繁琐到单纯,要经过很多苦心。”“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
在当时,在对一批作品的评论中,对这部书没有突出,因之,“轰动效应”平平。很久以后才改编成电影,恐怕因为没有表达出原作的特别风韵,也一般。但多少年来,人们叙谈起来,都说:“还是《风云初记》好,是那一段作品中更让人难忘的一部。”
从《风云初记》起,我便搜罗起孙犁的其他作品读,包括《白洋淀记事》和从中又选了些的《荷花淀》精华本及1956年写出的中篇《铁木前传》,都读了。每一篇,都无不喜爱。在同友伴交谈中,在帮助一些作者写作的过程中,讲到读书,不管列出多少本多少部,都几乎漏不了孙犁的《风云初记》和他的别的作品。但凡听过我介绍的,在读了之后,也都说好,于是,不少也成了孙犁作品的喜爱者。我发现,全国在孙犁亲自指导或受他影响下的作者,有十几个。还有的,可能不一定与孙犁有联系,但我也发现他们的作品有“孙犁味”。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味,我是指在大的方面的一个感觉。后来,全国果然有了“荷花淀派”的立说与研究。新时期初期,铁凝在二十岁左右写的几篇小说,我读了,惊喜地叫道:“孙犁味!”后知铁凝果是孙犁的新弟子。在1984年12月全国四次作代会上,我同铁凝谈这事,她说:“孙犁就是我的老师。我在老师那里,看到了你写给他的赞扬我的信!”
《风云初记》第一、二集,1953年出版的,第三集1962年定稿后,由作家出版社在1963年3月合成了一本。这合成的一本,我买过好几次,此前的一、二集本,也买过好几次,《铁木前传》也买过好几次,但最后我手头成了一本皆无。原因是,我介绍给一位作者,就把书借给他看,或有的不是作者,是文学爱好者,当我向他介绍了之后,也便随之送他一本。我想,反正我可以再买。可是,想不到,一个“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封资修”,我心爱的孙犁的书,再也倒腾不到了。
在我久久遗憾之时,省文联恢复前的过渡单位“省文艺创作组”成立, 以“原省文联”身份接回了省文联的大楼,在清理礼堂里堆满的乱书——“文革”中从各单位各家抄的归了“省直文革”又归省图书馆被拣完后的一堆中,如同海底捞针般,又得到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荷花淀》等书,还有一本孙犁的诗集,都破旧不堪。尤《风云初记》已破得约三分之一无了右下角,足见有多少读者读过。
至今我珍存的心爱的孙犁当年的这些作品,就是这样幸运重新得到的。若不然,我将像“失恋”似的不知会有多久。
2009年11月6日
三见孙犁
在我崇敬的作家中,孙犁是一位。见过三次面,文字联系多些。这位老作家,不大乐于参加活动。朋友讲,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像“打了个盹似的”,得了心脏神经官能方面的病,养病七年。此后,凡遇七八个人以上的场合,就感到紧张。参加活动少,可能也与这情况有关。孙犁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我理解,他意思是,从文这事,要不得虚浮,应坐得住,潜得下心。其实,他与人联系是相当广、相当多的。帮助的作者,读一些作品写的评论、读后感,与老中青作家、作者的书信往来,达到他那样数量的,在老作家中可能是居于上位的。
大约在1956年,他来过一次山东。省文联还在趵突泉那个地方,有一天,王希坚伴着他在走廊过道上走,我遇上了,希坚即停住向我介绍说:“这是孙犁同志!”我十分惊喜,因我在此之前已读了他的长篇《风云初记》和大量的短篇,已成了迷爱他作品的一个读者,忽然见到了作家本人,真是喜出望外。他个头高高,很潇洒,但朴素、和蔼,像个乡间秀才。 当希坚向他介绍我时,他笑着连忙说:“知道!”接着转身小声对希坚说:“唔,是个大小伙子了!”我说:“我爱读小说,您的作品,我很喜爱,尤其《风云初记》……”孙犁听着,笑着,点着头。然后,我们三人一起说了些别的,就急急分手了。他是这一年写完《铁木前传》后病的, 当时可能还未病。
29年后的1985年5月,我去东北采访,经天津,住了几天。中间,一天上午与朋友闵人、王树人、柴德森一起去看望他。我们到了多伦道他原来的住处,树人喊了声“孙犁同志”,我们就进了屋。他正在整理书,虽已过了古稀之年,还是潇洒、朴实的老模样。先是树人、闵人与他互道了各自的近况,便转为以我俩为主叙话。我讲了我有过多本他当年的书,因送人都没有了,多年后才又搜罗到的故事。孙犁听了,笑说: “我也是这样,一个‘文革’,什么也没有了,《风云初记》还是‘文革’过后朋友冉淮舟把他存的那本给了我;《铁木前传》,是林呐让出版社的同志费很大劲找到的一本……”我说:“我常对人分析,我觉得您作品的特点,是朴素、自然、真情美。”他听着,笑了笑,转说:“你的《文谈诗话》那本书,写得不错。”我说:“其中有《作品的感人之处》一文,专分析《碑》那一篇的,不知分析的准吧?”他想了想,点点头说:“唔,是那意思!”我又说:“我发现,你是用诗写散文,用散文写小说,用短篇小说写长篇小说……”他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没说什么,一边签字送我一本他新出的《书林秋草》。我出发去东北的过程中,仔细读了那书,书中对文学各门类,都有精辟的阐述,对我说的问题,不作回答地回答了。我不时地笑我的“发现”简单、肤浅。
第三次见面是在同年9月,全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在天津开成立会时,一天,张学新领参加会的几位作家峻青、俞林、陈靖、艾克思与我等一起去看望他。此次,多是别的同志与他叙话。然后又一起合影。叙话中心题目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问题,有的同志说到这个问题时很激动。孙犁一直静静听着,中间像自言自语似地插了一句: “文学,怎能不是通俗的?”我在一旁琢磨,我想到郑振铎的《俗文学史》,文学不但有俗,还有俗文学一个大种类,郑将许多名著都列到了“俗文学”的范围。大家说了一阵后,孙犁才说: “恐怕,你们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文学?”停了停,他又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文,也很通俗。还有,很有意思的俚曲,那可是不容易写的……”大家说:“对呀,关键在文学就应当是文学!”
新时期以来,孙犁写了不少散文、随笔和以“乡里见闻”、 “芸斋小说”为名的短篇小说三十余篇,出版的包括《书林秋草》在内的十几个集子中的篇章,我见到的,都仔细拜读了。我出的一些作品集子,差不多都送他指正。他几乎每收到都有回信。1991年9月,我寄去诗选和另外两本,他即于10月9日来信说: “今日拿到惠寄大作三种,甚为感谢。近年不断收到您的新作,知道您执著地创作,深为欣慰。我近年多病,今年心脏又出毛病,写作已经很少,质量亦差,唯有寄希望于壮年人了。”我一直觉得,孙犁老师没有离开我们。有一年春节,我照样写了贺年卡,待寄时,才又放了下来。在我的心里,老师还在多伦道那地方忙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