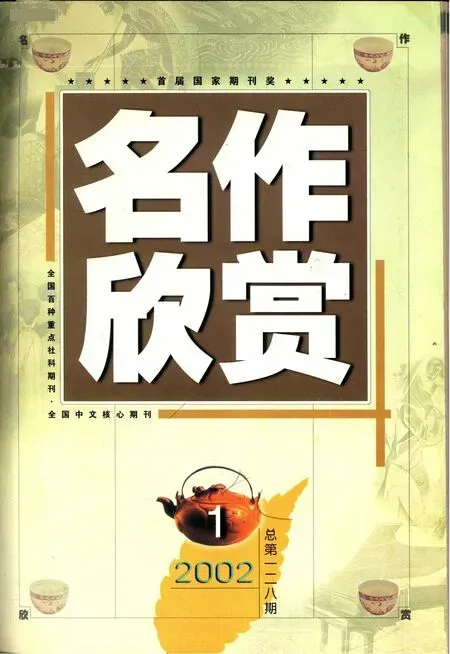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英雄观念(一)
2010-08-15孙绍振
/孙绍振
作 者: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三种方法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比较通用的方法,按时间顺序,从神话叙事讲起,从最原始的向最高级的方面攀登,通常我们写自然史,中国通史,西方文学史,欧洲经济史呀,用的都是这种办法。顺时间程序,最容易看出发展变化,有了变化,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变成了那样的,就有矛盾了,就有分析的对象了,就不愁研究不出名堂来了。当然,这个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对现象被动追随,失去揭示深层规律的主动性,纷繁的现象很容易淹没内在的、深邃的逻辑。
第二种方法,不是从最原始、最本初的状态讲起,而是从最高级的阶段回溯过去。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要解剖猿猴可以按第一种方法,从猿猴的老祖宗下手,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转向猿猴的后代,将人体解剖作为起点,从高级形态向低级形态回顾。这种方法之所以有必要,就是,顺时间程序,似乎顺理成章,也可能太顺理成章了,直观所见略同,提不出深刻的问题来。只有倒过来看看,后来有的特点,原先没有啊,就可以提出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条件造成的啊?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先有了一个完备的形态作为参照,此前一切形态的不完备性就一望而知了。
第三种,既不从最高级、最完备的,也不从最低级、最不完备的,而是从当中比较典型、比较发达、比较成型的形态讲起,特别是研究太古时代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方法有优越性。这在研究语音史的时候,特别有用。因为古代没有录音机,不可能准确记录古代语音的实况。但是,那些变化了的语音,在方言、在汉字、在诗歌的用韵,还有双声叠韵词语方面留下了很多痕迹,不过是分散的,零乱的。语音史学者可以把这些零碎的资料收集整理成系统。如果单纯从上古时代开始,距离太遥远,根据可能就很渺茫,也不容易准确,而仅仅从当代开始,又不利于往前推演。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抓住一个中间时段的成型期,比如唐朝的语音,将其声母与韵母、声调研究清楚了,往上一推到上古,往下一推到现代。我的老师王力先生研究古典音韵,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我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和美女,要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
英雄还是英“雌”?
我们从英雄和美女这两个字眼出发。
我还是把基本的观念弄得比较清楚一点。一个是美女的“美”,一个是英雄的“雄”。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学者们一直说“美”是“羊”和“大”的会意,“羊大为美”,也就是味觉为美的核心,许多中国学者,如李泽厚、刘纲纪、肖兵,还有一些日本学者都是这样看的。如果真是味觉为美,就只是生理的快感,给人的感觉,一言以蔽之:“馋。”“羊肉美酒”吃饱了,喝足了,就美滋滋,笑眯眯,连睡大觉,脸上都带着猪八戒式傻乎乎的微笑。口腹之欲的满足,是饱,饱的结果美不美呢?很值得怀疑。“饱暖思淫欲”,可知“饱”和“美”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超越生理的快感才可能有美感,“万恶淫为首”,吃饱了,倒是和丑与恶接近到危险的程度。
美食家,说是“美”,因为讲究“色”、“香”、“味”,充分发挥眼睛和鼻子的职能,舌头的感觉倒排在第三。重点是让你盯着看,凑近了闻。一动舌头舔,口水拉下来,姿态就很难美得起来。狼吞虎咽,吃相不好看;囫囵吞枣,有拉肚子的可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有失君子风度;从容一点,又怕人家说黄雀在看着螳螂,阴险毒辣。光是会吃,通俗的说法,叫做“好吃鬼”,福州人叫做“贪吃婆”。吃喝不应该属于“美”。一头小山羊看着很可爱,碰到个馋人,把它宰了,锅里一煮,吃起来是很不错,可是小山羊那可爱的样子、善良的眼神却没有了。哪儿还有什么情感的美呢?和以畜牧业起家的欧洲人、匈奴人不同,汉族人感觉中,茹毛饮血,一点不美,我们以神农氏后代为荣。六畜之中,据说,老猪在排行榜上位置不低。猪的体积比羊大,可不管比羊大多少,也永远是美不起来的。虽然闽南人把公猪,也就是配种的猪,叫做“猪哥”,那不是说它和自己有什么血统关系,而是说它“骚包”。
汉人的“美”,是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男子汉的“男”,就是人在田里出力。从美学来说,中国男性的力量是征服自然的勤劳,但是,光出死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还美不起来。农业这玩意儿,太不保险。水旱蝗疫,说来就来,种族绝灭,像影子一样追赶着人类。一场瘟疫来了,孩子都死得差不多了,人的再生产就比五谷丰登还重要得多。没有盘尼西林啊,也没有医疗保险公司啊,所以,《山海经》上,最大的女中豪杰,叫女娲,她唯一的能耐就是批量生孩子。不怕老天消灭多少,我就是批量生产,让你消灭不了。
生孩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一个女人所生,所育,极其有限。所以古希腊最早的维纳斯,并不像从米罗岛发现的维纳斯那样仪态万方,而是一个又胖又矮的女人,不过有一对硕大无朋的乳房,因为这个,她就成了当时的美女。恩格斯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说,需要巨人,就能产生巨人。这话真是有点道理。需要巨乳,也就产生巨乳。需要多生孩子,就能产生母亲英雄,中国的女娲就是用黄土造人。多方便啊!你想生一个孩子,十月怀胎,不能劳动,还得吃些酸梅汤,可是哪儿有啊,很难受,牙齿老是酸酸的,这还不算,处处得小心,不然,就流产了。就是临产了,还说不准要难产。生个孩子,等于在棺材边上转三转。多可怕!女娲所以是英雄,就是因为,她把生孩子的麻烦的生理过程简单化了,手工化了。但是,她的伟大,还在于,手工化转化成某种程度的机械化,一个一个造太麻烦了,用绳子一甩,泥点飞溅,孩子纷纷落地,省事多了。这可能就是荀子说的“人定胜天”,有人说荀子说得不对,“胜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以为,女娲生人例外。决胜的关键在于速度,你消灭得快,我比你更快,“速度就是硬道理”,在邓小平之前,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女娲就是理想主义的英雄加上美人。在《诗经》里,我们还有一个女英雄,叫姜嫄,也是英雄。她是踩了一个特殊的脚印,才生下了一个部族的首领的。
这表明了造人的英雄是女的,而不是男的。
我们中国没有留下当时女娲的形象,虽有画图,形象是和蛇有关的,但是,没有《圣经》中那个教唆人吃智慧果的蛇那么刁钻古怪,总的来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不够漂亮的。我们的文字所泄露的信息却是比较可靠的,“母”字,以女字为框,当中两点,乳房,能够生育,又能哺育,这就是很了不得的美人啊!世界上还有比养育生命更美的吗?还有“姓”字,是血统的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样的呢?——一边是一个“女”,一边是一个“生”,这是会意的,血统由来,就是女性生的。《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都是女性生的,这没有问题,但是,男性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可在“姓”这样一个重要的符号中,就被忽略了,就是说,男的没份儿。古代的姓氏很大一部分是与女子有关的,如“姬”、“姜”,这表明在中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是英雄,是生命的赋予者。这样的人,就是当时理想的、公认的美人。
学术研究表明,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可能是母系社会留下的痕迹。厦门大学教授詹石窗研究出来,道教经典里好多神是女性,比如西王母。他的结论是,中国有一段历史对女性的崇拜是高于男性崇拜的。
汉人的“美”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是羊与大的结合,羊大为美。
但是,近来中国美学研究有了突破,据我的朋友陈良运教授研究,古代中国人,并不是羊大为美食,相反,倒是以羊小为美食。所谓羊羔美酒是也。“羊”和“大”的结合,并不是美味的享受。从《易》的角度来解说,“羊”性情柔顺,生殖力强,“大”则为刚健雄强,是男性之意。上女下男,上阴下阳,在老祖宗那里,是男女阴阳交感为美(陈良运:《跨世纪论学文存》,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9—193页)。
这不是不要脸吗?但是,当时全世界的老祖宗都不知道要脸。古希腊和古印度原初的“性美学”,就美在不要脸,大家都不要脸,要脸的反而不美了。连孔夫子,据说,都是他老爸老妈野合而生的,也就是一时冲动,就有了旷古未有的美好的结晶。孟子引用孔子的话“,食色,性也”,不好色就是没有人性。要认真讲到美,最强烈的,就是色。因为它的刺激太强了,所以就不能不严加防范。偷东西吃的,可以原谅。贾琏偷养二奶尤二姐,被王熙凤发现了,这不是好吃,而是好色,所以就大闹一场,可是,贾母一句话,“哪有个猫儿不吃腥的?”把好色当作是偷吃,就开脱了。
要比生孩子的能耐,女性并没有多少优势,男性批量生孩子的潜在能量超过女性十万倍,可是就没有以生孩子为能事的男英雄,理由很简单,男性本来在这方面就够英雄的了,不是有句话叫做“雄起”吗?所以,最早的美学,就带有抑制男性的本能,性的冲动,本来就是够野性的了,再鼓励他朝这方面施展,一来怕地球上人太多,没法插脚,二来怕人和野兽也就差不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变成退化论。
所以,男性英雄在这方面受到压抑,那到什么方面去发挥呢?往力量方面去施展。最早的男英雄夸父,在逐猎美人方面,不让他有所成就,却让他在疯狂地追赶太阳方面大享威名。结果是渴死了。可是他的手杖,化为“桃林”。有一种解释说是舍己为人的表现:让后人在大旱时期解渴。另一个男英雄后羿,把天上十个太阳射下来九个。哪来十个太阳?不过是形容大旱而已。征服了大旱,当然是豪杰。但是,就是再大的民族英雄,也要抑制他的男性本能。大禹战胜洪水,有重新安排中国山河的丰功伟绩,可却让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对于女色,哪怕是对老婆(据说,老婆还不止一个,说是娥皇、女英两个美女,都是他老婆。中国诗史上最早的一首诗歌,据说是禹的妻子涂山之女为等候南巡的丈夫早日归来所作的情歌“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禹行水,窃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歌就这么一句),多年不见,一过家门,无动于衷,肯定是难能可贵的,而经过三次,都没有任何性的冲动,实在不是一般的英雄了。因而,就扬美名于千古。
所有这一切可能是说明,男女在美学上似乎是有分工的。女性管繁衍,多生孩子的就受到崇拜;男性则要遏制本能,不发贱,才能保证不让老天欺侮。
在老祖宗那里,男性的美学是力的美学,叫做阳刚之美。这一传统一直到中世纪传奇,都源远流长,如江河不废。关公、张飞、赵子龙,等等,似乎都有超人力量,但是,要问他们有没有老婆,可能比较难以回答,当然是有的,不然,关公的儿子关兴(一般认为,关平是义子,关兴是亲生)、张飞的儿子张苞,从哪儿来的?总不是老婆偷汉子生的吧。还有诸葛亮正准备出征,忽然一阵大风吹折了大旗,诸葛亮就悲从中来,泪流满面,说一定有坏事,结果赵云的儿子来了,报告说赵子龙逝世了。《三国演义》没有交代赵云有太太,但是也没有交代赵云像贾琏包二奶呀!
拿我们的神话和《圣经》来做比较,在创造人的业绩上,我们是母亲(女娲)英雄创造了人类,《圣经》里是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亚当是什么性别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亚当是男的,因而可以推知,上帝也是男的,如果说把希伯来文化和后来发展的基督教文化算在西方文化里的话,则似乎可以说,西方造人的上帝是男性,而我们的始祖则是女的。
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绝了。因为我们的汉字里,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祖宗的“祖”字。这个偏旁,在象形方面,是一个祭坛,而这边的而且的“且”字,则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的形象,里面的两横,就是包皮,很形象的。不要笑啊,我据很严肃的学者考证啊,它的确是在座男同学无论如何,都要遮挡起来的那个部位。这在今天来看,是很不严肃的,是吧?但在当时可能是很庄重的,是受到顶礼膜拜的。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崇拜的?可了不得啦!庙堂里那些牌位,包括孔庙里,祠堂里那些牌位,包括我们祖先的,为什么搞成那样一个样子?你们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它仿照而且的“且”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要向这样而且的“且”磕头的啊!而且这一磕,就磕了上千年。磕得忘乎所以,都忘记了这个而且的“且”原本是什么玩意儿了。甚至皇帝们称自己的前辈为太祖、高祖的时候,也忘记了,太祖、高祖的原初意义应该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太,可能就是天下第一吧,宇宙第一吧,太祖,就是天下第一生殖器啊!而高祖,就是高级的那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据考证,东南亚一带,至今仍然有拜石笋的风俗,石笋就是而且的“且”字的另一种形象,不过那个很庞大、伟大,而且,你们不要笑,我说的这个“而且”,不是那个“而且”,一般人,没有那么庞大、伟大就是了。而且,而且连讲“祖国”都感不到亵渎了。
一方面是女性的生殖英雄,一方面又是男性血缘祖先崇拜,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是,女性的生殖英雄在前,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后来到了父系社会,男性的生殖英雄才开始“雄起”,登堂入室,走上祭坛,发出神圣的光辉。
但是,这个男性的而且的“且”,有点矛盾,一方面是受到崇拜,可是另一方面,渐渐觉得,无遮无拦,怪害臊的。《圣经》上说,吃了智慧果以后,亚当就觉得这个而且的“且”,不太雅观,不用无花果的叶子把它给挡起来,就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路。这个办法很简单,可是只适用于日常生活,写成文字的时候,这种遮拦的办法却行不通。还是我们汉字厉害,就发明一种办法,把了不起的人,叫做花,花的功能,也是生殖呀。不过比那个而且的“且”,要漂亮好多了,是不是?不过这个花字,太直白了,不够含蓄,换一个文雅些的吧,“英”、“华”,都是花的别称。后来就集中在“英”上。
英者,花也。屈原的《离骚》中不是有“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落英,就是落花。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落英缤纷”也就是花瓣纷纷落地的意思。用“英”来形容人,就是说,像花一样,在植物生命中最为鲜艳、最为重要(生殖、传宗接代)、最为美好、最为杰出。现在我们说男英雄,就是男花瓣,女英雄,就是女花瓣,似乎是顺理成章。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英才就是最精华的、最精英的。孟子为什么只说,英才,而没有说雄才?因为“雄才”就不够全面,就不能把女英才包括进去了。英雄,英雄,一定要是雄的?有一个女英雄,叫花木兰。说她是女“英雄”,但,这是不通的。英雄,英雄,在原初的字义里,英雄只能是雄的,只有男性才能“雄起”啊!这是男权社会观念的普遍表现吗?是不是?
但是,不能孤立地研究问题呀,不能满足于单因单果的逻辑啊!这就要做比较。比如说,和英语比较,同样是英雄,就有一个男英雄(hero)一个女英雄啊(heroine)。俄语也是一样,读音有差异,词汇也是两个。而我们汉族,就很武断,英雄,就只能是雄的!那女英雄怎么办?花木兰怎么办?花木兰也只能是英雄,杰出的雄花朵。这是标准的汉族大男子主义!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今大学中学课堂上,总是读不懂《木兰辞》。老是情不自禁地把她当成英勇善战的男英雄。
我到一所中学听课,教师讲《木兰辞》,老师遵照所谓“平等对话”的原则,问花木兰怎么样?学生说是个英雄。这花木兰什么地方“英雄”啊?学生想来想去,回答说花木兰英勇善战啊……花木兰变成一个贫乏的概念。英雄就是英勇善战的。多媒体,朗诵,对话,花样玩得不少,可是学生看到的却不是文本中的花木兰,而是预期的心理图式中固有的男性英雄。
其实,在文本里花木兰是个女性英雄,作者设定的女英雄的特点,恰恰并不在英勇善战上。
我问,你说花木兰英雄善战,那么,这首诗里,写打仗一共几句?他说,“朝辞爷娘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是不是打仗?不像,写的是想家。他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打仗。我说,不是,这是行军。他又提出,“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是不是打仗呢?我说,这是宿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以说是打仗了。但是,第一,何其少也,只有两行,而且严格来说,只有一句。因为“壮士十年归”这一行,写的不是打仗,而是凯旋。就是“将军百战死”,也没有正面写她打仗,是别人牺牲了。打了十年,虽然后面有“策勋十二转”的间接交代,但是正面的,就这么区区一行概括性的叙述。她在战争中的英勇是全诗的重点还是“轻点”?战争场面轻轻一笔带过就“归来见天子”了?写战争这样吝惜笔墨,可是写她为父亲担心,决心出征,却不惜浓墨重彩。写了多少句呢?十六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然后写备马(从这里可以感到当时农民的负担是如何重,参军还要自己去买装备),四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接着写行军中,对爹娘的思念,又是八句:“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八句,想念爹娘的意思是相同的,句法结构完全相同,和前面的四句相比,只改动了几个字,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新信息。最多四行就够了,作者为什么要冒着重复的风险,写得如此铺张?奏凯归来以后,写家庭的欢乐,用了六句,写木兰换衣服化妆,一共十二句:“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如果作者的意图是要突出木兰作为战斗英雄的高大形象,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本末倒置了。
但是,这样的安排,恰恰为了表现文本两个方面的深层意脉:
第一,突出女英雄。本来,从军不是女孩子的义务,而是男人的义务,文本反复渲染的是,女孩子主动承担起男人保家卫国的任务,特点不在如何英勇,而是从军之前的亲情,立功归来以后,和男性享受立功受赏的荣誉,坦然为官作宰截然不同,她只在意享受亲情以及和平幸福的生活。女性的毅然担当,女性的亲情执著,女性的超越立功受奖的世俗功利,正是文本意脉的前半部分,文本意脉的后半部分,则是,恢复女儿本来面目的自豪和自得。两点一线,这个意脉是文本的生命线,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和老师视而不见呢?就是自发主体心理预期图式中的“英雄”同化作用。在汉语里“英雄”从语义的构成来说,“英”就是花瓣,杰出之义,而“雄”则为男性。英雄没有女性的份儿。而这里的英雄却是女性,顾名思义,应该是“英雌”。主题在女性从军立功与男性之不同,如果着重写英雄善战则与男性英雄无大差异。这一点,在文本的结尾处特别透露出来。中国诗歌是讲究比兴的,可是这首诗,居然几乎全是叙述,极少比喻,到了最后却来了很复杂的比喻。扑朔迷离,“安能辨我是雄雌?”隐含着女性对于男性的粗心大意的调侃和女性心灵精致的自得。这是全诗点题之笔,日后进入了日常口语,不是偶然的。
第二,经典文本的第三个层次,文体风格,蕴含着矛盾,统一而又丰富。一方面,在花木兰情绪的营造上,极尽排比渲染之能事,这是民歌风格。而另一方面,惜墨如金,百战之苦,十年之艰,一笔带过。表现了唐诗的成熟技巧。“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不但有精致的对仗,而且平仄在一句之内交替,在两句之间相对。这说明,民歌在长时间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同文化水准的人士的加工。最明显的莫过于,“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和“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留下的漏洞了。经典文本之所以不朽,肯定有它不同凡响、不可重复之处,自发的主体则以模式化的心理预期去遮蔽它。因而,阅读不仅要揭开文本隐藏的意脉,而且要从心理隐藏的现成预期中解脱出来。要真正读懂《木兰辞》,就要借助文本的信息,驱除现成的,空洞的英雄概念。用文本中微妙的、深邃的信息,推动读者内心图式的开放,从而做深度调整。孤立地强调自发主体,放纵封闭性,对汉语中“英雄”一词中蕴含的男性霸权就会视而不见,就只能感而不觉。
孔夫子讲究正名,中国这么多女“英雌”却没有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汉字里充满对女性的歧视,什么坏事情都是“女”字旁。比方说,奴隶的“奴”,妖怪的“妖”,明明《西游记》里,许多妖怪都是雄性的,可还是女字偏旁,谄媚的“媚”,娱乐的“娱”,其潜在预设,就是女性,都是讨好男人的,都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最不通的是“奸”字,汉奸,大都是男的,为什么一定要女字偏旁呢?更荒谬的是,强奸,也是这个“奸”字,繁体的写法是,三个女字叠在一起,就更不通了。明明是男性犯罪,写起字来,却全算在女人账上。对于这么普遍、这么多的冤案,居然没有人提出疑问,说明隐藏在汉字中的成见有多深了。
懂得一点儿人类文化史的人知道,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美国的女权主义却愤愤不平:英语里的chairman中的man就是男的,她们抗议,女的就不能做主席吗?!如果是女性当主席,改称chairw oman,要是主席还没选出来,不知是男是女,就改称chairperson,有时候仅仅抽象叙述一种现象和规律,并没有具体所指,怎么办?就干脆改称chair。这样她们就痛快了,感觉自己和男性平等了。其实,她们是把自己和男人一起贬低了,宁愿把自己当成椅子,也不愿让男人有任何优越感。
我跟一个女权主义者说,这种改变是可疑的。美国人重视历史,因为美国历史太短。从保存古董的角度来说,你们这种改变,不但好笑得要命,而且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文字是历史的积累的文化地层。你们可以改变chairman,但是history就不能改变。history就是his tory,就是男人的历史。改作 herstory,那就谁也看不懂了!文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博物馆。我说,你们(美国女权主义者)去篡改它,是粗暴的。你们美国西部乡村酒馆的墙上,上个世纪40年代的花露水瓶子就当做古董来展示,可对文字这么古老的文物,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层,你们的态度不够文明。我一边说,一边把汉字“奴隶”的“奴”字写给她看。我说,这边的偏旁,是个女字,它本身就是象形的,是一个人(侧面的)被绳子捆住了,就是“女”字,这边一个“又”字,是一个人的右手。一个被捆着,就是女人,另一个人的右手把绳子抓着,就是“奴”字。她问为什么被捆着的就是女人?我说,这是几千年前,古代嘛,部族之间战争是很残酷的。男人战死了一大批,没有死的,就被俘虏了,俘虏是要杀掉的。而女人则留下来,干吗?生孩子。女的不是要溜吗?就用绳子给捆起来。所以原初的“奴”字,就是留下来生孩子的工具。后来事情变化了,不仅仅有女俘虏,而且更多的是男俘虏,但是这个“奴”字,却一直没有改变。
这个女权主义者,大为兴奋,求我把所画的“奴”字,送给她,她说,你看看,从汉字里就有着女性受奴役的铁证。我说其实并不一定要从汉字里才能找到这样的证明,就是《圣经》里,不是说人类之所以要受苦,受难,都因为女人,因为夏娃,才被上帝逐出天堂的吗?还有古希腊的神话,人类本来生活在没有任何灾祸的境界,所有的病毒恶疾都被关在一个箱子里,在普罗米修斯手中。他把这个箱子交给弟弟,叮嘱他,绝对不能打开,但弟弟的老婆,漂亮的潘多拉很好奇,趁老公外出,偷偷敲开了箱子。结果里面无数的灾祸、疾病、虫害就冒了出来,人类从此就受苦了。我要说明,我说的是历史的偏见,不是我自己的观念。我是尊重女性的。在座的女同学,不要误会。就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心怀敬意。一些美国男性说美国女权主义者把性骚扰扩大化了,说女权主义者是“女性希特勒”,我严正声明,我不同意。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母亲就是女的,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否认母亲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