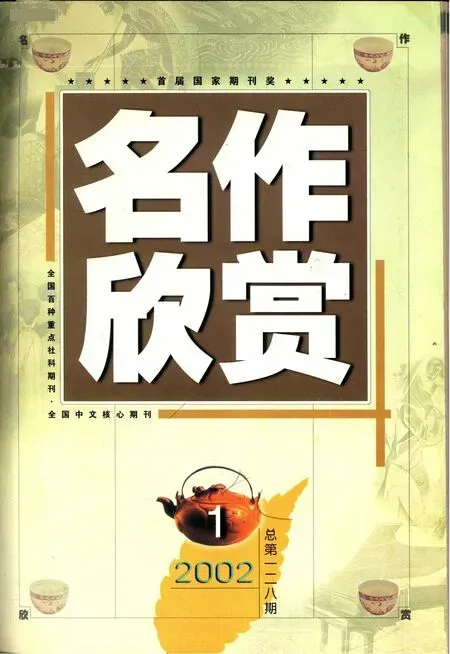从《静夜思》的意境创造,看“床”的字义选择——兼谈《静夜思》的时间地点
2010-08-15王琪玖
/王琪玖
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一句中的“床”,是作臥具(睡床)解,还是作井栏(井床)解,抑或是作“马扎”(交床)解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由来以久、聚讼不已的公案。此案并非由马未都提出的“马扎”说始,当然也并非能由“合阳方言”“一锤定音”。读二月十九日《西安日报》第七版《合阳方言能否解决床之争》文中诸多专家学者和网友关于“床”的说法,笔者深感一字之解,一诗之解之不易,而能为诸多读者所认同更为不易。
就“床”一字而言,笔者认为,诸多专家学者和网民朋友的见解,都可以称得上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特别是网友“小姨娘”的“一件事情的论证脱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伍永亮先生“研究有关历史文化,要懂关中方言” 之说,都对排解“床”字之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些都无疑大大有助于对“床”一字的理解。但是,笔者认为,对于《静夜思》中“床”字的理解,还是应该紧扣诗的意境,循诗人在诗的意境创造过程中的情感流变之迹,度情析义。通俗地讲,就是解字释词,辨义析疑,都要立足于诗歌文本的特定语境。只有结合《静夜思》的诗意、诗情、诗境来理解和把握“床”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床”字在这首诗的意境创造和诗意表达中的作用,似乎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床”字的字义及美学价值。笔者曾在2007年发表于《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的《李白〈静夜思〉意境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中反复强调,从这首诗的意境创造入手,援以例证,度以情理,庶几可以厘定“床”字的字义。笔者至今仍然认为,抛开《静夜思》的意境创造和诗意表达的美学特质,仅仅纠缠于某字字源意义的追索,难免会陷于“盲人摸象”式的“各执一端”的泥沼。近读《中华读书报》综述,得悉广州八旬翁陈云庵先生也认为,理解“床”字,应该从诗的构思意境着眼分析,笔者深感吾道不孤,所以愿贡献拙见于报端,就教于方家。
那么,从《静夜思》的意境创造这个角度来理解,“床”字到底是应该理解为臥榻(睡床),或者是马扎(交床)准确一些呢?还是理解为井栏(井床)更准确一些呢?我的看法是,就这首诗的意境大小狭阔、情感色调的浓谈冷暖和艺术美感而言,把“床”字厘定为井栏(井床)较为恰当。因为如果理解为臥具之床,那么就会把诗人的视域和情感域限定在斗室之内,诗的意境就比较狭小逼仄,诗的情感流动就会显得迟滞,诗歌情感意绪的跃动就会呈现出不尽情理的“拐点”。而理解为“井栏”,或者“井床”,那么,诗的情境、意境就会因之而呈现出高远辽阔的疏朗俊逸之象,诗情的流动、跃动,就会显现出清逸之姿,俊朗之态,其情感意绪,也就会呈现出“思而不哀,恸而不伤”的情感色彩,这是与李白豪放不羁的伟岸人格和雄奇飘逸的诗歌艺术风格相表里的。
我们先看如果将“床”作臥具之床理解,这首诗的情境、意境将是什么样的。按几成通识的理解,诗人李白是在客栈里的客房之内,辗转反侧(或者是走来走去),夜不能眠,不经意间,看见床前落满了明亮的月光,诗人心里暗暗起疑,地上怎么会落满了秋霜?抬头举目,啊,原来是明月的清光!诗人不禁低下头来,思念起了故乡的亲人。以上翻译如果大致不差,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是一幅室内望月思亲图。整个画面上,仅一屋一床一人一月而已,且人在室内,月在窗外,窗高月小人更小,这样的画境该是多么单调、逼仄、压抑!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狭小逼仄压抑的意境,轻浅淡薄的情感,会出自以豪放飘逸见长的诗仙之手,出自有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气度的李白的胸臆。
我曾经请数位画家朋友画此诗意图,均称欲在尺幅之内,构画其“思亲”意境,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为什么呢?欲画室内之人,则其屋不可全显,其窗不可全出;欲画室外之月,则室内之人难以全出。月,窗,人,床不可兼得,所以其意境难出。有数位朋友试着画了,但都觉得画意不能接李白之诗情,所以不肯示人。
除此之外,按以上的翻译,此诗在意境创造和情感意绪表达上也有几个不合情理处。
一是,如果月光是透过窗子落到床前的地上,作者怎么会怀疑是房间的地上落了一层霜呢?有过房间里落霜的事情吗?按照最基本的诗歌创作艺术规律,情因景起,象由心生,无论是“遥感”、“通感”还是“实感”,都是以现实的生活境象,或者是以诗人生存经验为基础而联想生发的,即所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所写的诗中的景、情,都是现实生活的“经验”的再现。那么,李白有过曾在某处看到过房间里落霜的“经验”吗?他难道没有秋霜只能起于山野田园的常识吗?怎么会在“恍惚之间”,把落在床前的月光“疑”为地上起的白霜呢?
二是,如果诗人写的是室内的景色,那么,“抬头望明月”一句就有悖于情理。因为以情理推之(姑且不论唐代是否是席地而居,或者是墙高窗小,我们假设床就设在窗前,作者坐在床上,或者是站在床前),月光从窗子里照到床头前之时(姑且也不论是否为落地窗,玻璃窗,或者秋夜是否大开窗扉),当是月上中天之时(否则月光就不会亮得让诗人会疑其为霜),那么,诗人抬头所望见的,只能是窗楣,屋顶,不是月亮(因为诗人不能平视,只能仰视),除非是他把头伸出窗外,方可望到。但这又似乎不大可能,诗人难道是先把头伸出窗外,看一下月亮,然后再回到床边,低下头来思念故乡?
三是,如果诗人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即便是能看见了月亮,那么他为什么会想起家乡?如果是月光引起思乡之情,那么诗人所望之月,是夏月,还是秋月?此时诗人身在何处?此诗是在长安时所作,还是在羁旅行役途中所作?
究其总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把诗中的“床”字的理解为客舍房间里的卧具所致。如果理解为井栏之“床”,上述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还会理解诗人为什么会疑月光为清霜,会因明月而思乡。同时,还能推定出这首诗是写于被“赐金还山”,礼请出长安之后的羁旅途中,诗中抒发的是诗人在中秋之夜伤己怀亲的情愫。因为,如果将“床”理解为“井栏”(井床),那么,诗人就不是在客舍的屋内望月思亲,而是徘徊在客舍院子里的水井旁边,触“井”生情,望月怀乡。诗的诗性画面上,客舍房屋就会成为诗的背景(衬景),明月、井栏(井床)、诗人,就成了诗的主景。月如玉盘,高挂银天,寒辉如霜,井床历历,山影绰绰,客舍低小,诗人问月,这意境何其高远清逸,空静疏阔!这诗情画意,岂不是要比蜗居室内,踌躇床前,临窗望月的意境更能传达出李白仕途蹉跎之抑郁之气,前途渺茫,思归不得的怀亲之意?
为了避免读者产生以上关于《静夜思》的意境勾画,只是笔者的“意”解,缺少文字训诂实证支持的误解,笔者就结合最近一段时间网友及纸质媒介上关于“床”字的讨论,援以训诂,度情辨析。
关于“床”字,据刘麟先生检索,在《李太白全集》中诗句带“床”字者大约有二十句,主要含义有三:一是卧具,即普通的床铺;二是坐具,如胡床、交床、绳床、交椅;三是水井的护栏。关于水井护栏的有如下例句:“去国客行远,还山秋梦长。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装。”(《洗脚亭》) 我认为,其中最能代表“床”作井栏(井床)来用的,是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中的“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句写的是一个小男孩手中拿着青梅,骑着“马”(一截小竹棍),和手中拿着花的小女孩绕着院庭的井栏追逐嬉戏的情景,描绘的是一幅天真烂漫、两小无猜的嬉戏图。“门前剧”就点明两个小孩子玩耍的地点是门前,所以“床”只能是门前,或者院庭里的“井栏”,如果是卧具的“床”的话,那就绕不成,难道这两个小孩子是由门前打打闹闹到室内,绕着睡觉的床追逐嬉戏?其二,除了皇亲国戚,富豪巨室,一般家户人家,是没有人会把床放置在房间中央的。退一步讲,这个“床”即便就是房间里的卧具,那么小孩子绕床追逐嬉戏,也就只不过是室内嬉闹而已,失去了户外活动的天真活泼之美。因而,此诗中的“床”为井栏(井床),应为李白诗作应用实例,可以佐证《静夜思》之“床”为井栏(井床)。
把“床”用作“井床”或者“井栏”,在汉乐府及李白同时代人的诗作中是很普遍的。如为网友和参与讨论的专家们所共引的唐朝诗人李贺《后园凿井歌》“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乐府诗集·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中“床”,都是“井床”而非卧具之“床”的明证。此外,周密《玉京秋》“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虫能说。”庾肩吾《九日侍宴》“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宝帐垂连理,银床转辘轳。广筵留上客,丰馔引中厨。”等诗中的“床”,都是做“井栏”解。从以上所引的例句来看,诗人们不但大都把“床”与“井”相配,而且将“床”做为一个有着特殊文化内涵的意象使用时,往往着一“银”色,使诗句有着一种清凉冷寂的意味。
除了“床”的字意理解而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作为“井栏”解的“床”在古代诗歌的意境创造当中,是一个有着深厚民俗文化内容的文化符号。在汉民族的民俗文化里,作为井栏的“床”即是“井”的同义词。而“井”则是家的同义词。因为,在农耕社会里,水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北方,家家户户都有水井,人们把“井”看成是家的同义语,离开家,就是离开“井”,离开“井”,就是离开家。成语“背井离乡”的意思,就是向井的相反方向走去,离开故乡。其中的“背井”,就是离开家的意思(吴裕成:《中国井文化》)。所以,如果我们从“井栏”、“井床”的意义上来理解《静夜思》中的“床”,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诗人会因明月而思乡——因为诗人由眼前客舍庭院里“井”边的月色,想起了自己家里庭院“井”边的月色,“井栏”边的亲人,“井栏”边的乡情,故而引出浓浓的思念故乡的情感。
那么,笔者把《静夜思》所描绘的景色的季节定为中秋节有什么依据呢?因为只有中秋时节是霜重露凝的季节。诗人流落异地,身居客舍,孤寂难眠,因而在客舍的庭院里的井栏边独自徘徊;此时正是中秋时节,风凉如水,月光落在井栏四周的泥土上,秋草上,清冷而明亮,所以诗人才会“疑”满院的月光是一层薄薄的秋霜。但是,仔细看去,却不是秋霜,而是月光。能引起诗人视觉错误的月光是如此的清冷而明亮,那么这时的月亮又该是怎么一种形态呢?所以诗人会很自然地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明月。明月到底是怎样的呢?诗中没有写,但可以推测,能洒落清冷明亮如霜的月亮,必定是大而圆,清而亮。此种月景,只有中秋节的月夜里会有。而中秋节,在中华民族的民俗里,是月圆人全的团圆节日,但是诗人呢?却身处异地,与家人分离,所以诗人才会因眼前庭院井边如霜的月色,而遥望明月,而起思念故乡家园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