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待师生与权贵的不同面孔
2010-08-06唐小兵
○唐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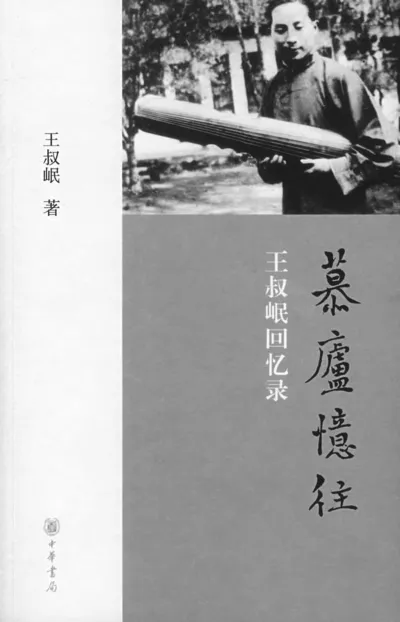
《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王叔岷著,中华书局2007年9月,32.00元
近日在长沙一特价书店捡得中华书局版《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闲读之际,对于庄子研究专家王叔岷记忆里的傅斯年形象尤感兴味。
出生书香世家的王叔岷本来是文胜于质的人,怀抱古琴,性喜诗词,骨子里是浪漫主义诗人;若不是青年时代偶遇傅斯年而走向学术之途,也许其人生之路会是另一番风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后,作为傅斯年入室弟子的王叔岷曾写下情深意笃的诗歌:“十年亲炙副心期,孤岛弦歌未忍离。点检缥缃余恸在,千秋风义忆吾师!”王叔岷先生坦承,自1941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因抗战内迁到长江北岸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到1951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执教的这10年,他在为人、处世、治学等方面均深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
王叔岷与傅斯年初识于1941年的四川李庄镇。当时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王叔岷刚刚被附属于该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傅斯年常驻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协助政府及教育学术界处理要务,秋冬之际回李庄。王叔岷与傅斯年的第一次见面可以说影响了其学术的取向:“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46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功,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傅斯年阅人无数,初次见面,就察觉到了王叔岷身上的才子气,也就是孤芳自赏甚至恃才傲物的文人气,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殊异,一生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傅斯年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学生“误入歧途”,因此对王叔岷来个当头棒喝,并且硬性规定其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这其实是民国很多学者在指导学生时的行规,流风所及,迟至1980年代,老一代学者王瑶、冯契等一样劝诫学生别急于出成果,要养浩然之气),并给王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即坐冷板凳,从校勘训诂等朴学途径入手研究庄子。王此前率性风流,写诗填词不亦乐乎,如今则在傅斯年规劝下别辟新途。从王叔岷后来治庄子的卓有所成,可见傅斯年的识人之慧。
抗战结束,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返南京,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的王叔岷也就搬到南京的峨眉新村。胡适从驻美国大使卸任回国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傅斯年也就回到南京指导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一天,傅斯年处理所务之暇,要王叔岷去讨论其著作《庄子校释》出版的问题。傅斯年让王叔岷将有重要创见的地方标识出来,阅读之后颇为欣赏。傅斯年提出给王书写序。王叔岷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我迟疑一下,说:‘不必。’隔几天傅先生见到我,又说:‘我跟你写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写。’我依旧说:‘不必,我自己负责。’傅先生爱护学生,顾虑年轻人的著作无人注意,所以才一再说跟我写序,我当然感激之至。但是我想,一方面我的著作,好坏应由自己负责,不必要前辈夸赞;一方面《庄子校释》是我第一部从事朴学的尝试之作,万一错误过多,岂不累及前辈。所以我不敢接受。”以“霸道”闻名学界的傅斯年激赏学生,并一再放低姿态愿为学生“做嫁衣裳”,居然被王叔岷这毛头小伙一口拒绝。不过细细咀嚼王拒绝其师作序的理由,却又不得不感慨民国时期学风之清正。名家写序,锦上添花,正可迎合青年人内心中炽热的名望欲,但竟不被刚刚出道的王叔岷放在心上,看在眼里,其学术上的自主与风骨可见一斑,或许也得自研究对象庄子的流风余韵?而王叔岷文责自负,担忧累及乃师的情怀,更让我们慨叹那时候师生之间至情至性的交谊。其时虽然西方大学制度引入中国已然半个世纪,但在研究生(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学科)培养方面,仍可窥见传统书院师徒制之遗泽。更难得的是,两次在学生那里碰冷钉子的傅斯年毫不为之挂怀,热情推荐《庄子校释》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9年,傅斯年随蒋介石政权迁移到台湾,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从实际出发,增建临时教室及宿舍,聘请优良教师,补充图书仪器。校外有些人故意攻击傅斯年,说花了政府那么多钱,表面看不出什么成绩。当时台湾政坛的大佬陈诚半开玩笑向傅斯年说:“你也买点石灰,把台大粉刷粉刷哩。”傅斯年笑着回答说:“还好,他们没有攻击我贪污。”据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叔岷回忆,当时有些达官贵人并无学术成就,想进台大教书,傅斯年立予拒绝。“有次沈刚伯(时任台大文学院长)先生笑兮兮地跑回文学院,说:‘你们快去看!’原来傅先生正接见一位贵人,傅先生口衔烟斗,两足放在办公桌上,侃侃而谈,那位贵人恭恭敬敬坐着在听。”学人在政客面前的风骨由此可见。被称为傅大炮的傅斯年先生一生正直,抗战后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更是震惊时人,没有这种风骨与自主,学术便很可能被权力侵蚀甚至收编,这样一来,学术便无自由可言,学人更无自尊可言。这种风骨,既可以理解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赓续,也可以解读成留学欧洲的傅斯年将西方知识传统中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引入了华夏。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正逢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那是一个依胡适所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百家争鸣时期,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师长辈倡导的现代思潮给了傅斯年精神上的滋养。内心世界的丰富,决定了个体的人格独立性。相对于在权力面前的铮铮傲骨,傅斯年在师生面前却是温柔敦厚,见到教师非常亲切,而“对学生最爱护,任何时间都可以接见”。
傅斯年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其行事方式常涉嫌乾纲独断之“独裁”,处事有担当,也有魄力,这似是中国国情所决定;不过,这种行事方式也招致诸多批评,比如认为傅斯年跋扈者不乏其人。与傅斯年情同父子的王叔岷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表面上看来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他舍己为人,不怕别人批评,这点要弄清楚。”王叔岷所忆及的一件小事可资印证傅斯年的公私观及其实践。1950年代的台湾大学,只有校长与总务长才有汽车,当时傅斯年的太太在外文系教书,到校及返家都搭公共汽车。总务长太太去世后,追逐文学院一位护士小姐,假日载她外出兜风。傅斯年知道了,警告他:“你要知道,汽油是人民的血汗!”正是在傅斯年的领导和影响下,筚路蓝缕的台湾大学校风正气盎然,声望日益提升,学术水准更是蒸蒸日上,成为延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血脉之正统的高等学府,为台湾的政治转型、经济发展和学术繁荣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王叔岷在傅斯年先生去世后所写的一篇哀悼短文中的一段话很精到地概括了傅斯年的人格与人生:“并世学有成者不乏其人,然多趋于鬻声钓誉,未必有骨气也;有骨气者,又多流于孤介冷辞,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气、治学,三者兼备,其惟孟真师乎!”以传统之标准,傅斯年先生一生在道德、学问与事功三个领域都卓有成就,可谓后世学人难望其项背也。不过细细想来,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文中所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细绎傅斯年的一生,其独立之人格、伟岸之精神也许相对其学术造诣和事业成就,更能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