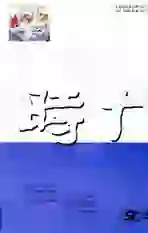对一个新女性形象所做的症候阅读
2010-06-28罗燕周蓉
罗 燕 周 蓉
摘要:萧红小说<弃儿)申的芹舍弃做母亲的权力而投身时代洪流。这是一个被她的爱人赞叹的新女性。但以阿尔都塞的症侯阅读法对(弃儿)进行症候阅读,不仅,芹的新女性形象是一个假象,缺乏主体意识妁觉醒,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期待;而且,这个新女性形象还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她内心真实的感受与她的所言所行是脱节的,个性处在分裂申,
关键词:阿尔都塞;症侯阅读;萧缸;弃儿;新女性形象
在(弃儿少中,几被社会所遗弃的芹,在蓓力眼里,是一个奇女子,是时代所需的新女性,值得终身相伴,她不愿嫁与有钱人,她现在窘迫处境是她自我选择的而不是那个有钱人抛弃她的结果。她离开了他,她自己选择了被抛弃的命运,她穷困到不堪的境地。灵魂却拥有圣母的庄严。面对这博大的女性心胸,蓓力被她征服。她激起了他的豪情,她正是他要找的那个与他有同样激情的女子:为了信仰而甘愿置身难中。店主眼中的芹,其形象是很糟糕的,未婚,大肚。被弃。他鄙视这个道德行为败坏的女人。非的妻子对芹满是不屑,未婚大肚又衣衫槛楼。在医院里,芹决定把孩子送人。因为她不能抗拒使命的呼唤,她是为时代而生的,她不能自私到只想到自己的孩子。冠冕堂皇的理由,她的形象瞬间在医院中变得不可理喻的神秘。追根溯源,芹的形象在他人眼中差异如此巨大都源自于她与那个有钱男人王先生同居而怀孕大肚。
王先生是神秘的,他没有在文本中出场,但每个人都对他不陌生,他是蓓力不屑的有钱人,却是店主佩服的对象,也是看护妇羡慕的好的结婚人选。可对他持漠然之态度的芹,似事不关己,好像与他从无往来。婴儿也是生出来就送人了。芹竭力与他不相干。的确,芹似在回避她的从前,因为它在文本中没有被提及,浓墨重彩的是她与倍力风云激荡的人生,倍力对她的侠骨柔情,她与倍力的志同道合。这样的叙事倾斜不是用叙事策略可以一笔带过的。因为文本未被说出的始终是重要的,这不在文本中被表述的又始终制约着文本。
阿尔都塞的症侯阅读的批评模式就认为“空白…‘沉默”是文本的意义支撑之所在,只有找到文本中意义矛盾和断裂之处,因它像地壳的断层,就能够使‘沉默”说话,从而,看见、感觉或体验到,某些‘指涉现实的东西,”I:I就可以获得现实的真相。现实的真相并不能在直接阅读文本中获得,只有通过症侯阅读才可以。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意义的矛盾和断裂的“症侯,之解读,文本说出了它没有说出的真相,令人费解的芹之形象才回复平常,芹之言行:把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命运归结为自己穷困的托辞;同意倍力的观点但又投有表达出与他同样愤愤不平的附和;把婴儿送人后认为多数小孩获救目的达到了的呓语;婴儿是送人而说成是丢掉还梦见院长杀死了婴儿这些口误和梦,闪烁其辞与义无反顾并存,显观了意义的矛盾和断裂,沉默不语之处被迫道出文本“不能说、不敢说、不便说或想不到要说的东西,”r21以形象的奇异性、神秘性取媚倍力以摆脱尴尬的处境,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任人宰割到豪气万丈,文本的沉默道出了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的悲哀的人世处境。新女性是她的面具,没有这个面具,她将被男权社会视为异端无处存身,有了这个面具,她就是男人眼中的女神,光芒万丈,但是芹的真实形象,始终并不被这个面具改变,她仍是一个卑微的他者,是第二性。
女人的人世处境全然不同于男人。普鲁斯特说过:‘只有经过所有的可笑丑恶之现形,他才有把握在可能的范围变成一个贤哲,”明智不能接受而来,必须自己去走一段路亲自去发现,任何人不能代替我们去走,不能免了我们这趟差,因为明智是对事物的一种观点。“FJI~S')而能够谋划走向自身存在的自由举动只是男人的特权,男人可以自由地经历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探索自我揭示世界,可以体味到孔子所言的人生智慧“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而女人的自由并不被承认,她仅只是男人的“抗衡”、“拯救”、“历险”、“幸福”,lQoQo‘,认定她是超验存在的女性神话“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的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r<(10Q0,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这预定的形象先于她尘世命运的展开,她只能是其所是而不能是其所不是。
在最难堪之时与蓓力相识的芹,大肚、被弃、欠债,她的人生已有太多不可更改的事情发生,其糟糕的形象根本相左男性对女人的想象。这个被弃的孕妇心境那么转辗苍凉,在岁月中流逝的她的过往并不能成为他爱她的资本,她的经验反而成为她超越的阻碍,她被男权社会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不得超生。为了让自己再次符合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与蓓力一起时的芹,她妩媚,她含情,她活泼,她激进,与在旅店里人为刀殖我为鱼肉的被动的形象大不一样。这柔情似水、热情如火的女人形象密不透风地窒息着那个大肚子女人那个被人抛弃的女人那个有道德污秽的女人。她要用蓓力没见过的爱来爱他,是因她绝望地想要自己忘掉她的“挂碍”,她不要有她自己的过去,要用她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把蓓力融化在她的爱里,让他沉迷,只记住她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他们的未来,把他的心占满,把他的时间填满,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她的,而是相反,自己能被他所有。芹之所说所做就是为了让他听到看到她,而他也确是从他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里看到和听到了他想要的所有。这在他的注视下的女性形象。是如他所期望的那么勇敢,如迎风博击的海燕。这是他认可的形象,满足了他的女性神话的情结。
如此,离开有钱人放弃婴儿,心怀着天下民生的忧患。这都只是她的做秀,是为了掩饰她过往的历史,而这是她的污迹。这样慷慨激昂的芹,这样追随蓓力投身时代的芹,人生选择看似热切而真诚,有着不顾一切的决绝,其实有着最谦卑的顺从。只是为了取悦他的品味,她选择成为时代儿女,成为新女性,却并非反思自己的处境而行动而抗争,并非“意识到自己在解放她人的行动的同时清楚地认识自己,并作为经历到自身的解放之人在行动”。没有主体意识觉醒的新女性成为主体浮出历史地表是假象,但犹如盾牌,屏蔽着芹的真实形象,对于这样形象的芹,沉默是其唯一的藏身之地。
芹找寻到爱与信仰后,软弱涣散的精神状态彻底消失了。她的出院,确如战士凯旋,新的世间新的人生在她面前展开。一个全新的芹,一个新女性在结尾出现,与开头困在旅店里的芹是完全两样。她获得了爱,有了爱人;她认识到世间的不公,要做一个战斗者。可是,这种线性阅读,“即不对其所阅读的对象提出问题,而是把所阅读的著作当作现成的东西。这种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来阅读一样,”,q陷入了认识的自映神话。这是阿尔都塞反对的,因对文本的直接阅读不能获得现实的真相,文本中,在非家,芹感受到了非的妻子的冷言冷语中所表现出的鄙薄与排斥,这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对她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芹在其优越感中,无地自容,但她对右力所说的是,这个女人势利以貌取人因她的穷。在医院,她梦见院长杀死嬰儿,却对倍力说:“丢掉一个小孩于是为了多数小孩子要获救”,她不能成为自私的人,她内心的感受没有告诉倍力,她的心扉在倍力面前是关闭的。她只在他面前
做小鸟依人状,做斗士愤慨状,这么多意义的矛盾和断裂的“症侯”,又本说出了它没有说出的,被所有人视为与众不同的芹,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这就意味着,这个新女性形象的自我是分裂的,她的所说与她的所感是分裂的,她内心的愿望与她的所做是对立的。她自谓的新只是皇帝的新衣,夸张而做作。
因为与王先生同居、懷孕、被弃,芹的人生几乎全毁。她改写她与王先生的同居真相,她说出慷慨激昂的誓言。都只是为了鲜亮地站在蓓力面前,与他一起去闯荡、开拓。这都是她为有新的开始做出的绝望的努力。这个新形象赢得了蓓力的认可,视她为自己忠实的伙伴!这其实是对自我的逃避,是对自我的无情鄙薄与否决。文本一再地写她的生活困境,一再地写她所受的磨难,不是为了对造成她的命运如此多艰的那个王先生的谴责与唾弃,而是为了突出她的阶级觉悟还有她患难之中的爱情,突出她灵魂贞洁的质地。阶级话语的崇高性既修辞了一个女人难堪的经历也置换了这事件的性质。叙述抹去了芹的个人遭遇,也阉割了一个女人血泪的人生。因此,让蓓力的血在沸腾的芹,与蓓力携手前进的芹,可说灵魂已被掏空,虽说她让蓓力激动的是她的灵魂的阔大。她的真实自我“隐藏在一个群体之内,闷死在一个关系当中,消失在某种团契里,”)那七个月她所经历的被她压抑升华为阶级经验,在话语的虚幻中寻求庇护,要用宏大的话语叙述隐匿她自己,否决自己的人生蔑视自己的女性经验。她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真实的内在自我不被他人看见,也置她真实的内在自我于沉默不语中。“结果导致个性的极度分裂:一个是被男性世界注视的客体一自我;另一个则是退缩的、看不见的自我——有时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的自我。”
“当女人把她自身视作客体时,她会为她的有形自我——她的肉体——所困扰,并为迫使自己的身体顺应男性所定义的美而苦恼。”因她认同父系文化所塑造的镜像。芹的身形体貌是对父系文化所塑造的女性偶像的冒犯与亵渎,她憎恶它。她用客观的物象来描述自己对身体状态的感觉,把自己怀孕的身体物化非人化,流露出不可遏制的厌恶,从没感到孕育生命的美好。她把自己怀孕的肚子看作是外在的事物,是个她无法控制的丑陋的异在。身体是肮脏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知情的物证与蒙羞的标本,耻感主导了她。当她如此感受时。她的身体所遭遇到的一切都被她毫不犹豫地删改。被店主催债,被饥饿折腾,她的大肚子,“每日她烦得像数着发丝一般的心,”她自己都羞于记起提起。羞耻感完全淹设了痛感。被羞耻感深深主宰了的芹只能自己更讨厌自己而对男人却不能愤怒起来,愤怒转向了她自己。被男人无情地弃之不顾,他对她没有任何的忏悔与顾惜而是毫不留情到残忍,经历了那么多人世冷眼的芹却根本想不到声讨他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她承受了所有的恶果,怀孕、生子、弃婴,可是她却把愤怒对向了她自己。在羞耻与愤怒的夹击下,芹的反应就近似精神分裂者。她的情感体验是复杂难言的。她讨厌怀孕的大肚对婴儿冷漠无情,因这一切让她处在泥招里无力自拔,但在丢弃婴儿时,内心的争斗、母子之情的留恋、眼泪全都涌上心头折磨她。这都是她真实体验。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对人说起,这些真实的感受她秘而不宜,只在独处时独自咀嚼人生的五味杂陈。而在人前,她把自己打扮成圣母样以圣母自居,送出自己的婴孩,只为拯救苍生。被社会认定是道德败坏者的她只能以男权社会认可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倍力面前,只能以这样让倍力赞叹不已的方式使真实的自己不被他人看见,那个经历了悲苦辛酸人生的真实的自我就只有被放逐永不会回归到她自己。可怜的女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与社会行为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取悦那些必须取悦的人。”
这就是性政治中的女人,掩饰自己的客观真实,藏起自己的真实情感,只有虚假的自我,她的体验因而是如精神分裂一般地被撕裂。苏珊,格里芬认为因为女人没有真正的传统可利用,女人只有虚假的自我可以仿效,所以“我们似乎都天才地成了我们所不是的人”。
结语
基于父系文化对女性自我的绞杀,西苏曾大声疾呼:“女人必须通过她们的躯体来写作”,女性的写作“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必须性别在场,用自我书写形式传达女性的真实体验,见证与表达女性自己生活的真相。由女性作家所写并还带有自传痕迹的<弃儿),虽缺乏性别意识,这一文本仍以它自身的不语、沉默启示着女性写作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之意义,具有性别立场的女性写作,与风花雪月无关,它是使命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