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策略的新变
2010-05-11马伟业
马伟业
如果有人撰写中国新式小说的艺术演进史,当他写到当代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新变时,他肯定会兴奋不已。因为他会发现,中国新式小说的叙事艺术在进入当代文学史阶段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竟然新法迭出,花样翻新。诸如意识流、黑色幽默、象征、复调、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等新的叙事艺术都纷至沓来,争奇斗妍,使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新式小说在艺术上不再像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阶段那样单一甚至单调,而是变得丰富多样起来。而在这新出现的丰富多姿的叙事艺术中,有几种方法不曾以自身的招摇引起过人们的特殊注意,而是以更潜隐更踏实的姿态默默运行着,那就是设谜人物、孪生故事和反观视角。它们虽未受到过太多的热捧和经历过太多的繁华,但却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留下了全新的印记。
一、设谜人物
假如我们从艺术演进的角度观察中国的新式小说,就会看到,当中国新式小说进入当代文学史阶段以后,有一种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崭新艺术方法突然出现了,那就是有些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故意设谜,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都呈现出明显的谜语性特征。他们在进行构思时,既设计一个具体的人,又设计一个或多个与之相似的人,让作品中的叙事者在辨认时发生误会,使他觉得此人既像某个人,又不是某个人;虽然不是某个人,但在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又与某个人如出一辙。有的作品最后揭出了谜底,确认作品中的此人不是某个人,而是另一个人;有的作品则最后也没有揭破谜底,不知道此人是否确系某人。在这些作品中,那个具体的人与他的相似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谜语关系。这种故意设谜的艺术最初出现在“十七年”间,它的始作俑者似乎是著名作家茹志鹃。她在《高高的白杨树》中,叙述一个战争年代的女护理员“我”在建国后去寻找当年的同事、大姐张爱珍,“我”到大姐的家乡张家冲寻找她,但找到的却不是当年的大姐张爱珍,而是一个养兔姑娘张爱珍,同时还听说附近有个种麦能手也叫张爱珍。养兔姑娘虽然不是当年在战火中冲杀的大姐,但整个精神世界却与当年的大姐一脉相承。“我”在这里没有找到当年的大姐,却从夏书记那里听说了在过去年代一个女孩小凤儿的往事,“我”突然觉得小凤儿就是离家出走参加革命队伍之前的大姐张爱珍,但夏书记却说不是。这样,作品在大姐张爱珍与养兔姑娘张爱珍之间,在大姐与小凤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谜语式关系。此后这种人物设谜的方法也被其他作家所运用。当年曾经一度崇拜并有意学习茹志鹃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短暂复出中写下的《眼睛》,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小说写一个大学毕业生苏淼如在作乡村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时,在秋收时节,遇到一个女孩儿来借《红岩》,并说她们的团支部准备组织团员学习《红岩》以配合秋收。这个女孩儿的一对眼睛引起了苏淼如的特殊注意,他觉得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林燕子,因为她的“雪亮的、充满热情的、望得很远又很坚定的眼睛”跟林燕子的眼睛一模一样。他深为自己在图书馆已无此书可借的情况下没将手中留给恋人的这本书借给她而遗憾。后来有人对他说,那个姑娘不是林燕子,而是另一个农村姑娘。即使如此,苏淼如仍然觉得她同样令人敬重。小说同样在农村姑娘与林燕子之间制造了谜语。其实,在“十七年”间,不仅小说家在运用这种设谜的艺术,甚至电影艺术家也在运用这种设谜艺术,著名影片《五朵金花》就是明证。在“文革”后期出现的某些叙事作品中,作者们仍然沿用着这种方法,《乌兰其其格》、《雪莲》等等都是如此。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设谜艺术虽然未受到过更多作家的垂青,但仍然有人在沿用它,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小说《二月杏》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小说叙述了 “文革”开始时中学生大亮为了能加入 “造反队”,便狠心地抛弃了与他相爱着的出身富农家庭的女同学二月杏,给这个少女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15年后,已经成了地质队员的大亮在一个镇子里意外地遇到一位与二月杏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他觉得她就是当年的二月杏,但她却矢口否认。她说自己不是他说的那个二月杏,但大亮却发现她的身世经历和心灵伤痛与当年的二月杏十分相像。直至作品结束,读者也未最后弄清她究竟是不是大亮当年的那位女同学二月杏。这样,在两个姑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谜语关系,而且谜底始终未被揭破。可以说,故意在人物形象上设谜,是当代某些作家曾经热衷的艺术方法,也是中国新式小说在进入当代文学史阶段后,在艺术上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方法。那么,这种全新的叙事方法为这些小说带来了怎样的艺术效果呢?
这种新的叙事方法为作品带来了强烈的隐喻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作家在创作时都有一个明显的社会目的,那就是或者为了歌颂,如茹志鹃、王蒙的作品,或者为了批判,如贾平凹的作品,但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作家都想强化他所写的人物和生活的普遍性,以此向世人证明,他写的人和事绝不是个别的单独的存在,而是涉及很多人的广泛的普遍的存在,以此增强歌颂或批判的力量。为了表明他们所写的人和事具有普遍性,他们不仅写某个人,而且还写了一个或几个与之相似的人,使彼此之间形成一种谜语关系,这样作品中的人就不仅是某个人,而且也是某类人,非常便利地向读者证明这种人和事确实普遍存在着。这样,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人,无疑具备了一种隐喻性。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建设者的,她既写了战争年代的张爱珍,又写了建设年代的养兔姑娘张爱珍、种麦能手张爱珍,让三个女性名字相同,以此在是否同为一人的问题上出现谜团,于是张爱珍既是具体的个人,同时也成了同类人的代名词,是一个隐喻。作家通过这个人物仿佛在告诉人们,从开创新中国到建设新中国,像张爱珍这样的奉献者何其多也!在此之外,作家又设置了张爱珍与小凤儿的谜语关系,进一步揭示了这类人成长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使作品所写的人和事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增强了作品的歌颂力量。王蒙的《眼睛》也是如此。作家意在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他既写了模范人物林燕子,又写了一位与之相似的农村姑娘,在这位农村姑娘与林燕子是否同属一人的问题上制造谜团。在两者的极其相像中,表明整个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林燕子式的先进人物,以此强调作品所写的人与事的广泛性。于是,在这里,林燕子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她也成了一种隐喻。贾平凹的《二月杏》的创作意图在于批判“文革”给广大民众造成的灾难,进而控诉“文革”的罪行。他既写了心灵受伤的大亮的同学二月杏,又写了一个与她相似的姑娘。两个二月杏构成了谜语关系。她们的相像甚或相同向世人表明,当年大亮的二月杏所遭受的不幸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从而加深了对“文革”批判的力度。这样,二月杏也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她也成了隐喻。由此可见,这种设谜人物确实都有极强的隐喻性。
这种人物设谜的艺术方法也为小说增添了趣味性。趣味性对于一篇(部)小说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小说毕竟不是必读文件,不是操作须知,不是农药说明”,“人们读它首先是因为它有趣”。那些有经验的作家总是设法“把小说写得更有趣”(王蒙:《漫话小说》)。而人物设谜的方法无疑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因为它们都存在着 “差头”,都出现了“误会”。而误会在生活中是趣味生成的重要条件,当一个人误把张三当作李四的时候,其结果必定是有趣的甚至是可笑的。《高高的白杨树》中的“我”来找大姐张爱珍,打听到了一个叫张爱珍的人,“我”便以为真的找到了要找的大姐,待到见面,却发现她是另一个人,一个与大姐张爱珍年龄差别很大的姑娘。这个误会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趣味。《眼睛》中的苏淼如把一位农村姑娘当成了著名人物林燕子,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还特意手捧《中国妇女》这本杂志,认真盯着上面刊印的林燕子的照片,反复端详辨认,越看越像,于是认定那个借书姑娘就“是她”!然而后来别人却告诉他那位姑娘真的不是林燕子,他误会了。他误会了,作品的趣味也就出现了。当年著名评论家黄秋耘先生在读过这篇小说后特别指出,“最后证明女主人公并不是林燕子,这使小说不落窠臼,颇有意趣”(王蒙:《半生多事》)。这位著名批评家当年的“接受”事实也证明着这一点。《二月杏》中的误会同样为作品增添了情趣。大亮把在一个小镇上见到的姑娘当成了他当年的恋人二月杏,但这个姑娘却说自己不是那个二月杏,这一“误会”同样让人感到妙趣横生。正是这些“误会”使作品不断节外生枝,趣味频仍,在它们所写的生活所表达的思想早已随同那页历史被翻过去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兴味盎然。可以设想,假若不是如此,作家当初在创作时不做这样的设计,让寻找张爱珍的人随后真的找到了张爱珍,让被认定为林燕子的姑娘后来真的成了林燕子,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小镇上出现的姑娘后来真的成了大亮的二月杏,其结果也许会有另一种风云际会,演绎出另一种人间活剧,而且这样的作品也不无新意,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创造出这种情趣美!
这种人物设谜的方法,还为作品创造了一种朦胧美。朦胧美同样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感类型,而且是一种很高的美的境界,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都有意追求这种境界。人物设谜的方法无疑为作品造成了朦胧美。因为它写的几个相似人物之间那种似是而非、似真实假的关系,本身就显得云里雾里,迷离恍惚。在当年的大姐张爱珍与养兔姑娘张爱珍,种麦能手张爱珍的似而不是的关系中,就有一种迷蒙感。特别是在大姐张爱珍与小凤儿的关系上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两者是否同为一人始终是个未解之谜,谜的存在使作品笼罩着一层迷蒙的轻纱。林燕子与农村姑娘的似而不是,在苏淼如的心里曾经是个谜,在读者心中也曾是个谜,虽然最后谜被解开,但在整个展开的过程中却让人觉得朦朦胧胧,因此作品也就产生了一种朦胧美。最能说明这个特点的还是《二月杏》。大亮当了地质队员后,在异地他乡的树林里意外地遇到一位姑娘,当他看到姑娘的眼光后,不仅大惊失色地“啊”地叫了一声,因为他发现“这是何等熟悉的眼光”!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眼前的这位姑娘肯定是在“文革”开始时被他抛弃的二月杏。他满以为姑娘肯定能认出他,但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认识”。在随后的接触中,他仔细端详了“她的头发,眉毛,鼻子,嘴巴,腰身”,发现果然“这不是那个她”,“自己果真是认错了人”!至此,读者以为这个女性绝不是大亮的女同学二月杏了。但紧接着,她的“一个笑”又“使他骤然间又证实了这种笑就是他的那个她的笑容”,事情仿佛又出现了转机,以为她可能是大亮的同学二月杏。但当这次分手时大亮在后面叫了一声“二月杏”的时候,她却回过头来说“你说什么?”证明她又不是那个二月杏了。但当大亮前去她的酒馆喝酒时,正逢酒馆人多,做招待的老太婆赶大亮走时,她却像对待多年的熟人那样制止了老太婆,让大亮留下喝酒,并问他“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似乎她又是二月杏,她不仅认识他,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此后的叙述中,读者也仿佛觉得她就是二月杏:大亮托人带给她两百元钱和“十几片无香无色而洁净完好的杏花”时,她病了;大亮在电影院前遇到她,她早已买了两张票,好像早就知道大亮会来似的;看完电影走出剧院门口时大亮在她后面喊了一声 “二月杏”,“她一个趔趄站住了,回过头来,突然满脸泪水”,此后她还让大亮在树下等她。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感觉:她果真是大亮的同学二月杏,她肯定要跟大亮破镜重圆,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她远嫁他方,走了!那么,她究竟是不是大亮那个二月杏呢?最后也让人无法断定。是与不是之间的模糊,创造出一种朦胧之美,真可谓“是花还是非花”!
总之,这种在人物形象上故意设谜的方法,是当代小说艺术的一大创新,它为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新面貌。
二、孪生故事
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一篇(部)小说只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尽管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也许套装着很多相对独立的故事,但它们却都统一在一个大故事中,中国古代的小说是这样,19世纪以前的西方小说以及这种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被引入中国后所繁衍出的中国新式小说也是这样。在中国新式小说的历史上,从它发端那天起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都走着这样的路。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那就是不论是长篇小说创作,还是中短篇小说创作,某些作家都在一个作品中同时写进两个独立的故事,有的作品中的两个故事在人物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有的则毫无联系。在这些作品中,故事都呈现着双胞胎婴儿的特点,它们是孪生的。邵振国的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麦客》,就是人物有某种联系而两个故事则完全独立的小说。作品既写了父亲吴河东当麦客为人割麦的一次经历,也写了儿子吴顺昌当麦客为人割麦的一次经历。两个故事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起承转合。霍达的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如此。作家在这个长篇中,同样讲述了两个彼此独立的故事,一个是“玉”的故事,讲述的是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的婚爱悲剧;一个是“月”的故事,讲述的是韩新月、楚雁潮的爱情悲剧。两个故事中的人物尽管有一定联系,但彼此又各自独立。而古华的引起过争鸣的中篇小说《贞女》则讲述了两个在人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故事,一个是“清末一个年少寡妇守节不贞的故事”,另一个是“当今一个年轻女子不守节倒又甚为贞洁的故事”,“两个故事互不相关”(《贞女》第一章)。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作家本来可以把两个故事分别写成两篇(部)完全独立的作品,此时乃至此前此后的绝大多数作家也都是这样做的,但霍达等人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两个故事共栖于一个作品中。这种构思和结构方式,可能是受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引进的复调小说创作及其相应理论的影响,但它们却不是复调小说。因为复调小说是在一个作品中回响着两个以上截然对立的声音,是将 “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同时摆在一个平台上”(米兰·昆德拉语)。中国这些作家不仅没有追求不同声音的同时出现,而是始终保持音调的和谐。既然不追求复调,又把两个故事装在一个作品中,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作品带来了怎样的艺术效果呢?
实际上,只要做些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叙事方法的好处首先是增强了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的纵深感,使作品的内容获得了厚实的底蕴。对此,古华曾做过直接说明。他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品的两个故事虽然“互不相关”,但它们“却交错渗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作品的“历史纵深意识”(《贞女》第一章)。其他作家虽未明确道破初衷,但无疑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尽管两个故事在人物和情节上“互不相关”,但在精神内涵上“却交错渗透”,它们一旦被组合在一个共同体中,便把出现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活连为一体,彼此形成互为参照、互为渗透、互为拓展、互为丰富的多重关系,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的历史纵深感,在意蕴上远比单写一个故事要丰厚得多。《麦客》写的是已经绝迹多年、在新时期重又出现的麦客生活,邵振国将两个故事写在一个小说中。作为老一代麦客的吴河东的这次麦客遭遇,无疑带有历史上传统的麦客生活的特点,他所遇到的顾主张根发也与历史上敲骨吸髓的地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他儿子吴顺昌的这次麦客经历,更带有新的时代里和新的环境中新一代麦客生活的特点,他的顾主水香也是人性开始觉醒的新一代人,两个故事组合在一起的结果,是互为拓展,展示了麦客这一古老职业的过去和现在,使作品获得了深邃的历史感。《贞女》更是如此。杨青玉的故事发生在前清,作家在这个故事中,讲述了历史上一个被传统文化中的罪恶的贞洁观念的绳索捆绑致死的女性的悲剧;姚桂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现实中一个被贞洁观念压迫的女性的悲剧,两个故事人物情节毫不相关。将两者组合在一起,却又互为拓展,既让人看到了这种文化在昔日肆虐的真相,也看到了它在今天仍然残存着的景象,以及正在逐渐丧失威力的事实,从而使作品形成很强的纵深感。《穆斯林的葬礼》中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悲剧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它揭示了历史和命运对人的捉弄,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悲剧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它揭示了文化与命运对人的捉弄。两个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故事的组合,互为拓展,使读者在更开阔的视野里看到了社会和命运给生命个体制造的灾难,作品也无疑形成了纵深之感。也就是说,孪生故事大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它远比单写一个故事使作品深邃丰富得多。
在这类作品中,两个孪生故事除了有相通处之外,还有相异处。如果说相通处增加了作品的纵深感,那么相异处则使两个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性。而在文学作品中,对照既可以使事物的特征更为明晰地凸显出来,也可以使两个事物构成互相映衬、各美其美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孪生故事之间就具有这种对照关系。《麦客》中吴河东的故事与顺昌的故事在对照中显示了各自的特点,那就是吴河东的故事涂上了旧时代旧生活的色彩,而吴顺昌的故事则染有新时代新生活的色彩,二者互为参照,不仅使各自旧或新的特征更为突出,而且旧与新互为衬托,构成了作品的丰富色调。《贞女》中的杨青玉的故事与姚桂花的故事也在对照中显示了各自的特点,那就是在传统文化统治密不透风的年代,杨青玉面对这种压抑无处告求,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姚桂花虽然同样受着这种文化的压迫,但她却可以求助法律,能自主掌握命运。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青玉在这种文化的森严统治下却“守节不贞”,而姚桂花在这种文化有所松动的统治下“守节倒又甚为贞洁”。这种对照,不仅使各自的特征更为明显,而且也相映成趣,使作品斑斓多姿。《穆斯林的葬礼》中两个悲剧故事同样在对照中显示了各自的特点,那就是造成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悲剧的是伦理与人性的冲突,而造成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悲剧的是文化与人性的冲突。两个故事的存在形态也大不相同,韩子奇与梁冰玉不仅有爱情经历,而且也有婚姻生活,并留下婚姻的结晶,就是他们的女儿;而韩新月与楚雁潮仅有爱情,没有婚姻,更没有结晶留存。这样,两个故事的对照不仅令各自特征鲜明,而且它们的相互衬托也使作品相映生辉。虽然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们在借鉴复调小说时没有追求主题的复调性,但他们所设置的孪生故事却使作品在艺术上具备了复调小说的繁复色彩。
此外,孪生故事还为作品制造了强烈的阅读悬念。因为既然要把两个故事装在一个作品中,那么就出现了如何摆布的问题,即结构问题。检视这类作品的结构方式,便可以发现它们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折交叉式,即将一个有情节联系的故事从中间对折,构成两个故事,然后又将这两个故事交叉叙述,《穆斯林的葬礼》即用了这种方法。二是总分交叉式,即开始时本来是一个故事,但随即一分为二,再将二者交叉叙述,《麦客》就是如此。三是平行交叉式,即两个故事没有任何情节与人物上的联系,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故事,只是被作家组合在一起,在叙述时便采用了平行交叉的办法,《贞女》即为其代表。不论运用哪种方法,都没有离开交叉,这恰恰是这类作品在结构上的最鲜明的特性。交叉的后果,是造成了强烈的悬念,也有人称其为“悬疑”。在叙事文学中,只要有故事存在,悬念就永远是一种可贵的元素,它能使读者始终保持强烈的阅读兴趣。特别是交叉造成的悬念还有用其他方式制造的悬念所不能比拼的优势,因为用其它方式所造成的悬念,如在每章结束时的故意设疑即“且听下回分解”之类,会在紧随其后的叙述中很快被释开,因为作品毕竟是沿着同一情节线索在叙述着。而交叉所制造的悬念则不同,因为作品是在沿着两个情节线索叙述,每条线索的中断都要等待同样长度的另一个情节线索叙述过后才能接上,悬念只能等到那时才会被解开,这样它更需读者有较长时间的等待。等待愈久,悬念的力量就愈强。如《穆斯林的葬礼》所叙述的两个故事,“玉”与“月”字章等量交叉,即一“玉”过后便是一“月”,然后再是“玉”、“月”,如此往复。正当读者兴趣盎然地沉浸在“玉”字章中所叙述的韩子奇与梁冰玉、梁君璧的故事的时候,情节突然中断,进入“月”字章所叙述的韩新月与楚雁潮的故事,于是悬念出现了。急于知道“玉”字章的后续情节的欲望被强行切断,便形成了作品的强烈吸引力。同样,随着新的情节的推进,读者不断地沉浸在这个新的情节中,兴趣逐渐高涨起来,然而恰在此时,“月”字情节中断,又转入“玉”字故事,读者的好奇心再次经受了新一轮的刺激。因此,作品在一个又一个悬疑与释疑的交替中走向两个故事的终点,读者也在一波又一波的兴趣涌动中读完了作品。《麦客》、《贞女》也都是如此。总之,孪生故事确有其优势和魅力。
三、反观视角
任何一篇(部)小说都存在着从什么视角去叙述的问题。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作家特别注重对叙述视角的选择,并且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深刻阐释,但其中仍然有一个问题似乎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反观视角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效果。这里所说的反观视角,是指作家的叙述是从作品中的否定性人物的眼睛和心灵里展开的。之所以应该充分重视这种叙述,是因为自从新式小说出现以后,作家在用作品中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时,总是选择肯定性人物。上世纪20年代蒋光慈曾试图出新,在《丽莎的哀怨》中尝试着用否定性人物,即一个流亡上海的白俄旧贵族女性作为叙事者,通过她的“哀怨”表现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小说发表后却招致了激烈批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指责蒋光慈同情白俄贵族。此后这种反观视角再也没人敢用了。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仍无多大改观。著名老作家魏金枝有感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曾经站出来进行呼吁,主张不妨尝试着从反面去写。他说:“为了杀敌致果,难道不应该运用一些袭击、侧击,以及从敌后打败敌人的战术么?”“在选取题材时,首先应该从多种角度来着眼”,“运用多种角度,作多方面描写”(魏金枝:《大纽结和小纽结》)。尽管他说得极有道理,但可能担心被安上同情否定性人物的罪名,这种视角始终无人敢于问津。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僵局方才被打破。那些热衷于改革文学创作的人,率先在创作中重新启用了这种视角。金河的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不仅仅是留恋》,矫健的同获这一奖项的《老霜的苦闷》以及随后出现的鲁彦周的《啊,万松庄……》等等,都无不如此。它们一改此时或以往通过肯定性人物的视角来反映某种社会运动的老套,选用反观视角来反映改革生活。《不仅仅是留恋》从张家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巩大明的角度来写改革。巩大明这样的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总是被设计成正面形象的角色,在这里被作家设计成了否定性人物,通过写他在集体解散牲畜分给个人时对昨天的留恋、失落、悲哀等等灰暗情绪,从反面展示了改革春潮对生活的激荡。《老霜的苦闷》则把以往文学作品中总是写成正面人物的老贫协主任、老劳模田霜设计成否定性角色,通过写他对政府鼓励个人发家致富的政策不能理解和由此引发的苦闷,从反面再现了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啊,万松庄……》也是如此,作家同样把昔日的劳动模范、人民代表“老主任”金松康设计成否定性角色,通过写他对先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恪守,对改革政策的抵制,以及面对失败所产生的“伤心”和“彷徨”,写出了改革的大趋势的不可抗拒。它们都从反面背面来叙述,成功地运用了反观视角,使作品显得新颖别致。
反观视角的选用,不仅使作品新颖别致,而且还产生了某些特殊的效果,这突出地表现为作品具有明显的折射感,一种强烈的艺术折光。我们知道,追求艺术作品的折射感,是很多艺术家千方百计地要达到的目标,不论是摄影艺术家、绘画艺术家,还是诗人、小说家,无不特别重视运用这种表现艺术。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中,那些有经验的作家都特别注重对折光的追求。从上世纪20年代鲁迅的《风波》,到上世纪60年代艾芜的《雨》,都莫不如此。但是,实现折射的途径却多种多样,反观视角的运用就是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类作品大都意在展现重大的社会生活,但它们却不直接地正面地切入生活,而是从反面或背面来写,从作品所设置的否定性人物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中,折射出重大的社会生活的某种状况,作品由此便获得了一种折射感。当年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就是如此,它通过丽莎这一白俄贵族女性流落中国上海后的境遇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诅咒,间接表现了这一革命的伟大胜利。上述新时期小说家的表现中国社会改革现实的作品也是如此,它们的主要创作目的是反映改革生活,但却不是正面展开,而是从否定性人物的感受和情绪活动中展开,读者所见到的不是直接展示的改革现实,而是在人物种种不适应的内心反映中折射出来的现实,从而间接地窥见了改革生活的真相,这样作品便形成了明显的折射感,也就是一种强烈的艺术折光。比如,在《啊,万松庄……》中,读者跟随被改革的车轮所抛下的原万松庄大队“老主任”金松康回乡的脚步来到了万松庄,透过他午睡起来站在堂屋前向东望去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座新楼已经盖好了”;从他“觉得腿有点儿酸,便顺势在石头台阶上坐了下来,怔怔地望着门前那条路”的视线里,看到的是一条旧路的废弃和一条新路的修成;随着他“拖着疲软的步子慢慢离开自己的家”到村中漫步,我们又从他的视线里看到了废弃的场院和在这里新建的校舍,然后又看见了精耕细作的农田和长势旺盛的庄稼,特别是看到了废弃多年的池塘里养起了鲤鱼的兴旺景象。这种种兴旺景象当然不是金松康愿意承认和正确理解的,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充满了拒绝承认和强烈的失落情绪,但读者却从他的视野里和心灵活动中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间接地感触到了改革现实。同样,从《不仅仅是留恋》中的巩大明灰暗的眼睛中所展现出来的生产责任制正在实行的景象,从《老霜的苦闷》中田霜灰暗的心理展现出来的人们正在忙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景象,都是间接反映,都是一种艺术折光。可以说,反观视角的选用使这些作品带上了一种折射感,它们有如高明的摄影师在镜子里拍下的拍摄对象的影像,呈现出一种曲折变幻之感。
正是由于作家通过人物的心理情绪来反映外部现实,因而为作品带来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把外在现实内在化,把社会生活心灵化,使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心理性特征。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外部现实的真实图景,而且更有人物的心理图景。这种心理图景都是在这些否定性人物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引发的心理冲突中展开的。在作品中,他们都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跟随新的现实脚步不断前进,而是头脑僵化地固守着昨天,当昨天即将过去时,他们仍然死死地抓住它不放,从而对已经到来的今天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正是在他们的心理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中,他们的心理图景得到了真切的呈现。在《不仅仅是留恋》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巩大明的心理图景:面对昔日的社员分畜到户的火热场面,他心里先是不满,总是无端地发火,没有好气地对待与他搭讪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深情的怀念:他怀念1955年冬天他是如何在这个院子里给乡亲们做入社动员的,怀念1958年秋天他又如何在这里主持召开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他久久地沉浸在对当年的火红热闹的回忆中。当怀念无法改变眼前的事实时,接踵而来的便是愤怒:当他看见今天在分牲畜时有人的那股高兴劲儿,便想起了1947年土改分地主财产时翻身农民高兴的情景,但他认为当年分地主财产时你高兴是正常的,而今天是在分人民公社的财产,你还高兴什么?于是他真想对着高兴的人“一巴掌甩过去”。由于愤怒,他再也压抑不住火气了,他不仅斥责别的社员,而且斥责自己的儿子。最后面对空空如也的院子他心里又升出了无限的留恋:“这个马棚是1958年他任三队队长时盖的,已经没有什么保留价值,该拆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也许再也看不到这个大院的昔日景象了,后人还会说起巩大明么?”作家围绕巩大明的心理与现实的冲突,非常清晰准确地勾画出他的心理变化过程,色彩分明地描绘出他的心理图景,把一幕集体解散时的生活景象内化成人物的心理画面,读者所见到的早已不是单纯的外部现实,而且更有人物的心灵现实。《老霜的苦闷》、《啊,万松庄……》所写出的同样是田霜、金松康的心理现实。可以说,这种化外部生活为心灵活动的叙事艺术,使文学有可能真正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最终完成文学是人学的艺术使命。在人物的激烈心灵冲突中,除了能间接窥见引起这些冲突的外部生活之外,还能更深入地揭示人的灵魂和人性深处的某些隐秘的东西。我们在巩大明等人的灵魂深处,就看到了人永远不愿打碎自己亲手搭建的七宝楼台这一人性特点,它无疑加深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深度。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反观视角的运用,也为作品带来了悲喜交融的审美效果。在文学创作中,通过悲剧的形式获得喜剧的效果,是很多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因为这种悲喜交融的审美形态可以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感受。这些作品就是如此。它们描写的是昔日的主任、书记、贫协主任面对改革后变化了的农村现实引起的种种心理冲突,冲突的结果造成了强烈的内心痛苦。这些昔日的英雄们的内心痛苦,表面上确有浓重的悲剧感。巩大明面对集体解散时的内心痛苦,田霜面对社会允许个人发家致富的内心痛苦,金松康面对心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被改变时的内心痛苦,都带有悲剧感。特别是作家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又总是沿着人物的心理逻辑展开,这就更使这种悲剧显示出局部的真实感,尤其是作品细致准确地描写的人物因不理解而与现实发生抵触所造成的巨大内心苦闷,是很感人的。如老霜每当自己苦闷至极而又无法排解时,就偷偷地走进幽黑的小仓房里翻看作为自己辉煌过去的标志的各种奖状的行为,确实使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苦闷的无所依皈的灵魂,让人感到一种浓浓的悲剧情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这种悲剧又被装在了喜剧的大框架中,使悲剧只成为一种表象,而喜剧则是更内在更根本的因素。由于这些“英雄”都是在逆时代潮流而动,他们妄图扯历史的后腿,在必然前进的生活大势面前,他们的行为无疑是极为滑稽的,作家将这种“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鲁迅语),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巩大明、田霜和金松康们的不识大局和由此引起的失落和无奈,留恋和苦闷,不仅违背了社会行进的方向,背逆了时代的潮流,而且事实上根本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他们硬要抓住已经风化的骸骨,以此排拒新生事物,不论他们自身的行为显得多么庄重和悲壮,也都是可笑的,是喜剧式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苦闷情绪只能引人发笑。作品就是在形式上的悲剧与实质上的喜剧的交融中创造出丰富的悲喜交加的审美效果,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可以说,反观视角的运用为中国当代小说增添了很多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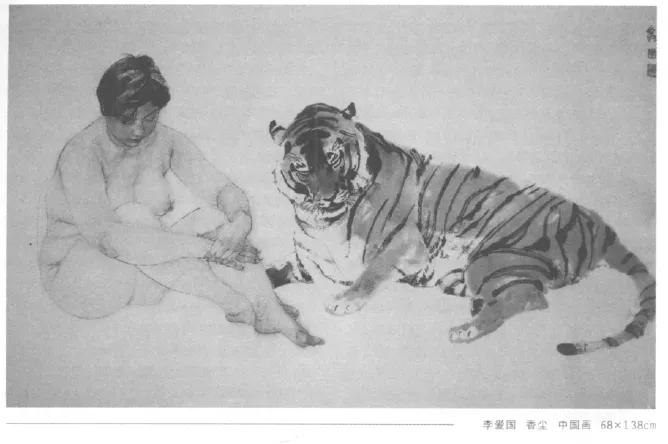
当然,中国当代小说在艺术上的新变,绝不限于设谜人物、孪生故事和反观视角这几种,而是在这之外还很多很多,值得研究者多方探讨,本文仅为引玉之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