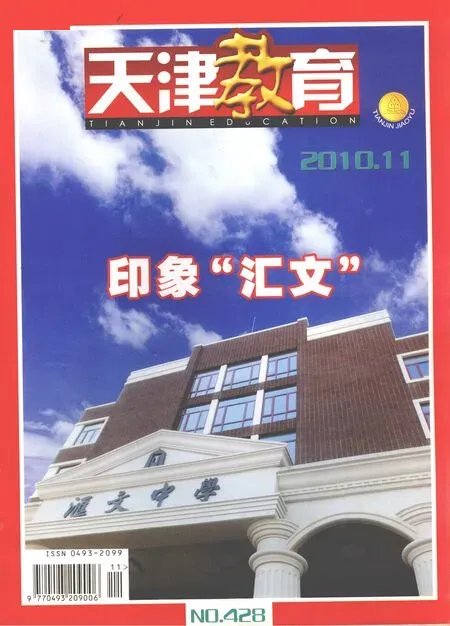小说的“解构”与“建构”
2010-05-10吴雅杰
■吴雅杰
吴雅杰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小说应该怎样读,历来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最流行的观点是从结构入手,按照故事情节发展的几个阶段梳理内容;然后是分析人物形象,概括主题思想,赏析语言与表现手法等。不能说这样做不正确,但总的感觉是这总有些“技术操作”的影子,挺活蹦乱跳的一篇作品被这么一折腾就变成了一堆零件和器官。
新课程提倡自主学习与创造性学习,体现在小说的阅读鉴赏上,我想应解决好两个层次的问题:解构与建构。“解构”即分析、解剖,即在对小说文本做要素解析的基础上获得对小说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认读;“建构”则属于开放式或多元性解读,是一种更高层次、更自我化的创造性鉴赏与审美过程。
信息的准确获取是鉴赏的基础,所以在对文本初读后应该能够对小说的内容做概括式表述,对作品的思路、层次有自己的理解判断,在此基础上可以思考如下问题:①小说着力刻画的是哪些人物?主人公是谁?谈谈你判断的根据。②人物主要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性格特征是什么?③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请说出你的理解。④小说塑造人物用了哪些手法?语言有何特征?小说形式与内容是如何统一的?等等。读传统意义的小说如此,读非传统意义的小说如西方现代派文学、先锋派小说,也可以做如是追问,但追问的目的是准确触摸文字背后的精神脉动。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由于抱不平,被抢苹果的人打得很惨,“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在而是挂在脸上”的情节与描写就有些荒诞,而且用的是一种很轻松的语言;汽车司机苹果被抢、车被破坏,居然哈哈大笑,还与抢自己的人一同离开。这些情节都不符合“细节的真实性”,是一种超现实的荒诞,但荒诞背后是对人性的冷思索。追问的过程也就是“解构”文本的过程。
文学鉴赏是一种个人色彩浓厚的审美活动,阅读者只有真正走进作品的内部与作者真正沟通,产生感情的共鸣,才能实现“以想象为方式填补作品的空白,以全部的人生经验作品中的一切”。所以,阅读时可以思考如下问题:我与人物的经历有无相似之处,人物的思想感情我经历过吗?以我的经验,能否认同作者的感情世界?等等。以自己的背景知识积极参与构建作品,可以获得阅读的愉悦,利于对人物感情的体验并产生共鸣;以自己的经验对文本的“空白”结构加以想象性充实、补充,就是对文本进行“具体化”的解读,从而对文本的意义世界作一定层次的开拓和创构,见人之所不能见,感人之所不能感,实现由“解构”向“建构”的跨越。如此,就可以从《阿Q正传》中读出鲁迅大声疾呼摒弃阿Q式的人生,做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让生命更有价值时的殷切。我们也可以认为,《套中人》批评的锋芒不单单指向已经异化为极端的别科夫,而是指向更多的把自己装进“套子”的普通人。因为这众多的“套中人”恰如鲁迅笔下的铁屋子的昏睡者,客观上维系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要破毁铁屋子,需要剥去人们身上或薄或厚的“套子”。

应当注意的是,在充分调动自己的创造性对文本进行建构的同时,也应当受解读对象即文本的制约。解读的创造性和文本的规定性是辩证统一的,读者解读创造的翅膀不可任意飞跃文本所不能及的界域,否则,将导致误读,甚至误入歧途。比如,读《孔乙己》,则想象孔乙己如何状告丁举人;读《项链》,则读出玛蒂尔德为夺回那挂钻石项链,与佛来思节夫人争吵不休,不得不对簿公堂……这样的“建构”其实是误读或戏说,不是独特的个人体验,而是对文本的扭曲和亵渎。切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必须“还是”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