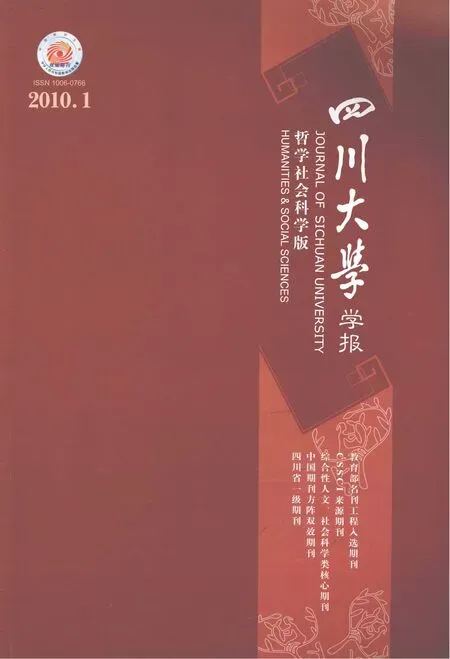论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的阐释——兼及文艺学规范性之反思
2010-04-13傅其林
傅其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如果说规范性基础 (normative foundation)是指哈贝马斯而言的公共性语言交往的规范-规则之奠基,那么文艺学是否具有规范性基础呢?本文检视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的阐释,进而反思文艺学规范性这一知识学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审美领域在现代拥有自身的规范性基础,这一基础可以回溯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然法权,从而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基础构成内在的联系,这亦是审美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意义上,审美领域可以用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加以阐释。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和悖论性,使得其内在地违背普通语言的惯例,逃脱日常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之掌控。审美领域既被纳入社会现代性的合理性规划之中,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元素之一,又适应了现代人最迷醉和向往的隐私性、神秘性诉求。因而立足于现代审美领域的文艺学既有自身的规范性基础又超越了规范限制,既拘宥于话语的价值合理性又要应对“无言之美”的微妙灵韵,文艺学规范性基础的思考理应聚焦于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点。
一、审美实践合理性
审美领域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维度,成为从康德到韦伯所设想的文化价值领域的重要部分之一,与科学、道德形成三种不同的合理性,即认识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审美实践合理性。这三种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观念通过相应的行动体系在生活世界中体现出来,并进行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从而控制社会部分体系以及生活世界的划分。哈贝马斯明确地分析了从文化价值到生活世界的逻辑结构:“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把现代意识结构压缩为三种理性复合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结构上可能的社会合理化视为相应的观点 (从科学和技术,法律和道德,艺术和‘恋爱学’各个领域中提出的观念)与在相应的不同生活秩序中的利益和表现的联合。这种 (极为冒险的)模式能够使我们陈述一种合理化的非精选模型的必要条件:三种文化价值领域必须联系着行动体系,以至于根据有效性主张而形成的专业知识的生产与传递得到安全地保障;专业文化所形成的认识潜力必须被传递给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必须丰富社会行动体系;最后,文化价值领域必须以均衡的方式被制度化,以至于与文化价值领域相应的生活秩序保持充分的自律,避免这些生活秩序被屈从于其他异质的生活秩序的内在法则。”①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译文根据英文版进行了修改。C.F.Thomas McCarthy,“Reflections on Rationalization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in Richard 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Pp.177-178.这表述了现代分散的意识结构-三种文化价值合理性(观念)-文化行动体系-日常交往实践的内在演化逻辑。文化行动体系形成了价值合理性的专业知识,构成了相应知识的制度,“在文化行动体系中,相应的‘话语’和活动是职业上被赋予的和制度上被组织起来的形式。”[1]206这样,文化价值合理性的内在逻辑与社会生活中的相应制度为文化领域独立或者自律奠定了基础。审美自律领域呈现为审美价值观念与艺术活动的行动体系制度,其核心规则就是美学实践的合理性的内在逻辑的扩展。为了深入理解审美实践合理性及其独特的规律,哈贝马斯从形式语用学或普通语用学出发,论述了美学批评或者艺术批评和艺术作品或者艺术生产本身的语言形式特征及其相关的学习过程,彰显了美学批评的知识价值与艺术审美经验扩展的累积性特征。
首先分析审美批评或艺术批评。审美实践合理性对哈贝马斯来说在于语言论断本身之中,审美领域的规则与规范来自于语言的规则或者规范。审美批评体现出特殊类型的语言论断或言语行为。对现代欧洲的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价值领域而言,不同的论证形式根据普遍的有效性主张加以特殊化,这就形成了经验-理论的话语、道德话语和审美批评话语。审美批评实质上操纵着一种特殊的以价值为标准的论断语言,其特殊职能是“鲜明地展现一部作品或一篇描述,使人们可以感知到这些作品是一种规范经验的真实表达,是一般真实性要求的体现。这样,一部作品由于具有论证的美学知觉,就成为有效的作品”[2]37-38。所以,在审美批评涉及的趣味性问题的论断中,人们仍然依赖于充分论证的合理力量,借助具体艺术作品作出价值的适用性的论断。哈贝马斯根据有效性与知识的联系阐释了审美批评或艺术批评和艺术作品的合理性:某种“知识”在艺术作品中被对象化,尽管其方式与理论话语或者法律的或道德的表现方式不同。而知识对象化也是可以加以批判的,所以艺术批评与自律的艺术作品是同时出现的:“艺术批评已经形成了与理论和道德-实践话语相区别的论证形式。由于不同于纯粹主观的偏爱,我们把趣味判断和一种可以加以批评的主张联系起来,这种事实为艺术的判断预设了非武断的标准。正如对‘艺术真理’的哲学讨论所揭示的,艺术作品提出了关于作品的统一性、本真性以及表达成功的主张,作品可以通过这些主张加以衡量,并且作品根据这些主张可能被认为是失败的。正是由于此,我认为,论证的语用学逻辑是最合适的引导线,借助于它‘审美-实践’合理性能够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合理性。”[1]200内在于艺术作品的有效性主张开启了看似熟悉之物的视野,重新揭示看似熟悉的现实的“唯一的启示的力量”。艺术按照一种抽象的价值尺度、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主张,可以辨别其自身的美好性,艺术的进步、完美、价值提高亦是可能的。审美有效性知识的累积奠定了审美实践话语的合理性,这既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条件,也是艺术批评得以可能的合法性基础。
就皮亚杰的学习过程理论而言,艺术作品本身的审美经验同样具备累积性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如果谈及“学习过程”,那么,正是艺术作品自身而不是关于作品的话语是具有方向性、累积性的转型。累积的东西在此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内容,而是特殊经验的内在逻辑分化的效果,即分散的、无限制的主体性的审美经验扩展的结果。本真的审美经验只有在有组织的日常经验的模式化期待的范畴崩溃时,在日常行为的常规与普遍生活的管理被打破时,在可计算的准确性被悬置时,才得以可能。审美经验激进地脱离认知、道德,体现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之中,凸显在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先锋派艺术之中。这些艺术运动所洞察的正是“审美经验的形式的转型”。先锋派艺术本身被“主体性的分散化和无限制化的方向”所引导,这种分散化显示出对非实用的、非认知的、非道德之物的高度敏感,进而为无意识、迷幻、疯狂、物质与身体打开了大门,“因而也打开了我们与现实无言联系中如此飞逝的、偶然的、直接的、个体化的,同时如此远如此近以至于逃避了我们规范的范畴所抓取的一切东西”[1]201。因此,这种被本雅明称为“集中的干扰”的经验不再披着灵韵之面纱,而是一种震惊,它持续不断地捣毁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及其虚假的意义总体性。通过反思地处置材料、方式和技巧,艺术家为实验与游戏打开了空间,把天才的创造转变为“自由的建构”,艺术的发展成为学习过程的媒介。尽管哈贝马斯对皮亚杰的学习过程理论应用于审美领域持有怀疑,但是认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艺术作品本身的累积与方向,“科学、道德实践和法律理论及艺术的内部历史——肯定没有直线的发展,但是有学习过程”[3]422。“由于学习过程,文化价值能够发生嬗变”[4]172。而颇感悖论的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没有把文学艺术与艺术批评理解为学习过程,而是认为“涉及真理和正义的专业性的解决问题之话语是以物质世界的学习过程为轴心”[5]339。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审美经验的这种合理性拥有特殊的语言形式结构与修辞规范,蕴含着文学艺术的话语规则,形成了独特的规律性,“美学价值领域可以自由地设置独特的规律性,这种美学价值领域的独特规律性才可以使艺术合理化,从而在与内部自然交往中的经验文化化”[2]214。这样,文化现代性的分化就是特殊话语涉及趣味、真理、正义的“知识增长”[5]339-340,审美实践合理性在于通过特殊的论断和话语形成了规范性主张,其在文艺批评、生产与接受活动中,在文本的话语形式中得到具体彰显。哈贝马斯从语言哲学角度奠定了文学艺术领域的自律性基础,用赫勒 (Agnes Heller)的话说,他阐释了审美领域的同质性的“规范与规则”:“审美的、科学的和宗教的意象在现代性中分道扬镳了,并且在‘审美地做某事’、‘科学地做某事’、‘宗教地做某事’方面,人们遵循着完全不同类型的规范与规则。”[6]152德里达关于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张与蔓延的“普遍文本”概念和美国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普遍文学”概念[5]193,消解了建立在自律的语言艺术作品和独立的审美幻象基础上的文学观念,这是哈贝马斯难以认同的。
二、文艺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把文学艺术视为公共交往的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他关于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的阐释都建立在审美交往的基础上,导致“交往的审美化”。伊格尔顿认为,“哈贝马斯理想的说话共同体中,可以看到康德的审美判断共同体的现代翻版。”[7]402罗伯茨 (Roberts)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审美基础即为“自由言语的自由主义美学”[8]。罗蒂 (Richard Rorty)也指出,差异的普遍共识的交往体现了“美的理念”,哈贝马斯企图“寻找和谐利益的美的方式”,“欲求交往、和谐、交流、对话、社会团结和‘纯粹的’美”[9]174-175。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区别为多种形态,如文学公共领域、科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而主要有涉及国家权力的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起初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分化出来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网络,可以按照交往密度、组织复杂性和所及范围区分出不同的层次,“从啤酒屋、咖啡馆和街头的插曲性 [episodischen]公共领域,经过剧场演出、家长晚会、摇滚音乐会、政党大会或宗教集会之类有部署的 [veranstaltete]呈示性公共领域,一直到分散的、散布全球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所构成的、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抽象的公共领域”[10]461-462。哈贝马斯谈及的文学公共领域不仅是文学活动的交往,而且有文学论辩的公共性交往,两者都是基于语言形式的意义共享。具体地说,审美领域的创作活动、文本、接受活动都同时构造了不同维度和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创作活动本身涉及创作者作为接受者的对话,对话的媒介就是语言文本;现实读者也以语言为媒介与文本、作者构成了对话性的理解关系。毋庸置疑,这是一种虚拟体验的想象性的公共领域或者共同体。审美公共领域也可以借助于实在空间而存在,现实主体直接进入咖啡馆、茶馆、剧场、音乐厅、博物馆、学术会议厅等场所,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插曲式公共领域和呈示性公共领域。当文艺活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一定媒介和影响的手段,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势不可挡。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的交往性:“群众交往的媒体,却仍然是表现语言的理解。这些群众交往媒体,构成了语言交往的技术上的加强,使空间上的距离和时间上的距离联结起来,成倍地增长了交往的可能性,紧密了交往行动的网络。”[2]470在现代社会,借助于传媒技术,语言行动脱离了时空的约束,语言文字的发展形成了作者的作用,“这种作者可以向不规定的,一般公众进行表达;形成了继续通过学说和批判构成一种传统的专家的作用;形成了读者的作用,这种读者通过选择读物,决定他可以参加什么样的交往”[3]243。作者、文艺专家、读者通过大众传媒形成了抽象的自由的审美公共领域。文学的公共领域从宫廷的贵族的文学公共领域向城市的、现代民主自由的公共领域转换,从而通过讨论或者语言理解形成主体间性的共识性经验。在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现代文学艺术必然需要美学批判、艺术批评等公共领域,分散化主体的审美经验的扩展亟待批评家、读者、作者的话语讨论,不断达成主体的差异或者私人性的理解,从而形成对艺术作品的共享,领会现代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
事实上,审美实践合理性与文学艺术的言语行为话语,为主体彼此理解与交往的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审美领域的合理性在于审美领域的特殊语言类型,其价值有效性就是言语行为的主观的真诚性,这可以说就是审美领域的规范 (Geltung)。哈贝马斯有意识地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基于语言哲学的艺术观。后者明确提出了艺术的语言逻辑规则特性:“艺术等于把握,等于从对象获得一种规定的表达。”[11]75哈贝马斯借助米德对抒情诗人的创造性的字句的意义协议进行了语言学的阐释。米德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在于发现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发现在另外的情况下表现出同样感情的表达方式。抒情诗人具有与一种感情激动联系在一起的美的经验,并且作为艺术家可以运用词汇,他存在适合他的激情的词汇,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引起自己态度的词汇……决定性的,是交往的词汇,就是说,象征在一种个人那里,本身是引起与其他个人那里相同的情况。应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相同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应该在相同的情况下出现。”[3]20-21以哈贝马斯之见,对一个创造性的诗人而言,意义惯例创造了新的作品,诗人在创作时必须直观地实现相应的发言者预计的态度,因此文艺创造蕴含着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的概念。塞尔从虚构话语的共享性方面解释得很清楚,就本体论的可能性而言,作家可以创作他喜欢的任何人物与事件,就本体论的可接受性而言,连贯性 (coherence)是最重要的,关于连贯性的标准在不同文学的类型中是不同的,但是“视为连贯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和读者关于视野的惯例的契约的功能。”[12]曹卫东研究指出,“文学 (艺术)实际上发挥的是一种交往理性的作用”,“艺术本质是交往。”[13]135可以说,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形成了一种基于语言的意义共享的审美公共领域。
文艺公共领域的形成不仅在于审美话语的规范有效性,还意味着它有相应的现代自然法律制度奠基。因为文学艺术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对象化,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空间,作家的创造空间、媒体形式空间、讨论空间、阅读空间,不仅包括私人空间,也包括公共空间,否则文学艺术纯粹是个人的虚无的想象。不论是文学公共领域还是政治公共领域,它们要现实地存在并发挥实际的功能,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保障个体具有自由参与语言交往、话语讨论的法律权利:“对于在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能够保障其内在主体性的私人来说,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标准必须具有一种真正的自明性。”[14]58这种法律权力是现代自然法的体现[15]88,“现代法律保护法律上在法律认可的界限之内的个人爱好”[2]330。自然法在形式上规定了个人意愿自由,保障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从而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提供了法律的依据。这样,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就不仅需要基于语言的主体性经验的共识,这奠定其内在的规范性,而且要求社会法律的承诺,这是其外在的制度规范性。但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自律主体,就无法言及审美的交往与意义的共享,不是“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则难以达至“伟大的爱情”(舒婷《致橡树》)。因此文艺公共领域与自然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性的,换言之,审美领域的自由主体的共识是一种软性的法则,而自然法则是把这种软性的法则规范化、制度化。如果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那么艺术的合法制度化存在就必须有自由民主的法律规范加以保障,同时审美领域的自由性本身象征了一种理想的自由的政治权力的选择。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中,自由的审美公共领域才得以萌生,得到法律的认可,并充分发挥自由言语的交往行动功能,推动审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建构,促进审美领域的文化再生产,而这反过来推动民主法律制度的建立与进一步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法律制度的感性形式。
文艺公共领域形成的意义是显著的。第一,审美实践合理性奠定了文艺公共领域的基础,而文艺公共领域的形成促进了日常生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对审美有效性本身、对审美领域专家化现象加以不断讨论,能解决现代生活世界由于文化的专业化从而导致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文化贫困化现象,使得审美价值合理性成为日常个体的合理性维度,但这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5]207或者哈贝马斯批判德里达的“语言的审美化”,因为“只有通过创造认识因素与道德因素和审美表现因素毫无限制地相互作用,才能矫正一种物化的日常实践”[16]。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下的选择:“一种审美经验——它并不是围绕专家批评的趣味判断而被设计出来的——能够使其意蕴加以改变:一旦此经验被用于阐释一种生活——历史的状况,并与生活问题息息相关,它就进入了一种语言游戏,那不再是美学批评家的游戏。”[17]21审美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构建成为审美价值、内在主体意识的充分表达,成为日常交往的构成性因素之一,成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的重要维度。第二,文艺公共领域不仅对文学产生意义重大,而且使得文艺学学科成为必然。如果说政治公共领域是通过话语的媒介而构建的空间,成为铺设自由民主社会的调节性制度,因此成为民主社会的规范性基础,那么自由的审美公共领域是文艺学的规范性基础。因为它促进对基于语言的趣味、美、真诚性、审美价值等问题深入而合理的讨论,使得文学研究者能够平等参与审美讨论,不断从他者的理解中深化自身的理解,避免美学领域的精英主义和主观意识中心主义,实现了文艺学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型。在审美的公共领域中,文艺作品获得承认或者批评,通过言语论断从而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或者权威性。如此看来,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的规范性基础可以成为文艺学学科的规范基础。
三、审美领域规范性基础之限度
问题在于,文学艺术具有审美实践合理性吗?审美领域只能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或者只能在特殊形式的语言规则中奠基吗?甚至进一步追问,审美领域是否具有规范性基础?审美领域颇为感性、幽微,以至于消解任何形式的规则性与知识的累积性、合理性。麦卡锡对哈贝马斯提出的质疑具有启示意义:“在艺术和道德范围里,在何种意义上有持续不断的累积的知识生产呢?”[18]179
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和美学立足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特别是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之上。他依此可以阐释审美领域的言语行为的规则性,认为写诗歌和开玩笑的语言基础即在于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的使用”[4]34,但是这并非不存在问题或者悖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建立在文字意义和直接表达形式之上的:“塞尔的理论根据文字的和直接的施为性来‘定义’以言行事的行为。”[19]177他与其他语言分析哲学家一样,通过语言逻辑的形式分析企图获得客观性与真理,甚至认为意义和意向性最终归结为神经生理学的问题。他对文学性、修辞性突出的隐喻也展开了语言逻辑的辨识,从表达意义 (utterance meaning)和句子意义 (sentence meaning)来探讨隐喻从“S是P”到“S是R”的内在逻辑原则,指出:“在隐喻的表达中,没有一个词语或句子改变了其意义,然而言说者意指了不同于词语和句子所表示的东西。”[20]借此,他批判德里达由于没有认识到语言哲学的基本历史,没有就基本概念进行区别,所以导致了语言概念的误用,从而提出只要遵循语言哲学的基本规则,文学理论看似深奥的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德里达关于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书写先于言语等观点在塞尔看来难以置信。不过,塞尔领会到隐喻原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非规范性,还认为“隐喻实质上是不可能意译的”[21]114。他在论述虚构话语与非虚构话语的差异中认为,后者涉及到一系列涉及句子与现实世界的“垂直的规则”,而前者没有实施以言行事的行为,只是借助于语言的实际表达或者书写,假装进行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完全没有遵循普通话语的规则,悬置了现实的规范要求和许诺。构成虚构话语的不是话语句子本身的特性,因此判断一个话语是否是虚构的,是根据超语言、非语义的“水平的惯例”,这种惯例突破了句子与世界的联系:“构成虚构话语的假装的以言行事是通过一套惯例的存在得以可能的,这些惯例悬置了联系以言行事行为与世界的规则的规范性运作。在这种意义上,以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讲故事是一种单独的语言游戏;为了游戏,它就要求一套单独的惯例,然而这些惯例不是意义规则。”[21]67虚构的文学文本话语所遵循的规则不再是普遍言语行为的规则,而是依赖于后者的表达形式又超越了后者的规范性基础。这使得文学领域虽然有共识的达成,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共享,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可交流性、非确定性和误解的必然性,或者说可以有交往和理解,却是伪交往和误解。青年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指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必然存在着契约”[22]80,文学艺术以语言形式作为载体即表达了交往的可能性,同时也仅仅是一种暗示,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与外在世界交往的方式也是交往的缺失,“这种非交往性指向了艺术的断裂的本质”[23]7。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的张力、悖论、反讽的分析,说明了文学语言脱离了日常语言的规则,现代审美经验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逃避了我们规范的范畴所抓取的一切东西”。在回应德里达、罗蒂、卡勒抹杀文类区分的论述中,哈贝马斯通过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深入地探究了文学艺术话语的独特性。认为文学话语区别于日常实践规范的普通话语在于其修辞特性、自指性、虚构性、寄生性、以言行事力量的超越性、揭示世界的功能性,它不同于法律、道德话语的规范性、解决问题的功能性。所以,虽然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具有诸多类似,均存在对修辞的看重,但是在不同领域,修辞的工具归属于不同的论证形式的学科。这说明,审美领域的规范性不能以交往理性的规范性概念来加以充分阐释,正如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当语言的诗性的揭示世界的功能得到凸显并获得构成性力量时,语言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束缚和交往功能”[5]204。后来他甚至认为,能够为理性支撑的有效性主张有两种类型,即真理的主张和正义化的主张[24]79,而不言趣味类型。倘若如此,审美领域就不适用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形式语用学的规范与规则,哈贝马斯认为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交往,但是文学虚构话语是寄生性模式,只是“间接的交往”,它混淆了现象与实质,事实与应该,意义与符号[25]。
审美领域的神秘性因素、迷狂、狂欢化的混沌状态导致自由的审美公共领域与合理性交往的消弭;艺术独特性与创造性的追求,对自我孤独的内在主体性的挖掘,导致没有对话的独白;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来的孤独与冷酷,超越了可理解性与共享性,崇高的非理性体验超越了形式的理性把握。即使可以对话与交往,但是所展开的只是表面的浅薄,而无法深入到艺术经验的实质性层面。审美经验的无意识因素、偶然性导致语言规则的无限性。无言之美的中国艺术精神的追求往往超越了语言的界限与规则,道心唯微,文心幽缈,诸如叶燮所谓:“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忽之境,所以为至也。”[26]333维特根斯坦也认为:“音乐中有一些充满感情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按照规则可以识别的。”[27]157坚持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塞尔也认为,虚构的话语虽然具有普通语言的意义,但是并不遵循普通语言的规则,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共同的特征,也“不可能存有构建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21]59。
因此,审美领域是规则与超规则的结合,是审美合理性与非理性体验的熔铸,是审美公共领域的交往的理性、透彻性与不可交往的神秘性、隐私性的交汇,是意义共享与无意识欲望的纽带。哈贝马斯也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艺术一方面满足主体性的私人化的自我陶冶,另一方面成为公共讨论和争论的焦点[28]3。阿伦特曾指出,正是现代人的内在隐私性的发展,艺术领域获得了重要性:“从18世纪中叶直到差不多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诗歌和音乐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小说的兴起。这一繁荣局面与一切更具公共性质的艺术门类——尤其是建筑——的同样惊人的衰落恰巧发生于同时。”[29]71这说明,审美领域在现代性的丰富多彩的私人性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同时它也满足了个体的私人的需要,满足了情感的私人化以及情感的隐蔽处置,内在空间的开拓与释放。不论是作者的隐蔽的创作活动,还是读者的私人化的阅读,都在审美领域寻觅到了合法的空间。但是审美领域对阿伦特来说又是一种自由的精神需要,从而从必然性的私人领域进入到自由的公共领域。所以在现代性中,艺术本身又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亚当·斯密曾说过,公众的赞赏“对诗人和哲学家来说,几乎占了全部”[29]87。
哈贝马斯试图从现代理性的重建中思考审美领域的规范性,这对文艺学的规范性的认知与理解是有意义的,但是有其限度。如果无限制地扩展,就导致规范性本身的失效。也就是说,“规范性基础”这个命题与提问方式如果仅仅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对文艺学而言不是全部仅是部分有效的。之所以部分有效,是因为他的建构可以为文艺领域划定理性的边界,但是无法界定审美领域复杂的内涵,只是设置一个形式的框架,但无法规范框架之中的实质内核。如果审美领域具有非规则的因素,那么文艺学学科就不必然有规范性基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余虹教授认为,文艺学是一门寄生性的学科[30]263。而且,哈贝马斯讨论规则或者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主要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从现代社会的整体的潜力的把握的视野来审视的,尤其注重从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出发来设置社会合理化的可能性,从话语伦理的程序来达到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的自由民主的形成,这是一个涉及民主权力与合法性制度的建设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这一问题[31]144。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充分汲取了从自然语言 (日常语言)的研究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自己的语言哲学基础,而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诗性语言中获得本体论基础。因为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一个社会文化的规则与惯例,所以批判理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挪用现代性的潜力,从现代性的潜力中获得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从而拯救现代性的规范性内容。这个规范性基础不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审美乌托邦诉求,而是一个社会规范伦理建构。如果把哈贝马斯这种规范性基础的概念,毫无中介地转移到审美领域和文艺学的规范性基础的建构,必然导致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文艺学的规范性基础的建构不能仅仅以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范式为依托,不仅是把“艺术作品的实验性的潜力带入规范的语言”,而是要居于“虚构话语”与“规范语言”的持续撞击之中。文学与规则之间,文艺学与规范性基础之间仍然玩的是猫和老鼠的游戏。
[1]Jürgen Habermas.Questions and Counterquestions[C]∥in Richard 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 [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 [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4]Jürgen 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Trans.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79.
[5]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trans.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
[6]Agnes Heller.General Ethic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7]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 [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Mark Neocleous.John Michael Roberts:The aesthetics of free speech: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J].Capital& Class,Spring 2006.
[9]Richard Rorty.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rnity[C]∥in Richard 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
[1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1]江怡,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4卷 [M].程志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John Searle.The Logic Status of Fiction Discourse[C]∥in Peter Lamarque,Stein Haugom Olsen eds.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The Analytic Tradition:An Anth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13]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性话语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恩斯特·斐迪南德·克莱因.论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致君主、大臣和作者[C]∥载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6]Jürgen Habermas.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C].in Cluvre Cazeaux,ed.The Continental Aesthetic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17]尤尔根·哈贝马斯.论现代性[C]∥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8]Thomas McCarthy.Reflections on Rationalization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C]∥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
[19]Robert M.Harnish.Speech acts and intentionality[C]∥in Armin Burkhardt ed.Speech Acts,Meaning,and Intentions:critical approaches to philosophy of John.R.Searle.New York:de Gruyter,1990.
[20]John R.Searle.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C]∥New Literary History,1994,25,(3).
[21]John R,Searle.Expression and Mea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2]Georg Lukács.Soul and Form[M].trans.Anna Bostock.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74.
[23]T.W.Adorno,.Aesthetic Theory[M].Trans.C.Lenhardt.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4.
[24]Jürgen 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M].ed.and trans.Barbara Fultner.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3.
[25]Jürgen Habermas.Some distinctions in universal pragmatics:a working paper[J].Theory and Society,vol.3 no. 2(summer,1976).
[26]叶燮.原诗·内篇下[C]∥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7]江怡,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 [M].涂纪亮,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8]Nick Crossley.John Michael Roberts,eds.After Haberma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ublic Sphere[C].MA: Blackwell Publishing,2004.
[29]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C]∥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30]余虹.文学知识学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1]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