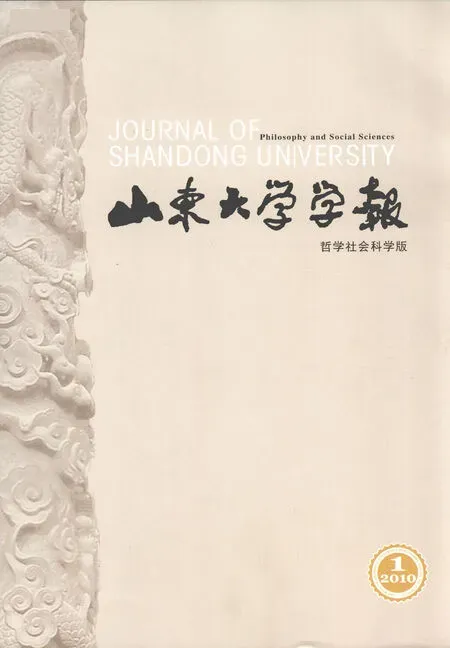康德和因果问题的解决
2010-04-12邱文元
邱文元
康德和因果问题的解决
邱文元
因果必然性问题,关涉到自由(自由的因果性)和必然(自然的因果性)的关系问题。康德不否认自由和必然的同一性,只是否认了人认识此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康德并没有彻底割断自由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先验自由的直接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与必然的本源的统一性。通过这个本源的统一性,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因果问题,并且对康德因果问题解答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出解释。
先验统觉; 康德; 因果问题; 体用论
因为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特性,因果规律的概念在西方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原子论最为著名,其代表人德谟克利特说:“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近代,牛顿建立了一个彻底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体系,对因果关系的探索也成为近代哲学的重要课题。休谟提出了因果关系概念的必然性问题,康德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回答,认为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来自于认知主体的因果范畴的必然性,并且用先验演绎来证明因果范畴的客观必然性。
康德的因果性概念除了知识论范围内的自然的因果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道德领域内的自由的因果性,并且这二者是同一的。自由的因果性和自然的因果性的同一,实际上是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同一。康德本人认为,我们的有限存在无法理解这个同一,只能在上帝统治下的天国中二者才有同一的认识。康德以后,德国古典哲学的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曾经致力于阐明二者的同一关系。但是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兴起以后,这个问题就被抛弃了,因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都认为知识(自然的因果性)和道德(自由的因果性)二者是分裂开来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因果规律的概念,这也是中国有机自然观的应有之义。近代以来,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为价值和知识分离提供理论资源(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遭到批判。但是,随着后现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复活了。
在中国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学者从价值和知识相贯通的角度理解因果性问题。牟宗三用儒家的圆善论来解读康德的道德哲学,提出“人既有限又无限”或“人可有智的直觉”对康德的“有限人”作了修正。李泽厚则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试图从历史实践理论中发现康德“先验范畴”的来源。邓晓芒最近提出:“将认识和实践合而为一,克服自由与必然的割裂,建立哲学的人学本体论,才能真正解决因果必然性问题和自由问题,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①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58页。。俞吾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也探讨了这个问题。②俞吾金:《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本文继承了前贤,结合价值与知识、贯通道德和认识的基本观点,解读康德自由(自由的因果性)和必然(自然的因果性)的关系问题,即道德和知识的同一性问题。我们发现,尽管康德否认人认识道德和知识的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自由的因果性仍然要通过自然的因果性的范型表现出来。康德在分割现象与本体的同时,也利用了现象和本体的同一性作为前提。这个解读引导我们回头重新诠释先验演绎。因果范畴的普遍性必然性,来自先验统觉本源的统一性,而先验统觉作为自然因果性的理知的原因性和先验自由作为自然因果性的无条件的条件是同一的,这样自然的因果性就成为自由的因果性的结果。康德否认认识自然和自由同一性的可能性的理由,有着深刻的西方历史根源。我们通过对比中西文明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来认识康德哲学的立场,从而正面提出中国哲学传统对因果问题的解答。
一、两种因果性
休谟的因果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单纯知识论的问题,即关于自然的因果规律的必然性问题,另一个是自然的因果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问题。
康德对休谟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进行的,这也是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对康德因果性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休谟主要是从形而上学的一个单一的然而是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力、作用等等派生概念)出发的。……休谟无可辩驳地论证说:理性决不可能先天地并且假借概念来思维这样一种含有必然性的结合。不可理解的是:由于这一事物存在,怎么另一事物也必然存在这种连结,它的概念怎么能是来自先天的。他因而断言: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弄错了,错把这一概念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由经验而受孕之后,把某些表象放在联想律下边,并且把由之而产生的主观的必然性,即习惯性,看作是来自观察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页。
康德对因果问题的解读要点在于,他接受了休谟认为因果必然性不能从经验中获得的结论。但是他提出,理性可以先天地提供这个因果必然性的知识。
普遍必然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成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的出发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把认识和对象的关系进行了颠倒。在常识理性和康德以前的认识论中对象是自在之物,认识是围绕着自在之物进行的。康德则把认识对象看作认识过程的产物,即不是自在之物而是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综合产生的现象。先验观念论认为我们的知识都是由范畴和直观的综合造成的,范畴无直观、直观无范畴都不能产生先天综合判断。直观是感性直观,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直观的形式,通过二者感觉杂多被给予我们,成为认识的质料。知性思维运用量、质、关系、模态四类范畴对感觉杂多进行建构,而构造出认识的对象,从而获得知识。关于这个构建的过程,康德通过范畴的先验演绎进行了验证。康德通过自己的哥白尼式革命解答了休谟的因果必然性来源的问题。但这个革命的变革把自在之物推给认识的彼岸,康德因此走向了不可知论。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为设定自由和上帝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康德批判哲学除了认识论上的自然的因果性以外,也还有一个伦理学上的自由的因果性概念。“在意志的概念之中已经包含了因果性概念,从而在纯粹意志的概念中就包含了具备自由的因果性概念,也就是说,这种因果性不能是为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从而任何经验直观都是不能够作为其实在性的证明的,但是在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之中,它的客观实在性的正当性仍然得到了完满的证明,然而(很容易明白)这不是为了理性的理论运用,而是为了理性的实践运用。”*[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意欲能力包含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对象的观念通过意志对这个观念的对象的因果关系,而纯粹意志的因果关系则是排除了对象观念的一切经验内容的因果关系的纯形式,因此纯粹意志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意志自律。而自然的因果关系则是一个事件的存在,决定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自由的因果关系是自律,而自然的因果关系是他律。自由的因果性和自然的因果性是互相规定的。
邓晓芒、俞吾金认为知识论上因果问题和自由与必然性关系问题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本文要推进的方向。实际上,没有道德论上的自由也就无法建立知识论上的因果必然。
二、先验统觉与自由的原因性
在这里我们并不按照康德自己承认的思路,而是从康德著作文本蕴涵的思路展开。因为正如康德可以比柏拉图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哲学,我们同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哲学。康德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蕴涵着许多康德本人没有自觉到的线索,虽然康德本人并不自觉到它们,这些线索支配着康德的哲学思考,没有它们康德的哲学体系就会崩溃。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找出这个线索来,并且用它贯穿康德哲学的全部内容,并使康德哲学获得清楚的理解。
康德认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同一性的认识只有对于拥有智的直觉的上帝才可能,因为神圣的意志可以不受一切感性欲求的干扰。可见,康德的哲学并没有否认道德和知识、现象和本体同一的可能性。实际上,他把追求这个同一性设定为自己批判哲学的最终目的。既然同一性是原始智慧所有的,因此也必然会在康德的道德和知识的统一中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康德不承认我们认识的可能性,我们后文有探究。
我们通过分析康德文本发现,康德的文本中潜伏着理智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道德和知识)二者同一性的认识,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同一性认识回头来解读康德的先验演绎来论述二者统一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更进一步确立了道德和知识的同一性。
道德律或自由的因果性是行为主体的人的理知的品格,人的行动在经验现象序列中表现的现象的因果性,就是其经验性的品格,二者是显现与被显现的同一关系。“我把那种在一个感官对象上本身不是现象的东西称之为理知的。因此,如果在感官世界中必须被看作现象的东西本身自在地也有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任何感性直观的对象,但它凭借这种能力却可以是诸现象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存在者的原因性,既按照其行动而把它看作理知的,即看作一个自在之物本身的原因性,又按照这行动的结果而把它看作感性的,即看作感官世界中的一个现象的原因性。因此我们关于一个这样的主体的能力将会造成对它的原因性的一个既是经验性的、同时也是智性的概念,这两者是在同一个结果中一起发生的。在对一个感官对象的能力进行设想的这样一种两面性,与我们关于诸现象和某个可能经验所造成的那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矛盾。”*[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A538,B566,第436页。
同一个行为,按照其行动可以看作理知的,即作为一个自在之物的原因性,而按照行动的结果看作了现象的原因性。我们在这里发现康德不自觉地预设了经验的品格和理智的品格的同一性,即经验的品格可以显现理智的品格,或者用康德批判哲学的话说理知的品格是经验的品格的先验条件。这样,我们可以获得了一个理智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在行动中的同一性的存在证明。
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解读先验演绎证明二者同一的逻辑必然性。
知性范畴客观有效性的先验演绎包括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前者是从经验上升到认识的主观条件,即上升到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主观演绎包括三重综合: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认定的综合。在空间和时间的直观形式中接受的感性杂多,总是要有一个组织和整理,并且“每一个表象作为包含在一个瞬间中的东西,永远不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绝对的统一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99,第115页。。这就是直观中领会的综合。但是直观中的表象如果不能有想象力再生就会在时间序列中永远地消逝了,也就不会在领会中结合在一起,因此想象力再生的综合的追溯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概念中认定的综合,再生的想象力综合也不可能,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再生的表象是否是同一个表象。在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中,我们通过概念范畴的普遍性必然性而给予直观中的杂多以必然的综合统一。康德在论述了三重综合之后,接着就又指出:一切综合又都是毫无例外地以先验的条件为根据的。如果没有这个根据,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综合,从而就不可能思维我们直观到的任何对象。这个本源而先验的条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统觉”。统觉即指“自我意识”,所谓先验统觉是指“纯粹本源的、不变的意识”。康德认为,所有经验对象的统一性都来源于这种先验统觉的统一性,或者说,所有经验对象的统一性都是以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为根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把统觉的原理称为“人类知识整个范围里的最高原理”。*[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5,第91页。
“因此在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那些现象上的秩序和合规则性是我们自己带进去的,假如我们不是本源地把它们、或者把我们内心的自然放进去了的话,我们也就会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它们了。”*[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125,第130页。
客观演绎则是从上而下,它从认识的最高的主观条件即先验统觉下降到范畴对客体的客观有效性。康德认为,由于人类的知性和直观是分离的,因此直观杂多的综合联结必须另有来源,那就是这一普遍必然的联结必须来自先验统觉的自我同一性原理。先验统觉的自我同一性只是通过对感性杂多的联结才实现自己的同一。“统觉的必然统一这条原理是自同一的,因而是一个分析命题,但它却表明直观中给予的杂多的一个综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综合,自我意识的那种无一例外的同一性是不可设想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5,第91页。先验统觉对杂多表象的联结是通过“是”为联结词的判断进行的。“是”在康德的先验逻辑里和形式逻辑的功能是对应的。“一个判断无非是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同一性的方式。”*[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43,第95页。因此有多少种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就有多少种知性范畴。一共有4类量、质、关系、模态12种范畴(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交互作用;可能或不可能、存有或非有、必然性或偶然性)。知性范畴综合感性杂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来自先验统觉,知性的12种范畴不过是先验统觉综合表象杂多的12种表现形式。“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同一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46,第97页。这样,康德就证明了知性范畴的客观有效性。
先验统觉即自我意识是康德理论理性的最高原理,它是自我同一的,但是它的这个同一是个综合的行动。先验统觉既然不是经验来源的,就属于理智的品格,它的原因性就是一种自由的原因性*康德的道德律自由的因果性和先验统觉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等同的:自由的因果性是自然因果性的无条件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自然因果性的根据。同样,先验统觉是因果范畴用于自然的最高原理,后者只是其一种表现样式,因此先验统觉也是自然因果性的根据。这二者存在着统一性。。“通常仅仅只是通过感官而知道整个自然的人,也通过单纯的统觉来认识自己,也就是在他根本不能归于感官印象的那些行动和内部规定中认识自己,他对他自己来说当然一方面是现相(Phaenomen),但另一方面,亦即就某些能力而言,则是一个单纯理知的对象,因为他的行动根本不能归入感性的接受性中。”*[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42页。我们把(自然的因果性)范畴的先验演绎看作一个行动(为自然立法),那么先验统觉就是一个自由的因果性,它产生的结果即自然的因果性。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自由的原因性和自然的原因性的同一性。
康德认为,自由的因果性是知性世界的规律,自然的因果性是感性世界的规律,知性世界是自然世界的“原型”,感性世界是知性世界的“摹本”。*[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46页。自然的因果规律是自由的因果性规律的范型:“道德法则除了知性(不是想象力)以外,就没有其它居间促成其运用于自然对象上的认识能力;而知性为理性理念所构成的基础不是感性的图型,而是法则,但却是能够具体地在感觉对象上呈现出来的法则,因而是一条自然法则,但是这仅仅据其形式而言,而作为法则其鹄的在于判断力,于是,我们能够名之为道德法则的范型。”*[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75页。
只有道德法则即自由的因果性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因为它是绝对的命令和职责(即“应该”),其他的一切普遍性和必然性都是派生的。所以,先天综合命题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或知性范畴的普遍必然性来自先验统觉的本源的统一性。先验统觉就是纯粹的理性,它不能直接连接感性材料,它只能通过知性范畴,但它作为理性“它本身就是实践的”,它具有自由的原因性。这个自由的原因性就造就了自然的原因性,也就是普遍必然的自然规律。这样我们通过揭示先验统觉和道德律的同一性,就把认识建立在了道德实践基础上。
三、西方传统:分裂人格和双重世界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自由和自然的同一性或者说道德和知识的同一性是本源的同一性,对于康德来说二者却是分裂对立的,而同一性只是一种希望或信仰(神学和宗教的需要)。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从康德文本中释读出的自由和自然的同一性,对康德来说就是视而不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把康德的哲学放到整个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进行。
康德之前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乃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认为理性一旦发现就可以按照其设计改造人生。康德对这种独断论进行了批判,从而借助自然合目的性原理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大自然的创造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就是自由意志的人。但是在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意志自由,从而错误地利用了自己的自由,使其服从自己的动物性、社会性的欲求。康德称之为人类伦理上的自然状态,充满了战争和冲突,大自然就借助这个对自由的误用,促成了科学技术的发明,造就了人类文化的进步。康德认为,伦理上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人性陷入“根本恶”的状态,这是与意志自由不相称的,因此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伦理上的“目的王国”。康德为结束普遍的战争状态设计了万国法。为了使人摆脱与生俱来的根本恶,康德设计了从基督教脱胎而来的理性的宗教,提出了弃绝旧人(根本恶)成为新人、并进入道德共同体、最终实现目的王国的设想。康德的历史观和人性论是从基督教的历史观和人性论中脱胎出来的。

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路径也造成了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别。在中国从家族到国家的演进,造成了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而西方文明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从家族到国家的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没有继承家族而发展出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而是走向了多元的贵族封建制和多元的资本主义。
中西哲学也因此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哲学的人格是和谐的人格,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合一的,而希腊哲学则把灵魂和肉体看作是相冲突的;中国哲学追求的就是和谐人格,如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其主流的伦理学却是所谓的“战斗模型”:灵魂和肉体冲突不已。
西方文明经过私有制进入国家的文明道路,形成了其分裂人格。在其中,感性与理性(在认识中是理论理性,在道德中是实践理性)是分裂的,因此在伦理学中无法实现人和道德律的一致,而只是把道德律强迫自己遵行。在认识论中,感性与理性(理论理性)的分裂导致二者的结合只能是后者把范畴强加到前者上,从而导致物自身的隐藏,无法实现对物本身的认识。不仅如此,我们看到理性自身也因此而遭到分裂的命运,其自身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的同一也是遥遥无期的,康德同样把它推给上帝,只有在上帝存在的设定下,作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同一,或道德和幸福的配称的至善才有可能。我们认为,在实践的过程中,道德和知识是可以合一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一致也可以达到。自由的目的性和自然的目的性的同一(即体用关系)就是本源的,只是因为理性与感性的分裂,康德才视而不见,不能觉察出来。
中西哲学道理是相通的,即只有实现了道德律和人的自然性的和谐,人才能够获得人格的完善,也才能获得物自身的认识,才能获得与德性相配的幸福。西方文明发展因为走向了私有制发达的破裂型道路,因而告别了文明之初的和谐以后,就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而不能自拔。
四、体用论:因果问题的解决
自然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的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局限在知识论的范围内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必须要沟通知识和道德两个领域,才能够明确自然的因果性范畴的来源:先验统觉就是自由的因果性,就是道德自律。我们发现,自然的因果性之普遍性必然性,最终要追溯到康德的道德律的强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强制性源自感性和理性的(人格的)分裂。我们看到了康德论证的有条件的合理性,但是关于这个康德未曾明言的条件,我们发现存在着问题。自然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一个预设了分裂人格和知识与道德二重世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知识论命题,是欧洲文明的地方性知识,它在古希腊和现代的机械论科学观中有核心地位,但在其他文明中就没有这种地位。
如果我们追溯因果律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来源,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因果规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最终来源,职责的必然性即道德律的强制性。而道德律的强制性是因为“有限的人”不能和道德律一致——服从道德律是出于义务和职责,而不是出于爱好。康德的“有限的人”就是陷入“根本恶”的人,它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破裂性造成的。
而中国文明的形成路径是连续性的,因此就没有私有制膨胀带来的人格的分裂,也没有形成二重世界的世界观,因此这个文明培养的人就具有了本源意义上自我同一的人格,这就是孟子性善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缘由。因此对于儒家来说,人性本善就为道德自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里的道德自律不是康德的空洞的逻辑形式,而是落实到实践行动中的道德自律。换句话说,道德律不是人强迫自己遵守的,而是自觉地和道德律一致,从而道德律已经变成为人的“本性”。这样道德律对人的强制性就消失了,于是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消失了。
二元分裂人格是陷入了自我冲突中的人格,其中纯粹理性和感性直觉造成了冲突,一种情况是纯粹理性必须和感性直觉结合,另一种是纯粹理性必须和感性直觉分裂,前者是理论的应用,后者是实践的使用。和感性直觉相结合理性就自我坎陷成了知性(范畴),和感性直觉分离就成为自身就有“实践力量”的纯粹理性。如果理性可以不用和感性分离就可以保持自己而不陷溺于感性之中,那么感性和理性就融合为一,也就是成为和谐人格而不存在上述冲突了,于是纯粹理性的道德律就不是强制性的,而知性的因果范畴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样,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和理论使用就结合为一:理论必须来自实践,实践也必须从理论开始,二者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知识和道德的一致性。
对于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的上述认识,可以归结为如下:关于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问题,只是一个西方文明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我们只有体用和道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对因果问题的解决。
[责任编辑:勇君]
KantandtheSolutionoftheProblemofCausality
QIU Wen-y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In order to resolve Hume’s problem of necessity of causality, we must inquire the unity of freedom with necessity. Kant did not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unity but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cognition. In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we can find the original unity of moral freedom and natural necessity, through which the solution to Hume’s problem could be worked out and judgment could be made regarding whether Kant had resolved this problem.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Kant;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theory of noumenon and express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2008-06-16
邱文元,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后(济南 250100);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曲阜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