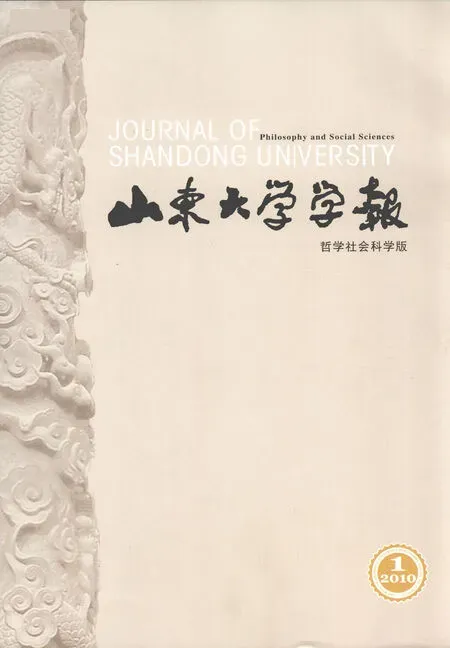论和谐派美学中的丑学理论研究
2010-04-12张中锋
张中锋
论和谐派美学中的丑学理论研究
张中锋
与其他实践派美学流派不同,和谐派比较重视对丑学理论的研究与运用,如代表人物周来祥、邹华、牛宏宝等在他们的一些著述里,对于丑的产生、价值、地位、审美特性、本质、特点等均有所论述,并逐渐使丑学理论走向体系化。和谐派美学流派中的部分同仁之所以如此看重丑,这一方面与丑学在美学中的地位日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和谐派美学体系的建构需要否定因素有关。尽管如此,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对丑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其中对于丑本质的挖掘、审丑可能性的论述、丑特性的概括,以及把丑放在一个动态状况中来考察的做法,还是应该引起“丑学界”关注的。
和谐派; 丑学; 崇高; 体系化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学界便逐渐开始了对丑学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丑学毕竟是美学体系中的一部分,虽然与狭义上的美相对立,但从广义上说丑学仍属于美学,可以说没有丑学研究的美学是残缺的、不完善的;另一方面在美学研究相对沉寂的今天,开启丑学研究更有利于推动美学本身研究向更深更广发展。基于这两点原因,近30年来,丑学研究在当代美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如今你随便打开一本美学教材,基本上都能看到为丑所设置的章节。但是也应看到,由于丑学与当代占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存在着哲学观念上的分歧以及所处地位不同,丑学的发展空间难免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挤压,再加上大多数人对丑作望文生义的误解,因此,当前丑学研究仍举步维艰,成就也差强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和谐派对丑学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丑学理论的发展。同时由于和谐派研究者们能够把丑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应用到美学体系的建构上去,从而使和谐美学体系自身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显然,和谐派美学流派之所以如此看重丑学研究,除了丑学研究也是美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领域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对自身理论的建构需要。和谐派美学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但是在逻辑上却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辩证法对否定因素的肯定为和谐派研究者们注意吸收美学的对立面——丑学提供了可能。为此,和谐派部分同仁对丑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成就比较大的当推和谐派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周来祥先生,以及他的两个高足和同仁邹华教授、牛宏宝教授。他们对丑的研究都以“崇高”美学范畴为切入点,进而对丑的产生、价值、地位、功能、本质、特点等均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逐渐使丑学理论走向体系化。尽管三者都认为丑来自于崇高,但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储备和研究目的差异,他们所研究的着眼点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周来祥主要是从宏观研究出发,提出了丑是由崇高走向荒诞的中介等观点;邹华则是从微观上研究丑的产生,认为丑是进入美学领域的恶;而牛宏宝则更偏向于关注丑的本质研究,认为丑不过是主体非理性强力意志的直接表现等,这些不同有利于促进丑学理论向着纵深、全面、系统化发展。尽管和谐派同仁们对丑学研究的目的存在着功用性,以致于有些丑学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和展开,但和谐美学体系的逻辑严密性以及丑学在该体系地位的重要性,又无形中使得丑学研究带有极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下面就对上述三位学者的丑学理论研究状况分别加以论述。
一、丑是由崇高走向荒诞的中介
周来祥在经营建构他的和谐美学大厦时,较早认识到了丑的价值。与一般的美学家认为丑是负面的、静态的、衬托美的看法不同,周认为丑是具有否定价值的和积极作用的;丑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近代产生的;丑的存在不是以丑衬美或化丑为美,而是一个积极活跃的独立美学范畴。周认为:“当丑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之后,我们对美的范畴和形态,也会产生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看法。过去我把美分成古代和谐美、近代崇高美和现代辩证和谐美三大形态,而在丑独立之后,特别是它作为西方近现代美的典型形态之后,那么审美的对象和形态实际应是古代和谐美、近代丑和现代辩证和谐美三种,而崇高和荒诞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只是美和丑的组合形态。”*周来祥:《三论美是和谐》,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7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和谐派美学体系看作是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那么丑就是这列火车的内燃发动机。因此,如果研究周来祥的美学理论不研究丑,你就会不得要领;如果对丑的研究不看周来祥的理论,对丑的研究也就会失之偏颇,因此,认真研究周对丑的论述,将有着深入研究丑和研究和谐派美学的双重功效。

对待丑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待人自身的态度,丑的本质说来复杂,实际上就是人自身的感性欲望问题,对丑的承认与否关系到人自身的自由程度和解放程度。在传统社会丑是得不到重视的,因为受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制约,客观上人的欲望必须受到抑制。而到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急剧增加,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冲破古典理性束缚,满足个性欲望的时代到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并不是人的所有感性欲望都是符合美的丑,它必须有一个机制来界定什么是符合美的丑,什么还只是符合欲望的丑,丑的本质是什么?审丑为什么可能?等等。周虽然从宏观上指出了丑的产生发展到独立的过程,给丑已足够的地位,但上述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为周真正关心的还是他的和谐美学大厦,丑再重要也不过是他美学体系中的一环。但尽管这样,周仍然是目前美学界对丑学理论研究比较深刻的学者之一,辩证法的强大力量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使它的丑学研究视野比较开阔,说服力比较强,并为后来许多丑学研究者带来不少的启发,当然受周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他的两个弟子兼学派同仁邹华、牛宏宝等,他们在周的丑学研究的宏大框架下,分别对丑的产生和丑的本质,进行了充分研究。
二、丑是进入审美活动的恶



由以上论述我们看到,邹华仍然是沿着周从崇高的结构来研究丑这条路子走的,也充分肯定了丑的积极的富有否定的特性,肯定了丑是一种新的美学范畴的诞生,同时用“熵的增加”和“美的扩散”来论述“丑”,便显得形象而别具一格。
三、丑是非理性强力意志的直接表现
牛宏宝对丑学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康德关于崇高的原典论述上去,重新对丑的本质进行发掘;二是对尼采的美学加以研究,试图寻找到丑的本质,以便论证丑之所以独立和审丑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三是对丑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较好地概括,使丑学研究逐渐趋于体系化。
牛继续通过研究康德的崇高来发掘丑的来源,这一方面是对周来祥和邹华研究丑学路径的继续,另一方面牛没有停留在周对丑的宏观性论述上,也没有停留在邹对崇高美的迷恋上,而是紧紧凭靠康德本人的崇高观念,来探寻丑何以从崇高中独立出来的原因。牛早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康德在丑面前的尴尬》中,就充分地论述了康德面对丑强大的无奈,并设置了“主观合目的性”以解决客观上“反合目的性”事物大量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康德不放弃这部分“反合目的性”的事物以保持美的纯粹性呢?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康德设置审美判断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沟通自然界和道德界这两个领域,如果轻易拒绝那些粗糙恐惧的事物,沟通的目的就很难达到;另一方面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力”作为一种“反思判断力”是没有界限的,这样康德也就处在两难之中,只好设置“崇高”来解决。因此,牛才会明确指出:“崇高作为独立的审美形态,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即它是丑与美之间的过渡,是能转化成美的丑,或者向丑转化的美。”*牛宏宝:《康德在丑面前的尴尬》,《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合目的性”的事物都能被转化,因为“‘反合目的性’的对象与‘主观合目的性’的达成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旦‘反合目的性’的对象作为美的否定而彻底存在的时候,‘主观合目的性’的链条必然断裂,那时真正的丑就出现了。因此,康德没有让崇高来完成美与丑之间的真正综合,也不可能完成”。*牛宏宝:《康德在丑面前的尴尬》,《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由此看来,从微观上考察丑的产生方面,牛与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牛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牛看来被转化成美的丑还只是形式上的丑,崇高只能揭示出丑的存在,而要真正让丑获得独立,还必须寻找到丑的本质特性,这样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审美观便进入到了牛的视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牛宏宝对丑的产生、丑的本质,以及丑的特性都做了很充分的论述。对于丑的产生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丑来自崇高这一事实,也巩固了周关于丑是由崇高走向荒诞的宏观判断和邹关于丑是进入审美领域的恶的观点。牛对于丑的本质和特征的概括,对审丑可能性和丑感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周关于丑是独立美学范畴的提法,并试图把和谐派审丑理论走向体系化。当然还应看到,非理性主义也仍然是一种“理性主义”,人对丑的接受也得受过较高教育,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众多的观念”(康德语)才行,丑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赏的,与崇高感相比,丑感的要求更高,也更需要培养。还有关于“欲望”亦应看到,人的欲望永远是属人的,它不再有纯粹的动物性。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吸收到丑的本质中来谈的。
四、结语
总的来看,通过以上对周来祥、邹华、牛宏宝等三位学者的丑学观点加以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更注重对丑的宏观把握,对丑的产生、地位、价值的定位是比较确定和明晰的,丑既是崇高对美超越的结果,也是崇高走向荒诞的中介,这不但指明了丑的特性,也为和谐美学体系的建构做了准备。邹华则从崇高的形成,论证了丑是进入审美领域的恶。而牛对丑的本质提出了丑是非理性的强力意志的直接表现的观点,则极大地解决了丑的独立问题和审丑(审美)可能问题。因此,三人对丑理论的建构既各有侧重点,又在周的宏观丑学框架下,实现着丑学理论的趋向体系化,因此,和谐派美学流派对丑学理论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是应该引起“丑学界”关注的。联想到和谐派们对丑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丑学本身而仅仅是为了建构和谐美学大厦时,这种成就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责任编辑:刘光磊]
OntheTheoreticalStudyoftheUglyinHarmoniousAesthetics
ZHANG Zhong-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P.R.China)
Unlike other schools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the school of Harmonious Aesthetics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n the ugly. This is evidenced in 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cluding Zhou Laixiang, Zou Hua, Niu Hongbao and others wherein they expound the origin, value, statu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the ugly. Such studies have jointly built up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ugly. The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the study of the ugly by scholars of the School of Harmonious Aesthetics stem from two facts. First, aesthetic study on the ugl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econd, the building of the Harmonious aesthetic system requires negative factors. All this has pushed forward the aesthetic study of the ugly. Their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ugly, the possibility of aesthetics of the ugly,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gly, and their dynamic study of the ugly well deserve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particularly those engaged in the aesthetics of the ugly.
the school of Harmonious Aesthetics; the aesthetics of the ugly; noble; systematization
2009-08-06
张中锋,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