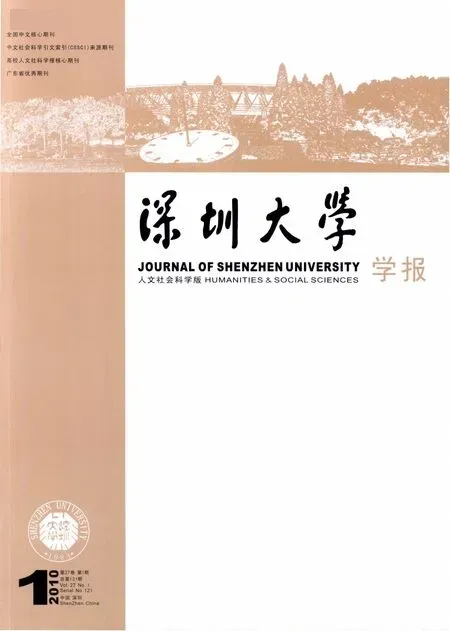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
2010-04-12唐忠毛
唐忠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 200433)
佛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实践,一种社会组织力量,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①。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宗教,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所属的思想、观念与价值通过与中国本土儒道思想的对话、碰撞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佛教自身的文化因素也因此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佛教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其无形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与审美倾向已经涉及并渗透到非常广泛的文化与生活领域,因此需要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展开细致的研究。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在社会系统中,佛教文化对于中国社会与人群的作用与功能,重点是分析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古今之变,以及当代都市佛教的主要文化功能与诊疗价值。
一、中国古代都市佛教的主要文化功能
大量考古史实说明,寺庙、教堂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并使城市发展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如欧洲的城市建筑大都以教堂作为中心,教堂及其广场往往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间。中国佛教由于一直依附于王权,不具有欧洲基督教那样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因寺成镇”②的现象也很常见。当然,“因寺成镇”虽然由于寺院经济的影响力,但其中的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中国古代都市佛教不仅是佛教徒的信仰活动场所,具有神圣与超越的宗教性特征,同时,它也是市民文化的发源地与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具有文化娱乐与文化传播功能,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功能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作为一种信仰与灵性的空间,古代都市佛教承担了政治象征仪式与个体灵性生活的功能。古代都市佛教往往为政府提供带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服务,举行各种法事、斋会。如“国忌日”就需要到寺院中设斋行香,由于参加人员都是国家官员,故称为“官斋”。自宋代起,设在州、府、县的某个城市佛教寺庙往往被指定为地方官员节日行礼的场所。“官斋”之外,一般的法会、超度、礼忏、放生等活动,则往往为老百姓提供了灵性生活的空间,使一般市民获得了生命归宿感与精神寄托。这些法会有的声势浩大,成为古代都市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唐长安高僧普光寺释法常的葬礼,“京寺僧侣门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车,前后威仪四十余里,信心士女执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数万,卿相傧从”[1]。武则天迎接北禅宗神秀入京都时,“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浮拜,日有万计”[2]。而唐代朝廷六次迎取法门寺舍利入京供养,更是成为重大盛事。每次的迎佛骨活动都会引起长安全城的轰动,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长安市民则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农人则“多废东作,奔走京城”。古代都市佛教法会仪式活动是佛教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古代都市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
其二,古代都市佛教由于其自身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往往成为佛教学术研究中心与佛教经典翻译重镇,从而使都市佛教寺院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播功能。就长安佛教来说,它就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历史上出现了翻译佛经的四大译场——草堂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以及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长安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西晋武帝之末,译师为高僧竺法护,译经地点在长安青门外大寺,译经总数为165部,从此开长安佛典翻译事业之先河。此后,长安佛教借助都市佛教的地位与优势贡献了中国汉译佛典中的半数以上。一般来说,大型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还需要组织严密、分工具体的领导与协调,而正是由于都市佛教自身具备的物质与文化保障才使其承担了这一重任,给我们保留与传播了丰厚无比的佛教文化遗产。
其三,由于寺院集中了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品,古代都市寺院往往成为重要的文化艺术展览中心。我国古代大量雕刻、绘画、书法以及碑刻等艺术品,往往被供奉或收藏于寺庙之中。同时,古代僧人往往都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僧人中能书善画的人不在少数,因此他们会自己动手为寺庙进行艺术设计与创造。此外,古代的文人艺术家往往对佛教文化多有喜好,他们通过与僧人交往,并为寺庙增加艺术作品。据《洛阳伽蓝记》(卷二)称,北魏洛阳城东,有专门由“百官等所立”的正始寺,而其余名寺也多为王公将相所立,这些寺院在客观上成为士大夫们与佛教之间的一道桥梁,所谓佛教文化精英往往荟萃于此[3]。《卢氏杂谈》中曾论及长安各名寺中的名画古迹,记述道:“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思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4]
其四,唐宋以降,由于佛教法会中面对一般市民的“俗讲”的出现,使得古代都市佛教寺院逐渐成为市民文化娱乐的重要公共空间。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唐以后,中国寺院已被逐渐嵌入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分身为芸芸俗众的文化娱乐中心,不仅普遍兼有画苑、戏场、公园的功能,而且普遍成为士庶游冶、交友、消闲的场所[5]。在都市佛寺提供的市民文化特色的服务中,还包括诸如住宿、洗澡,甚至宴饮与送行等等,俨然成为古代市民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如,保唐寺的俗讲法会上不仅士子众多,而且不少歌妓也前往凑热闹。孙棨在《北里志》中记载道:“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6]到了宋代,俗讲更为普遍,一般市民老百姓往往借助这些俗讲法会,进行交际活动,甚至青年男女乘此机会进行恋爱。由此可见,古代都市寺院已经成为向公众开放,具有通俗性、普及意义与文化教育功能的社会活动中心。
其五,古代都市佛教还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唐都长安不仅是印度、西域僧人来华的长住地,也是日本、新罗等国与中国互派僧人,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之地。事实上,中国古代各朝各代都之中都有中国都市佛教与国外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例,如近代的上海佛教界就曾与日本、印度、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活动。由此可见,古代都市佛教还俨然承担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
二、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近世衰落与现代转型
自宋明以降,中国佛教义学逐渐衰微,僧人的文化素质逐渐下降,其夕日的文化功能与理性光芒几近淹没。明清时期,不立文字的禅宗与念佛的净土宗合流之后,佛教寺庙往往偏向选择山林僻地,而大多数佛教“名山圣地”都以民间形式的“香火佛教”接引信众;同时,都市佛教的相关文化功能也日趋衰落,惟独盛行荐亡、超度、放焰口等“佛事”活动,并呈现出民间化、俗世化,甚至鬼神化、迷信化倾向。近世中国佛教衰微的原因众多,但佛教义学不振、僧人文化素质低下是最关键的内在原因。事实上,清朝以来佛教寺庙与僧尼人数仍保持庞大的规模。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直省敕建大寺庙6073座,小寺庙6409座;私建大寺庙8458座,小寺庙58682座,在籍僧110292名,尼86015名[7]。进入民国时期,汉地僧尼人数有70多万,但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80%以上是文盲,他们(她们)大多是因为贫苦、战乱、灾难而遁入佛门[8]。由于僧众文化素质低下,因此无法从事佛学研究、讲经说法等佛教文化活动,众多的寺庙与庞大的僧众规模无法掩盖佛教文化功能的衰微本质。
民国期间,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衰微实况,仅以北京与上海两地为例就可窥其全貌。据倓虚法师回忆,民国期间,北京寺院很多,但都以经忏为务,不仅无法师讲法,而且还以攀附官场、争取钱财为荣耀。倓虚法师在其《影尘回忆录》中回忆说:“那时候在北京办一个讲经法会很困难,各庙都不欢迎。据佛教会登记调查,全北京城,大小有1100多处庙,在这么多庙子里,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而且听经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因为清朝以来,北京的旧风气。都是以经忏交际为主,如果能对经忏佛事拿得起来,再能交上某督抚、某提督或王爷,就成功了。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舒服,而却没有人发心出来宏法。这也难怪,因为在过去,旧风气不开通,很少有人提倡,一般人也不知道这讲经的好处。”[9]不仅北京,即使是作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心的上海,其佛教文化功能事实上也在走向衰落。游有维先生在其《上海近代佛教简史》一书中指出:民国期间,上海新兴的寺庙,至抗战前约有149所。这些新兴寺庙,大都是中小寺庙,有的购地自建,有的租屋改建,规模狭小,唯以经忏佛事为务[10]。此外,如当时沪上著名的法师兴慈创立的“法藏讲寺”(1924年起建),也因为寺院经济困难而进行较长时间的经忏活动。事实上,民国佛教经忏之风已呈普遍态势,而其他城市佛教寺院的经忏之盛行,绝不在北京和上海之下。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新学的兴起,中国佛教也面临着“现代性”挑战。如何实现佛教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如何重建现代佛教文化功能成为摆在佛教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一时期,佛教界的有志之士深感佛教文化教育功能的衰败,在杨仁山、太虚等一大批大德高僧的倡导下,僧界与居士界在民国时期掀起了佛教办学的小高潮,企图重振中国佛教的文化教育功能,并以人间佛教的理念来探索佛教的现代转型。应该说,佛教及其文化功能的现当代转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相对于古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现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于理性化的“祛魅”,佛教信仰逐渐成为一种私人的事情,而佛教文化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种。就现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而言,由于政教分离、学校教育与宗教教育分离,寺庙已不再承担政治象征意义,也不承担国家意义上的祀典活动,而是作为一般大众宗教信仰活动的平台。同时,像古代都市佛教中的佛学研究、佛经翻译、佛教艺术活动等功能也逐渐被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所分担;而诸如古代寺庙的娱乐、住宿、洗澡、宴饮与送行等面向市民的服务功能,也被现代专门的服务业所取代。因此,现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相对于古代,其范围已经缩小了许多。
其二,在现代性与理性化的背景下,重建佛教的理性精神与文化内涵成为了佛教现代转型的重要任务。针对近世以来中国佛教的重经忏、重荐亡、重鬼神的迷信化倾向,太虚大师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其重点是:民间观念的启导和传统思想的转化、佛教僧团制度的整顿、僧伽教育的普及等朝向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在观念层面,太虚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理性的祛魅”——即改变传统神鬼的信仰,使佛教成为人生的、生活的佛教,这是佛教面对现代性也是佛教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在太虚等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推动下,近代佛教文化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各种佛教组织、佛教教育机构、佛教学术活动在城市中兴起,为中国都市佛教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解放后及文革期间,佛教又成为“迷信”的代名词,中国佛教作为文化意义的合法性亦遭否决。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出于谋求佛教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地位,也出于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深远与广大,中国佛教界在倡导“人间佛教”导向的同时,一再强调佛教作为文化的因素与功能。在2002年9月16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提出要在弘扬“人间佛教”的同时,要“以文化阐扬佛法”,指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
其三,佛教文化功能中的心理引导、精神诊疗与伦理构建作用在当代佛教文化功能中空前突显出来。“现代性”不仅是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同时它也是作为种种“问题”而存在。佛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独特智慧,其对现代人的惯性与常识性思维具有特别的启迪与反省意义,从而有助于启迪现代人解决各种现代性的困境。同时,佛教教义中蕴涵的“和谐”、“平等”、“慈悲”、“节制”、“奉献”、“宽容”等丰富的精神资源,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伦理觉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当今的社会和谐与个体的心灵愈合。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佛教这一突显的诊疗作用也是佛教回归其原始的精神本怀,直接契入人性与人心,对治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一种内在表现。这种从外在宗教走向内在的“宗教性”与“精神性”的变化,也正如西美尔所言:“克服宗教的现代性危机,不在于致力于宗教教义和机构的现代化(这是徒劳的),而是个体自决的生命意义的实现。只有内在的宗教性是不会消亡的,它会不断创造出客观的宗教文化。”[11]
三、契理契机的当代都市佛教文化诊疗价值
当代都市生活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背离关系,是都市佛教直面都市现代生活,诊疗都市众生的一个良好契机。作为文明象征的现代都市,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十分丰富,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往往显得相对苍白。都市生活的紧张、忙碌与孤独,造就了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使得都市人的心灵世界有时就像都市的群楼和复杂的交通一样,显得杂乱和堵塞。可以说,现代都市人的各种身心疾病既是现代都市紧张生活的产物,也是都市人展示的人类现代困境——那就是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空虚之间的现代张力。漫无边际的“忙”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现代特征,它打破了应有的自然节奏与内心宁静、异化了人的实存,并将都市人的生活编织在无名的疲惫之中。事实上,简单的、机械的游戏已经无法将现代都市人带向内心的宁静,相反,信仰——宗教的信仰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给现代人以精神的抚慰,心灵的超越。相对于世俗文化,佛教文化可以从一个特殊而超越的视角来启发现代人们的思维,有助于人们走出心理的不安与精神的困境。比如,佛教的自我解脱性思维、佛教的和谐思想、佛教的慈悲理念、佛教的财富观念、佛教的苦乐辩证法、佛教的五戒十善伦理等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世俗文化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当代都市佛教及其文化的诊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引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佛教是一种追求自由和解脱的信仰体系,它有着自身的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并通过其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为人们确立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信仰的迷失、价值的失范导致了私欲的膨胀,从而使得现代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扭曲,并诱导了一系列的“疾病”。从价值观而言,大乘佛教主张的“无我思想”以及“觉我觉他”、“度人以度己”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积极利他、为社会服务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有助于现代人摆脱狭隘的自我欲望,而且还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契合。就人生态度而言,大乘佛教主张“不断烦恼而涅槃,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因此,它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与拥抱困难、知难而上的乐观态度,这有利于培养我们顽强拼搏的人生态度。在行为方式上,佛教的“五戒十善”,不仅为我们确立了向善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向我们指出“节制”生活的重要性。在佛教看来,人的“攀缘心”是无止境的,人们不能任由自己的欲望来牵制自己的行为,只有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才有利于阻止私欲的膨胀,才有助于避免自我的迷失,从而回归真实、健康的当下生活。同时,在具体生活方式上,佛教倡导的“素食文化”、“简朴文化”、“洁净文化”等,也都有助于现代都市人培养科学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与精神愉悦。
其二,发挥佛教及其文化的心理抚慰与精神诊疗功能。佛教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学问,也是一种关于身心的愈合之道,具有积极的精神诊疗价值。在中国,人们不习惯于去看心理医生,不过佛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不知不觉的心理治疗作用。佛教的超越性思维与信仰活动,为人们摆脱当下的痛苦起到了一定的安慰作用,而佛教提倡的修身、禅坐等,也能使人们放松心情、获得心理的平衡,从而增强心理自主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欲望的态度上,由于佛教重视对种种“我执”的消解,从而使人能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得失,心态平衡地承受人生的挫折和失败。事实上,“占有欲”的膨胀是现代都市生活种种病态的根源之一。诚然,恰当的“欲望”是人们进取的动力,但是过分膨胀的欲望则成为人性扭曲的根源,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很多罪恶就是由于人们私欲的膨胀。在佛教看来,执着于自己的欲望就是一种“无明”,是对事物的本性缺乏洞察的结果,是对自己心性本质缺乏了解的结果。因此,只有放弃对自我欲望的无尽攀缘,以利他的精神去面对一切,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解脱。可以说,佛教的心理抚慰功能,既是其信仰的精神作用,也有其复杂的心理学背景。事实上,西方的一些心理学流派如精神分析学派等,早已从佛教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并运用于其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在当今的都市生活中,心理与精神问题越来越多,佛教的独特智慧与文化功能对于舒解人们的不良情绪与心理精神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理应日益获得人们的认同与关注。
其三,提供积极的伦理价值,树立诚信的优良品格。佛教有着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行为准则,并以此影响广大的信教群众,维系社会的稳定。因此,深入挖掘佛教中积极的伦理价值,可以在引导树立社会道德规范、稳定社会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佛教的“五戒十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为人们树立利他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持。就经济伦理价值而言,马克斯·韦伯就曾详细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基督教的伦理价值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在韦伯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物质的市场部分,还要有精神的支持,而新教伦理主张的“天职观念”与“入世禁欲”的克己节俭精神,恰恰促进了西方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事实上,佛教伦理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大乘佛教的“五戒十善”、“出世与入世不二”、“人成佛成”、“人间净土”等思想理念都可以进行现代诠释,从而有助于培养利他、诚信、勤劳、公平、服务众生的价值观。而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佛教不仅主张财富的积累要通过合法的 “正业”来取得,还主张通过积极的“布施”,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社会上的弱势人群,从而回报社会和众生。
其四,培养和谐、和平的理念与互助互爱、抚危解困的慈善精神。佛教是和平与和谐的宗教,佛教文化也是一种积极倡导和平与和谐的文化。佛教文化的和平与和谐理念,源自佛教教义自身的理性与慈悲精神。在佛教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以及各种现象的产生,皆由其“因缘业力”所致;要解决各种纷争与矛盾,任何非理性与暴力都将无济于事,只有洞察万事万象复杂的“缘起”,坚守“因果法则”,并通过其自身的积极拯救才是真正的出路。在此理性智慧的基础上,佛教还认为,世界上一切众生与万事万物,其在究竟的层面上都是平等的;不仅“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而且从“正报”与“依报”的关系上看,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一体而平等的关系。由此可见,佛教的和平、和谐的文化理念,在当今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不仅将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的和谐、生态秩序的和谐,同样也有助于现代文明病下的个体心灵的愈合与回归本真自然。此外,佛教文化中除了“智”的一面,还有“悲”的一面。“慈悲喜捨”是佛教文化的重要部分,被视为佛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中国慈善文化和慈善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当代,都市佛教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在慈善文化上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能以其实际行动来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安定团结。
四、结语
依托佛教的独特智慧,挖掘佛教中种种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食粮,发挥当代都市佛教文化的积极诊疗功能,将有助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引导、伦理建构、心灵净化与精神提升,同时也有利于现代都市的和谐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诚如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佛代会上所倡言:“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12]如何把佛教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智慧,转化为现代人生活和工作的有益的启发和指引,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巨大的心灵文化工程,也是佛教在当代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探索目标,这个目标需要佛教界和相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当然,佛教的文化功能的发挥,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精神诊疗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个体参与者的积极实践。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功能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的说教上,更应该体现在个体参与者的修持实践中。佛教的修持,也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过程。其中,“真”就是领会 “四圣谛”,排除世俗偏见,把握真如实相;“善”就是戒和定,克己奉公,利益众生;“美”就是由善的伦理规范行为而获得的内心的和谐与解脱,是通过修持实践而获得的人格美和境界美。
注:
① 今天所说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含意是耕作、培养、加工出来的人工事物,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事物相对应。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 ylor)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指出:文化或文明,从较广的民族之意义上看,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2001年版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中,将“文化”定义为“不同历史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工具、符号、习俗和信仰等等”,该词典还引用了辛格尔所编著的《美国哲学》中对“文化”的定义:“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与价值观念组成的相关网络。”(参见尼古拉斯·布宁和余纪元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第222—223页)由此可见,佛教作为一种信仰、观念与价值系统,无疑也应列入“文化”之中。
② 各种地方志及相关文献资料证实,佛寺在中国城镇崛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城镇都是直接从庙会发展而来。仅以上海为例,如“龙华镇”是由“龙华寺”发展而来,“法华镇”是由“法华寺”发展而来,“真如镇”是由“真如寺”发展而来,这些镇都是因寺而成、因寺而得名。
[1]道宣.释法常传[A].道宣.续高僧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赞宁.神秀传[A].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参见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4]黄夏年.“都市佛教与人间佛教”研讨会综述[A].都市中的佛教[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48-371.
[5]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A].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
[6]孙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A].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清朝续文献通考[A].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487.
[8]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3.
[9]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上册)[M].青岛:山东青岛湛山寺印. 89.
[10]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58-159.
[11](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曹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1.
[12]参见赵朴初于1993年10月15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