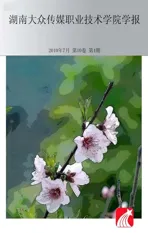《大国崛起》:一个迷你型文化事件
2010-04-11黄林非
黄林非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主持与播音系,湖南 长沙 410100)
央视经济频道播出的《大国崛起》,在狗年岁末的中国大地搅荡起一股谈论“中国崛起”的热潮。这个电视纪录片引发了人们对世界历史和国家未来的关注和思考,国内外主流媒体纷纷加以报道评介。它承继了20世纪初启蒙者的言说姿态,回应着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精英口吻,在提供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的同时,再一次照亮了尘封在历史暗角里的关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的陈旧话题,成为大学讲坛上知识阶层手中的时政分析案例,也为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国事开拓了一方诗意的想象空间。在经历一段短暂的疑似历史青春期所特有的想象和兴奋后,人们似乎又迅速从虚拟的思想前线集体撤退,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伴随着学界名流和民间思想者一阵颇为热闹的“力挺”或“酷评”,在节目策划者和创作人员收取了极高的收视率和轰动效应之后,渐渐归于平静。
应当承认,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众口难调的时代。大众文化的过度繁荣让人们不仅在稍有深度的读物面前哈欠连天,而且在一道道娱乐大餐和一轮轮视听刺激面前开始觉得麻木与腻味。打开电视机,低俗的娱乐节目千篇一律地闹哄哄地维持着空洞的笑脸,弱智的智力抢答题每天都在声嘶力竭的主持人口中批量生产,无聊的戏说历史和名人访谈也已经令人面带倦容。毫无疑问,一部交织着文学、学术、政治以及媒体意识的《大国崛起》进行了一次收效良好的尝试,它的背后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三方会谈。这个电视纪录片是一场包含了汹涌海涛、庄严建筑和异域风情的视觉盛宴,这里有队伍庞大的由学者和政要联袂组成的超强明星阵容,有“以史为鉴”的学术探讨意向,有“和平崛起”的官方命题的主旋律理论基调,有中国国力日趋强盛的现实生活背景。从吸引观众目光并产生普及历史常识和激励人心的效果来说,《大国崛起》的成功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当我们郑重其事地细读这个电视文本时,一番必要的挑剔和适度的批判似乎不可避免。这部片子真的“注重历史带给现实的思考”、“建立历史理性”了吗?我看未必。甚至恰恰相反。《大国崛起》的最大缺陷正在于历史理性的迷失,是一个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没有独立思考而且逻辑混乱的东西。在对近五百年来主导世界的九个大国的兴盛过程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后,本该成为点睛之笔的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却显得疲惫不堪、小心翼翼、矛盾重重。它得出的结论,诸如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加强合作、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等,几乎全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正确的废话。除了挥洒着“大国之谜”、“大国之惑”、“大国之路”、“大国之思”之类大而无当的空洞语汇外,其实,《大国崛起》并没有真正“思考”或“探讨”什么深刻的或者有新意的东西。比平庸的结论更为遗憾的是,整部《大国崛起》的历史叙事暴露出令人吃惊的理性缺失。
在价值取向上,《大国崛起》以政治、经济的实用功效为基点,借用韦伯的话来说,是把“功用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当作衡量历史进程的唯一标尺,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被弃之不顾。于是,富国强兵、弱肉强食成了历史进步和文明衍化的基本价值诉求。用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实用眼光打量历史,“崛起”的目标便被摆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而人类的友爱、互助的价值理想为之毫不犹豫地作出了牺牲。海盗的行径功绩卓著,郑和下西洋只能是无功而返的值得揶揄的蠢笨行动。在这种狭隘眼光的裁剪下,文化传统的作用、现代化带给人类的精神危机等许多历史细节被一笔抹煞,“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留下的只是“九个世界性大国”乐此不疲的捉对厮杀。面对鲜血淋漓的“竞争”,《大国崛起》欢欣鼓舞,豪情振奋,“主宰”、“称霸”、“荣光”之类的华丽诱人的呼号划过历史的天空,发出巨大的轰响,种植着非理性的铁血崇拜的阴霾,麻醉着世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纪录片里,葡萄牙凭借“强大的王权”和殖民掠夺奋然前行,西班牙在扩张中“收获”了美洲——“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荷兰在与苏格兰人的三次战争中“脱颖而出”;英国人怀抱“远涉重洋的信心”,在“前赴后继”的海外掠夺中开疆拓土;拿破仑的铁骑踏遍了欧洲大陆,“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一面是有意的揭示,一面又是无意的遮蔽。《大国崛起》以饱满的激情和赞赏的语调描述着一场接一场大快人心的拼杀,丰富复杂的文明史被简化成一只扣动扳机的毒手和一双贪婪的眼睛。虽然在片尾勉为其难地陈述了“历史的教训”,但这一微弱的声音更像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技术性处理,而不是贯串在整个历史叙事之中的内在反思。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曾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写道:“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据于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如果说陈独秀在国势颓败、民族危亡的历史氛围中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以偏激的方式体现了一种问题意识,其良苦用心值得理解和同情,那么,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而贫富分化加剧、欲望合流而利益分配失衡、亟需呼唤公平、亟需关怀弱势群体的现实中国面前,《大国崛起》从胜者为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点出发的对“崛起”的解读和艳羡,究竟意味着什么?
激进的功利主义心态和口号在中国从来就容易收获掌声,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总会有一些冷静的思想者在寂寞中坚韧地对它进行质疑。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到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被众多的激进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遭遇了哲学反思,文化与道德价值得到有力的意识性防卫。艾恺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更是深入分析了“擅理智”(ration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必然导致的“讽刺性的非理性”。一百多年来,当国人比较中西文明之差异、试图学习西方以至赶超西方时,争执不休的核心问题通常是:以自由平等本身的价值为理想,还是以富国强种的目标为理想?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容易相互分离的两种倾向。作为一个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探究,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学理上的“思考”似乎总会有些远离现实。但是,当下中国物欲空前膨胀、人文精神失落、浮夸冒进之风盛行的社会百态,还是不难让人对一声“崛起”背后的激进心态保持一份应有的警惕。
《大国崛起》中有这么一句:“大国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都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这一平实的话语多少道出了创制者运思过程的艰辛和窘迫。实际上,这个纪录片的叙事线索和叙述着力点还是较为清晰的。除了战争,它的另一个突出中心词非“领袖”莫属。由于过分集中地把国家强盛的功劳和荣耀堆砌在领袖们头上,《大国崛起》简直就是一场贤明君主和英雄个人的形象展览。“雄才大略”的恩里克王子;“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庄严高傲的王权偶像”、“凶狠的老母鸡”伊丽莎白一世;“欧洲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孤身一人”带领法国复兴的戴高乐将军;“铁血宰相”俾斯麦;“不顾一切”的彼得大帝;“母仪天下”的叶卡捷琳娜;“钢铁般的领袖”斯大林……在第九集《风云新途》中就有这样的判断:“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英雄史观统摄了整个历史叙事,导致对片中若隐若现的民主诉求的排斥和消解。这样一来,在谋求国家强盛的名义下,在“崛起”的宏伟目标前,专制变得可以接受,自由可以作出牺牲。因此,尽管《大国崛起》赞赏了法国国民的革命激情和《人权宣言》,但事实上,以领袖和英雄为线索的历史叙说内在地规定了该片无法真正面对民主制度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文化观念导致该片对血与火的战争缺乏反思,英雄史观主导下的崛起故事则放弃了对民主与自由的追问。
启蒙者的话语姿态和煽情主义的修辞策略让《大国崛起》着实“火”了一把。观众的兴奋之情联系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追求民族复兴的实践。《大国崛起》所涉及的是一个宏大得难免空疏的话题,这个话题与中国近代以来众多文化事件的关联清晰可辨。从远一点说,它拖着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及国民性改造的五四启蒙话语的长长的影子。无论是“海洋时代”还是“激情岁月”,都流露出对“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语)的想象与憧憬,只不过在对战争与领袖的凝视中淡化了“赛先生”,尤其是淡化了“德先生”的鲜明色彩。从近一点说,它延续了《河殇》的“蔚蓝色”梦幻,在消除了对“黄色文明”的偏激否定的同时,又似乎少了一些痛切和真诚。在《大国崛起》中,随处可见这么一种向着历史高度无限攀爬的煽情表述:“巨大的问号折磨着欧洲大陆”、“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撬动历史的主角就是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胡椒粒”、“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灵”……不难看出,这种言说方式既带着《河殇》的雄壮调子,又依稀晃动着余秋雨散文的深情面孔,是引动观众激情的一个醒目的手势。
《大国崛起》当然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它毕竟只是一款漂亮的文化按摩器。在轻轻拭去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种种历史创痛后,它又亲切地抚摸着每一个渴望国富民强的观众的脸庞。它准确无误地捕获了大众所关注的文化母题(民族情绪及历史情结),牢牢抓住了大众喜爱的叙事模式(中心事件:战争,主要人物:领袖与英雄),恰到好处地采纳了高度煽情的表述方式(华美的语言和非凡的历史高度),最终得以在一阵欢呼与亢奋中引诱出值得庆幸的市场价值回响。它确实以大场面、大视角、大气魄、大手笔为特征。可是,它终究只能昙花一现,而无法演变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