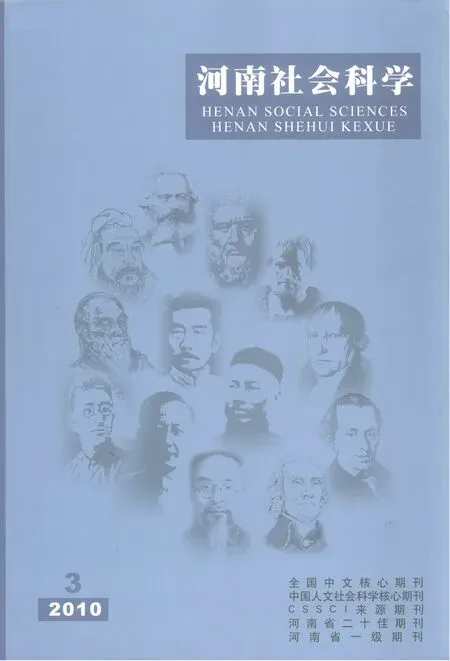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证伪
——基于检察权定性的分析
2010-04-11魏胜强
魏胜强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证伪
——基于检察权定性的分析
魏胜强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我国的检察解释制度受到了各种质疑。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法律依据不足,也不符合法律解释学原理,在实践中会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除此之外,基于检察权的定性进行分析,检察机关也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因为,无论是把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司法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两重属性,还是把检察权定位为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权力,检察机关都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检察机关不行使法律解释权,并不影响其职权的行使。因此,检察机关根本就不应当具有法律解释权,我国当前的检察解释制度应当废除。
检察权;检察机关;检察解释;法律解释权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法律解释权的唯一“法律依据”,是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解释(学界称之为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法律解释(学界称之为检察解释)会发生冲突,该决议专门强调:两种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这显然违背了“法无二解”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使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通过作出法律解释来“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当然,从权力的来源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尽管都拥有法律解释权,但它们权力的法律依据并不相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直接法律授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并无涉及,它仅仅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实际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把《宪法》赋予自己的法律解释权“转授”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种“转让”在法律上很难成立。在实践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个主体作出的法律解释发生冲突而影响案件审理的事情时常发生。在学界,一直有人主张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废除当前的检查解释制度。这是因为,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最终的选择判断权,检察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并不能最终决定案件。
主张废除检察解释制度的学者,多是从法律解释学原理、司法实践中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的矛盾等方面论述的。笔者支持废除检察解释制度的主张,同时认为,检察解释制度应当废除,除以上原因外,还可以从检察权的定性上分析。检察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关于检察权的定性主要有如下四类观点:(1)检察权属于司法权;(2)检察权属于行政权;(3)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4)检察权属于独立的权力①。笔者认为,不管检察权属于哪一类权力,从检察权的权力属性上说,检察机关都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一、即使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也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和法学教科书当中,人们一般把检察权归结为司法权的一部分,认为司法权可以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由法院和检察院行使。这种观点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至今在我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近年,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特别是把检察权归结为行政权的质疑,有些学者又对此观点做了修正,认为虽然检察权在某些方面接近行政权,但并不意味着检察权就是行政权。即使按照三权分立的理论,行政权与司法权也不是绝对分立的,司法权的发展使其自身不断丰富,并在与其他权力相互作用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权力形式。检察权属于广义的司法权,是“以法律监督权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权”②。
如果检察权属于司法权,那么检察机关就属于司法机关。当然,法院更是司法机关。作为适用法律的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应当行使法律解释权。因此,法院(或者法官)必定要解释法律。如果此时检察机关也解释法律,由于不同解释主体的理解和解释常常是不同的,必然导致法院的解释与检察机关的解释发生矛盾。要协调这一矛盾,无非在它们解释的效力上从以下四种方案中选择其一:
第一种方案,是规定法院的解释效力高于检察机关的解释;第二种方案,是规定法院的解释效力低于检察机关的解释;第三种方案,是规定法院的解释与检察机关的解释在效力上相同;第四种方案,是规定当检察机关的解释与法院的解释相矛盾时,报请另一个机关决定适用法院的解释或者适用检察机关的解释。
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就意味着检察机关的解释要服从法院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作出的解释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对案件没有决定性,充其量只是法院审判案件时的参考。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那么法院的解释要服从检察机关的解释,法院事实上对案件没有决定权,这显然使法院形同虚设。如果选择第三种方案,就会违背法无二解的基本原则,也会导致检察机关干预法院的司法活动和法院无法司法的后果。如果选择第四种方案,那就意味着法院和检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作出裁定的机关才是真正的司法机关,这不仅会导致司法的混乱,更会导致整个国家权力体制的混乱。
因此,当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而存在时,无论它怎么行使法律解释权,都无法调解它作出的解释与法院(或者法官)作出的解释的矛盾,最终会影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如果规定检察机关的解释和法院的解释效力一个高一个低的话,也意味着法院和检察机关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自然都不存在了。由此看来,即使把检察权认定为司法权,把检察机关认定为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也不能因为具有了司法机关的属性就能够行使法律解释权。
二、即使检察权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也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有种观点把检察权视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例如有学者认为:其一,在检察机关的设置上,目前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是实行“检察一体”,即检察机关对外是一个整体,对内自上而下是一种领导关系。将检察权归属于行政权,既体现了检察权的本质,又符合世界潮流。其二,将检察权归属于行政权,符合诉讼构造理论。将检察权归入行政权,使检察机关成为刑事诉讼中名副其实的控诉方,才能改变检察机关目前所处的尴尬局面,正确确立符合刑事诉讼构造要求的控辩审三方关系,进一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保障司法审判的独立与公正。其三,将检察权归入行政权,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实现司法独立。检察权作为司法权,是根本无法实现司法中立的。其四,检察权归入行政权,既不会弱化对执法活动的监督,也能保障检察机关集中精力行使控诉职能③。还有学者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从检察机关的起源和历史传统、检察官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诉讼职能、诉讼机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法律监督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四个方面分析,认为检察机关与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在权力属性上把检察机关定位成“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不具备科学的理论依据。作者进一步指出,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权,既有悖于法治社会中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也有悖于诉讼职能区分理论,而且,对法律监督的强调与检察机关必须拥有法律监督权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而,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权这种国家权力配置模式是反科学的。最后,作者明确指出,从权力特征上看,检察机关的职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和必然的联系,却和行政权趋于吻合。进而可以认定,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实际上是具有国家公务员性质的承担控诉职能的公诉人④。
如果检察权属于行政权,那么检察机关就属于行政机关。无论怎么说,行政机关都不能行使可以对抗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由此而论,检察机关同样不能行使我国检察机关目前正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也许有人会说,检察机关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而是专职实施刑事法律的机关,它比一般的行政机关更具有法律的专门性,由检察机关解释法律要比一般行政机关解释法律更加准确和专业,因此应由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至少要行使刑事法律解释权。这种观点看到了检察机关组成人员的法律职业素质要求较高,是值得肯定的,却忽略了检察机关的职责和检察权行使的特性。
一方面,在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关系上,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追诉,代表国家提起刑事诉讼,执行控诉职能。这种职能会使检察机关养成一种职业思维,把许多人的违法行为都当成犯罪行为而予以追究。同时,检察机关一般会主动地行使其职权,主动地追究其认为有罪的人。当它进行追究时,其实就已经认为被追究的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而且检察机关一旦把被追究的对象的行为确认为是犯罪行为,就很难再改变其看法。在检察机关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被追诉人都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无法同检察机关相抗衡,他们行使的各种权利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由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不可能是公正的,只可能是倾向于维护检察机关职权的行使,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另一方面,在检察机关内部普遍存在着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如果检察机关有权解释法律,那么直接受理案件的下一级检察机关对案件的解释就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它很可能被未受理案件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所修改,最终要按照上一级甚至更上一级检察机关的解释来定案。而上级检察机关由于没有直接参与案件,难以把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结合起来,它作出的法律解释必然不具有针对性,在适用于案件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因此,检察机关即使是专司刑事法律的行政机关,它这种作为行政机关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解释法律。
三、即使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检察机关也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有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行政权的部分特征,表现在:检察权以法律的实现为目的;检察权贯彻积极干预、主动追究的原则;检察权采取行政权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同时,检察权也具有较强的司法权特征,表现在:检察权的运作追求合法性,以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为目标;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见,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准确定位应当是过渡性的,即检察权具有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将检察权定性为行政权或司法权,甚至法律监督权,都失之片面⑤。有的学者赞同检察权的双重属性说,认为我国的检察权也具有双重属性,但在我国,从法制上说,应当把检察权定性为司法权,把检察机关定性为司法机关,把检察官定性为司法官。这是因为:其一,有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独立性;其二,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而且在体制上已经脱离行政系统成为相对独立的另一类司法权;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强调检察权的司法性并由此强化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应当说具有普遍的趋势⑥。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就同时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司法机关。前面已经分析过,检察机关无论是作为行政机关还是作为司法机关都是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的。而当它同时作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时,更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因为此时它作出的法律解释既是行政机关的解释又是司法机关的解释,这些解释当然会直接应用于它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当它以司法机关的身份活动时,它也在把行政机关的解释贯彻到它的活动中;当它以行政机关的身份活动时,它也在把司法机关的解释贯彻到活动中。显然二者分别有行政干扰司法和司法干扰行政之嫌,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讲不通的。
四、即使检察权属于独立的权力,检察机关也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有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一项独立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与之并列的权力。例如有学者认为,检察权中的侦查权具有鲜明的行政性,“检察官一体化”是检察权的运作方式之一,这两方面使检察权具有了行政性,但它们只是检察权的局部特征,不能反映检察权的全面和根本特征。同时,检察权还具有浓厚的司法色彩,比如公诉权是具有司法性质的权力;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检察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检察官与法官享有同等或接近的职业保障。但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最根本、最本质的属性,即中立性和终局性,所以检察权不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也不是“另一类司法权”。作为检察权主要内容的公诉权实质上是一种监督权,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特点,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都只是检察权的兼有特征和局部特征。因而,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既不隶属于行政权,也不隶属于审判权。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处于同一系列之中,并对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和审判机关的司法行为的合法性依法负有监督的职责⑦。
还有学者认为:其一,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接近度”以及检察官与法官的“近似性”并不具有充分理由告诉我们检察权就是司法权,“接近度”、“近似性”本身就表明它们之间有距离,而且检察权的特征和机构设置同司法权的内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称检察权为司法权或者检察机关为司法机关都是一种不科学的、不规范的概念。其二,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和行动原则与行政机关有相似之处,也不能说明检察机关就是行政机关、检察权就是行政权,毕竟它们有不同之处,将检察权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权抹杀了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判断权和处置权。把检察权归属于行政权易导致行政恣意,把检察权归结为司法权则产生司法不公,因而应跳出“三权分立”的思维定式,在三权之外寻求检察权的合理位置。检察权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是专司国家追诉权的社会公共权力,是社会发展的选择,客观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它应当定位于与行政权、司法权共享的执行和实施法律这一平台上⑧。
此时,我们或者把检察权定位为独立的法律监督权,或者把检察权定位为独立的追诉权,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当检察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的时候,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它的职责是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仅意味着其他法律实施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处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更意味着其他法律实施机关在其职权活动中都要以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为准,否则它们的活动最终都会被检察机关认定为违法。因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最终不是依法进行的,而是依自己的法律解释进行的。这样的话,检察机关事实上就变成了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太上皇”,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和腐败。有学者对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活动提出了质疑,认为现代诉讼程序本身就设置有防止司法权力异化的制衡机制,因而根本无需任何一种公权力来担当“站着的法官”这一角色。如果置诉讼机制内在的公正性和规律性的要求于不顾,人为地在诉讼中另设立一种由检察官主持进行的法律监督机制,就会使诉讼程序自身的平衡性完全被打破,权力的分立制衡机制将成为虚无,易于滋生司法的专断和腐败,所有的民主诉讼原则也因此而有可能完全丧失其本来的意义,沦落成为一种实现某种非法目的的幌子。与此同时,这种一体化的权力运作机制由于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很容易演化成为一种失去制约的专断性的权力。很明显,它的人治社会的色彩极其浓厚,从本质上说,与封建社会诸权合一的体制并无太大的区别⑨。这种观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行使独立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行使了法律解释权,这种观点所描述情况的出现就不是没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当检察权是独立的追诉权的时候,检察机关如果有权作出法律解释,它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解释在行使追诉权,而案件最终要由法院来作出审判结果,检察机关的解释未必会得到法院的认可,这种解释事实上没有意义。而且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由于各自的解释不同,实际上是分别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了追诉和审判,这样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不利于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追诉权。
所以,检察权不管被定位为一项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还是被定位为一项独立的追诉权,行使这一权力的检察机关都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
五、检察机关不行使法律解释权,并不影响其行使职权
在检察权和检察机关的定性的争论中,任何一种观点都有说服力,观点的不同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审视而导致的罢了。相比之下,笔者更赞同视检察权为一种行政权,认为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是执行一般的行政法的行政权,检察机关的行政权是执行刑事法的行政权。其中的根据,以前的论述已经很多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正如以上分析的那样,不管检察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力,不管检察机关是什么性质的机关,检察机关都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如果检察机关不行使法律解释权,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准确地说,是不具有当前检察解释所具有的那种明确、肯定的约束力),这样的话,怎能约束当事人呢?会不会妨碍检察权的行使呢?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检察权是一种权力,具有强制性。就像行政机关不具有法律解释权也能正常行使其职权一样,检察机关职权的行使也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提出检察机关不具有法律解释权,并不是说检察机关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解释。我们仅仅是想强调,检察机关不能像审判机关那样作出法律解释,更不能作出对抗审判机关的法律解释。而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检察解释居然可以对抗审判解释,检察机关可以以遵循检察解释为由而公然对抗法院的审判,这显然是公诉权对司法权的干扰,这不仅在法理上、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⑩。
总之,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法律解释权,不仅缺乏法律依据,在法律实践中会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而且缺乏权力产生的理论基础,在我国法治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了。要回归检察权的本位,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维护司法公正,就必须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废除当前的检察解释制度。
注释:
①关于检察权的属性,参见张智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理论探索》,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第178-180页;韩成军:《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89—95页。笔者认为,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和独立权力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因而本文仅针对这几种观点展开探讨。
②吴北战,李晓辉:《检察权的法理分析》,载《长白学刊》2001年第1期,第47页。
③王美丽:《检察权的本质及其定位》,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2期,第65-67页。
④郝银钟:《检察权质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71-76页;韩成军:《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载
《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89页。
⑤万毅:《论检察权的定位》,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2-38页。
⑥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第2-6页,韩成军:《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90页。
⑦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4-17页;韩成军:《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90—91页。
⑧唐素林:《对检察权属性定位的重新认识》,载《江汉论坛》2002年第8期,第88-91页;韩成军:《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综述》,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90页。
⑨郝银钟:《检察权质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72页。
⑩这在安徽黄友谊申请赔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黄友谊2000年12月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石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01年7月县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2001年9月黄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赔偿。县人民检察院对黄申请的司法侵权事项不予确认。黄不服,向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市人民检察院复查维持。2002年1月黄向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作出以县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要求县人民检察院向黄支付赔偿金9958.97元。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权将存疑不起诉决定视为县人民检察院对错捕的确认,县人民检察院已经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对黄作出不予侵权确认的确认书,其效力不得推翻,遂拒不执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作出《关于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的批复》,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该刑事案件审查程序的终结,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决定,从法律意义上讲,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该犯罪嫌疑人即是无罪。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认定无罪的决定,同时该不起诉决定即是人民检察院对错误逮捕的确认,无需再行确认。根据《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赔偿请求人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程序合法,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池法委赔字第01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4月作出《关于黄友谊刑事赔偿案的批复》,指出:“黄友谊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而申请国家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八条之规定,石台县人民检察院对黄友谊的申请事项依法不予确认,池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予以维持,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确认的案件,不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作出的赔偿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摘自张兆松:《刑事疑案赔偿问题之检察解释质疑》,载《法治论丛》2004年11月,第31—32页。
责任编辑韩成军
D9
A
1007-905X(2010)03-0081-04
2010-01-02
教育部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820109)
魏胜强(1976— )男,河南遂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法律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