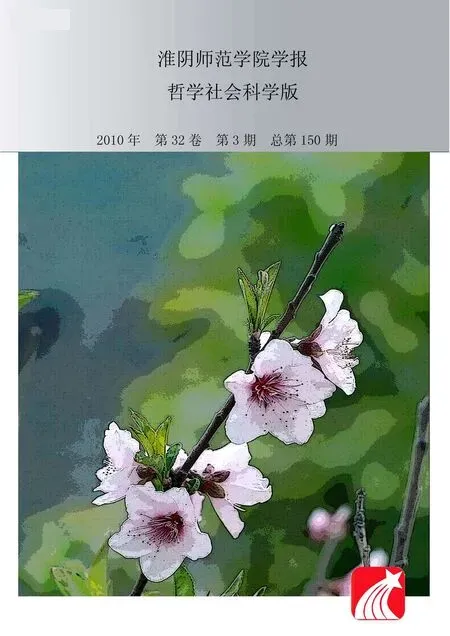传统“虚静”理论的现代审视
2010-04-11武克勤
武克勤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传统“虚静”理论的现代审视
武克勤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传统“虚静”理论的阐释着重于“审美观照”和“审美心胸”的静态内涵,对它的现代审视则指向“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的动态内容与深层目的。在哲学和心理学的视域中,“虚静”既涉及审美心态,也涉及审美方法论。“虚静”的审美态度对于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虚静”理论的现代审视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所要做的,是赋予其更多的时代内容与精神特质。
虚静;审美态度;创作心态;鉴赏心态
“虚静”这一理论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发展是从哲学走向美学的。传统“虚静”理论的内涵从先秦老庄的哲学认识论阐释开始,就已经包含有“虚实结合”、“动静相生”的辩证思维。前人比较多地论述了“虚静”理论中“静”和“虚”的内容,其隐含的“动”态内容大多没有得到具体的阐述和全面的生发,使得这一范畴本身易于被视作是静态结构的呈现。本文主要是从文艺心理学和审美文化的角度对现代“虚静”理论的动态特质进行解析,由此反观传统“虚静”理论“静中有动,动中寓静”、“动极则静,静极而动”的审美特质。
一、“虚静”作为一种审美态度
“虚静”作为传统“审美心胸”理论的载体,其内容主要是精神性的。老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虚静”,强调的也正是认识主体应物体道时必须摒弃一切的功利性欲念,从而保持寂静空明的心灵状态。“虚静”说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把物质性的内容排除在外,它关注的是人的心境,进而又将这一心理内容和人的身体及外部世界完全分隔开来。“虚静”心理中无欲无求、超然物外的身心因素导向了一种审美态度。
审美态度既不同于实用态度又不同于科学态度,它是服务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殊的精神状态。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以木商、植物学家、画家为例,将他们看到同一棵古松时所产生的三种不同态度进行对比,很好地解释了审美态度区别于实用和科学态度的特质所在。木商和植物学家都脱离不了本身的“心习”,前者关心的是古松作为木料本身能值多少钱,后者关心的是古松作为一株植物所具备的属性特征,而只有画家才可以“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1]96。人们在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主体先天既有的知识储备与习见思想的干扰,想要完全超脱于其外并不现实。因此,老庄“虚静”思想中所崇尚的“去知去欲”的精神境界在今天看来是难以企及的。如木商和植物学家,他们在观看古松时已经带有了各自的职业习性,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以审美的态度,而只能以实用或科学的态度去进行审视。其意识是跳跃性的,总是不自觉地由古松联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其注意力没有专注于其中,最终所获得的意象也不是“独立的”、“绝缘的”。相比之下,审美态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1]98。画家完全沉浸在对古松形式的观照中,他不会考虑其是否具有实用价值,也不会去辨别其与另外一棵松树的不同属性,他的唯一目的是将内心所体悟到的美的特征更好地表现于画中。这样的心理活动暂时摆脱了“意志”和“抽象思考”,审美主体在这一前提下就可以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从而在审美态度的指引下促使审美活动顺利进行。
“虚静”作为一种审美态度,主要是指主体在审美发生之前就已经做好的一种心理准备。它贯穿于整个审美心理活动的全过程,不仅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的特性可以归因于心理活动中的“注意”现象。“普通心理学把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并集中于某一对象或活动,称之为注意,而在审美活动中,一当主体的日常意识状态中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并停留在审美对象的形式和结构方面时,则出现了审美注意。其主要生理机制均受中枢神经过程中的优势兴奋中心和相互诱导原理支配。”[2]传统“虚静”理论中的“收视反听”现象,就体现了日常意识向审美意识的转换,这也是一个由体验走向经验的精神提升过程。
“虚静”的审美态度充满着主体心灵意蕴的内容。在具体的审美观照下,主体在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一方面,审美主体将自身的情感潜沉、投射到客体对象上,建立起新的审美意象,这一过程需要排除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主体又将审美意象作为新的客体进行观照,并从中反观自身的生命力量和精神世界。这是对审美意象中所包含的主体情感的再现与再度体验,期间,主体先在的意向结构会产生一定的筛选和影响作用,也使这一过程本身带有了功利性的色彩。审美观照中“入”与“出”的自然融合正体现了“虚静”状态中“动静相生”的心理特质,最终,在外静内动的心理空间内达到了一种积极的平衡状态。
总之,“虚静”这一概念范畴本身可以从“虚”、“静”、“动”三个层面来进行解析。“虚”指空(kōng),与“实”相对,它要求主体摆脱物累,超脱尘世,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从而达到无成见、无杂念的清明心境。“虚”又指空(kòng)着,它不是完全的虚空,而是似虚非虚,虚位以待的心理状态。“虚”也并非虚空一切,主体意识中的审美经验内容是不能被丢弃的。“静”指用心不分,用神不乱,是主体去除纷扰、止息欲望后达到的专一、凝神的心意状态。这一静态的心理空间只是暂时的存在,它在创造着适宜进入审美活动的主体条件的同时,也期待着下一次审美飞跃的来临。因此,“动”即表现为在“虚而待物,静而生思”的前提下心理活动的升华和审美效应的获得,它指向由静态的心理蓄势向动态的艺术兴会的转换,从而建构起“静中有动,动中寓静”、“动极则静,静极而动”的现代“虚静”理论。
二、“虚静”作为一种创作心态
从审美态度来谈“虚静”,强调的是创造一个适宜进入审美活动的审美主体,也即在进入审美活动之前所要保持的特定的审美心理状态,它与主体自身的精神境界和内在修养密切相关。艺术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创作主体心境的影响和作用是贯穿始终的。
“虚静”心态历来被认为是审美创造中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把“虚静”心态看作艺术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心理状态。陆机在《文赋》中说:“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凝思”(艺术思维的发生)必须以“澄心”(宁静空明之心)为前提条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明确指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心态最容易促使作家文思的萌发。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诗人在创作前使自己心空意静,才能营造出美妙的诗语和诗境。类似于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艺术家们在审美创造前必须具备“虚静”无碍的主体心胸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虚静”心态是艺术家创作时凝神观照、潜心沉思的心理状态。艺术创作过程在文艺心理学中被称为“体验的迹化”[3],其中包含了创作发生、审美体验、构思想象、技巧运用等多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个体审美心境在创作发生前即已准备就绪,一旦创作开始进行,这一审美心境就会延续下去,目的是要保持审美注意过程中大脑优势兴奋中心的继续存在,从而不至于让主体的创作意志抑郁沉滞、创作兴致遭到破坏、创作构思中断止息。在预设了“虚静”心态的前提下,创作主体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通过艺术沉思进入创作实践,在构思物化的过程中同样可以获得一种虚静的审美心境。艺术沉思是创作主体对个人情感及理智的一种再度体验,它总是带有一定的内在指向性,即使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也已经受到主体“先见”、“先知”的经验性内容的影响。创作者在体验的同时又将情境中的内在心理转为观照的客观对象,构思就在体验——经验——体验之情理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下去,最终达至物化的高峰体验,也实现了创作主体的审美飞跃。
“虚静”是审美创造的前提,它观照着审美体验的开始,也体味着审美体验的极致。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它呈现为外静内动的心理平衡状态,如《朱子语类》中所说:“人身只有个动、静。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4]外静指向内动,内动体现外静,动静相生,以静养动,最终形成积极能动而富有创造性的动态心理。期间,主体可以充分获得思想解放,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迎接审美高峰体验的到来。“虚静”心态中的“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创作主体内在心灵世界的“静”,这也是自老庄以来的传统“虚静”理论中强调最多的内容。艺术家要关闭外部感官之门,排除杂念欲望的干扰,使“心不牵于外物”,从而为心灵拓出空间,这一“收视反听”的动态过程就是“虚”,心灵被“虚”化之后所呈现出的也是一种“虚”态。二是创作时外部环境的“静”。北宋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提到作画时对环境的要求:“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迓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5]通过种种方式消除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内心的“虚静”。“虚静”心态中的“虚”和“静”都不是纯然绝对的状态,“虚”的目的是“实”,“虚”空了心灵可以更好的体纳外部世界和创造审美意象;“静”的内因是求“动”,过滤心灵,清除杂念,才能为艺术思维活动的展开提供足够的心理空间。创作中的“虚静”心态体现为“虚”与“实”、“静”与“动”两组范畴(四种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融合,其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
总之,审美创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其中的每一流程都必须以主体的心理状态为基础,并且都需要在主体的心理状态中展开。“虚静”心态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不可缺少的一种,它对于审美创作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作用,并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虚静”是创作前的心理准备,艺术家只有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才能顺利地进行创作活动;“虚静”心态使艺术家精神高度集中,从而在审美注意的指引下为艺术想象的活跃运动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心理空间;“虚静”心态使艺术家在审美创造过程中既顺乎自然又超越技巧,最终在物我浑融的妙境中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即使在现代的艺术家们看来,“虚静”心态在创作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虚静”作为一种鉴赏心态
对于审美主体而言,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是双向交流的过程,它们都是对生命体验的一种阐释。没有鉴赏主体的参与和响应,任何创作活动都只能停留在物化阶段,创作主体所阐释的生命体验是否具有自身的价值也只有在鉴赏主体那里得到确证。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鉴赏主体的心理体验是对创作主体原体验的一种延续和升华,鉴赏主体以什么样的心境去进行体验将会直接影响最终的鉴赏效果。“虚静”心态无疑是鉴赏心态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虚静”作为一种鉴赏心态的主要功能是创造一个适宜进入鉴赏活动的审美主体,它同样也是首先指向鉴赏前的心理准备。这一过程中,鉴赏主体能否保持内心的宁静澄明状态是首要的,只有在那样的心境中,日常意识才能逐渐转向审美意识,进而应对鉴赏活动的随时发生。艺术鉴赏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鉴赏者在对作品内在意蕴和旨趣的体味中,使自己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同时,他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对艺术作品作出审美判断。这其中,既有情感的投入,又有理性的指引,鉴赏者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整个鉴赏过程在“虚静”心态的控制下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平衡。
鉴赏主体对于艺术作品的接受并不是机械、被动的等待过程。艺术作品一旦呈现于眼前,鉴赏主体的内心世界就不可能再安静下去,他一方面体味着由艺术形象的直觉观照所带来的美感,另一方面又在特定的心理时空内不自觉地对艺术作品进行二次创造,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审美意象。“这种新的审美意象既是对艺术形象以及艺术家审美意象的反馈、补充、发展……又是审美者原先已有的原初审美意象在当前艺术形象刺激下加以改组、再造、发展的结果,是新旧意象的复合、化合、整合。”[6]在审美意象的不断建构中,“虚静”心态内能动性因素的作用是明显的。在它的指引和控制下,鉴赏主体的创造力才能被更好地发挥出来,从而使鉴赏活动本身变得更加能动而富有生命力。
艺术鉴赏过程中主体对作品的理解和判断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虚静”心态中的动态因素在鉴赏冲动的引导下不断发生着作用,而导致鉴赏冲动产生的客观条件则是艺术作品本身“虚实相生”的审美特质。我们可以用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来加以理解。“召唤结构”认为,作品文本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启示性结构或圈式结构,其中有许多“未定点”和“意义空白”,有待读者去填充完成。反观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召唤结构”就体现为一种空白效应,“艺术中的虚实相生有两方面含义:一、表现为中国画的黑白体系、书法的疏密、诗文的含蓄蕴藉、戏剧的虚拟化等艺术本身的虚与实的结合,作品本身的虚实又导致鉴赏者心理有一个在作品虚与实的张力作用下由虚静而充实的过程;二、艺术应该是主观之虚与客观之实的结合,也就是指艺术创作的化景为情、鉴赏者在无欲无妄的状态下将艺术品的情感转化为新的艺术形象的过程”[7]。“虚静”作为一种鉴赏心态,主体的能动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调节着主观与客观、审美与现实中虚与实的距离,从而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达到和谐共鸣的状态。在具体的鉴赏过程中,鉴赏主体在“虚静”的心理状态下可以比较容易地纳入他人(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如同我们在生活中所有过的“想他人之所想”式的心灵感应经历。通过“虚静”心态的导引,审美个体可以超越有限的自我空间,从而在更广阔和自由的世界中去实践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通与交融。
综上所述,传统“虚静”理论的阐释着重于“审美观照”和“审美心胸”的静态内涵,对它的现代审视则指向“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的动态内容与深层目的。从哲学角度看,“虚静”所关注的是个体能否以无功利性的方式在心理时空中分隔出相对静止的“虚空”地带,以此为参照,人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和角度去重新认识和体悟运动着的客观世界;反观到心理学当中,“虚静”所探究的是个体如何在不同的审视方式下营造出不同的心理能量结构,从中可以催生和激发出强而有力的主体创造性,这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虚静”既涉及审美心态,也涉及审美方法论。即使在今天看来,审美观照也必须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胸为前提。“虚静”的审美态度对于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它可以使人们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在日益浮华躁进的生活中重视生命内涵的培养,从而以高远的心灵、真朴的气质、深沉的思想引导出丰富的创造源泉。对于“虚静”理论的现代审视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所要做的,是赋予其更多的时代内容与精神特质。
[1] 朱光潜.谈美书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 鲁文忠.虚静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4):91-97.
[3]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7.
[4]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9.
[5] 潘运告.宋人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12.
[6] 邱明正.审美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368.
[7] 朱立元.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562.
责任编辑:刘海宁
I01
A
1007-8444(2010)03-0382-04
2010-03-15
武克勤(1979-),女,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