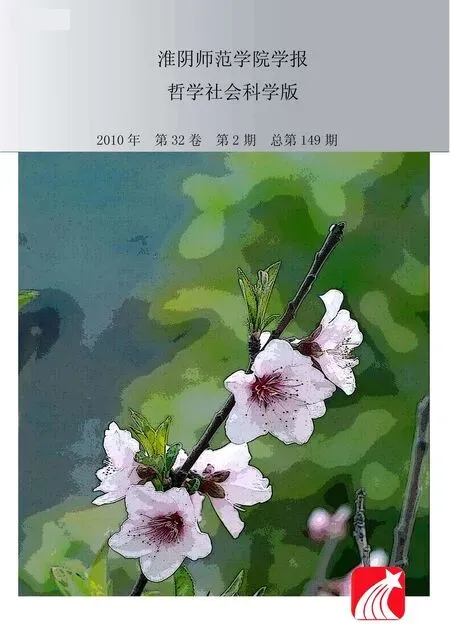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2010-04-11毛宣国
毛宣国
(中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毛宣国
(中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对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从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相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针对这一倾向,笔者认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中,必须坚持这样的理路与方法,即突破经学与文学、政治与教化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以“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并在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
汉代诗学理论;《诗经》阐释;历史语境;存在价值;合理性
一
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汉代诗学理论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基本是围绕经学释义,更准确地说,是围绕《诗经》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认。不过,如何评价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论价值,却存在着分歧。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论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声音,也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那就是:汉人功利性太强,将文学价值依附于道德政治功能下,汉人的《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是经学而非文学的,是以经学为本位而遮蔽了《诗经》的文学性,根本忽视了《诗经》的文学和审美价值。
对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这种否定性评价,早在20世纪初就突出表现出来,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就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批判了汉代的诗学理论和《诗经》学研究,在他们的眼中,汉代学者是一群腐儒,完全曲解了《诗经》的本义,把《诗经》变成道德说教的工具,从而也使汉代诗学从根本上丧失了对文学的审美认识和把握的功能。此后,这种研究思路就成为汉代《诗经》研究的基本思路,主宰着20世纪以来的《诗经》研究并从根本上影响着对汉代诗学的整体评价。闻一多先生是现代《诗经》学研究中的杰出学者,他创人类学和新训诂学研究《诗经》的新方法,注意到《诗经》研究与社会历史、宗教民俗、文化心理的广泛关系,不过,他在谈到汉代诗学时,也像“古史辨”学者那样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予以否定:
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些,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是诗……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1]
在闻一多看来,《诗经》只是一部文学作品,读《诗经》最重要的就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只有这样才能还《诗经》以本来面目。汉人偏离了《诗经》的文学本质,以非常功利的眼光看待《诗经》,所以应该予以彻底否定。闻一多先生尚且如此,一般的《诗经》研究者就更是习惯从经学与文学、道德与审美对立的立场上看待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并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比如,一部很有影响的《诗经》研究史的专著就这样看待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研究:“它不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分析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通过对《诗经》的解释和论述,附会引申儒家的教义,把一部古代的诗集,变成封建政治伦理的教科书。”[2]有的人则从汉代推演到整个南宋以前的《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研究,认为在南宋之前,它都笼罩在汉学的阴影下而意识不到《诗经》的文学价值和本体地位,从而把《诗经》研究引向歧路。比如,近几年出版的一部影响颇大的研究明代《诗经》学的著作,就这样看待汉至南宋前的《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论,认为在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从文学角度来认识《诗经》的只言片语”,但这对于《诗经》的诗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变化,牵涉到研究者心态的变化,只有研究者从认识心态转化为艺术心态时,《诗经》的文学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开始”[3]。言下之意,就是汉人以道德说教和功利的心态对待《诗经》和《诗经》学,所以,无法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还原《诗经》研究的本来面目。还有人这样概括西汉以来两千年的《诗经》阐释的诗学历史,那就是:“基本脱离《诗经》的文学性质,无论在方法上和内容上,都陷入传统经学的窠臼,受到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力支配和控制。”[4]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充分地体现在大量文学批评史和诗学史著作的写作中,比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认为:“两汉是封建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的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5]71,于是“诗的地位逐渐崇高了,诗的真义逐渐汨没了”[5]74。有的论者则用“前文学思想”的话语来概括汉人对《诗经》理解和由此所引发的诗学思想,认为汉代诗学思想“主要倾向是重功利的”,“大抵从政教角度着眼,多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较少从文学自身着想……独立的文学思想潮流似未形成”[6]。有的学者如张少康虽对汉代文学批评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它和魏晋一样,同属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期,但仍认为汉代文学批评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将文艺纳入统治阶级的教化轨道,汉代所形成“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遂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文艺发展的桎梏,使文学变成了经学的附庸”[7]。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流行“魏晋文学自觉”的理论,也是针对汉代教化文艺观的,以批判否定汉代《诗》学的文艺教化观为前提,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学正是冲破了这种教化文艺观而走向文的自觉的,李泽厚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二
对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评价所表现出来的偏失,学术界也不是没有认识和反思。比如,有的论者就认为经学的文学化和文学的经学化是中国传统《诗经》学的基本特征,不能因为从经学角度出发看待《诗经》就否定了《诗经》的文学特征[8]。也有的学者注意到汉代诗学在政治与审美、文学与经学之间的矛盾与关联。比如,胡晓明在谈到汉儒以比兴诠释《诗》时,亦认为其中含有中国文艺思想之先天痛苦,即政治与审美的矛盾张力和悖反[9];汪祚民谈到汉代《毛序》《毛传》《郑笺》这些典范的经学阐释文本时,就认为其中也包含丰富的文学阐释内容,经学与文学的阐释并非形成截然的对立[10]。
但是,从总体上说,这种声音还显得微弱,没有对传统的否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看法形成根本的挑战。在学术界占支配地位的,是对汉代诗学予以轻视或否定评价的声音。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评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在面对汉代诗学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汉代诗学是经学语境下的诗学,以《诗经》阐释为中心的汉代诗学理论建构是以经学、政治和道德教化为核心的。囿于这样的事实,再加上对汉人的诗学语境、汉代《诗经》阐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和诗学精神缺乏认同和理解,习惯于以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相对立的思维模式看待汉代诗学,很容易导致对汉代诗学的否定性评价。所以,要认识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价值,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将经学与文学、政教与审美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回到汉代《诗经》阐释的历史语境中,以中国古代诗学本有的精神和话语系统来看待汉人的诗学理论,同时,在中西诗学比较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这一观点,也可以看成是本人所确定的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路与方法。具体说来,它大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
第一,把汉代《诗经》阐释所形成的诗学理论放在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重视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在汉代诗学理论建构中的价值和意义。加达默尔说:“在精神科学里所进行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11]397我们在评价汉人对《诗经》的解释和在这一阐释中产生的诗学理论观点时,也应该坚持这一原则。要看到,汉人对《诗经》的阐发,是汉人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关系的产物,我们今天对汉人解《诗》立场和诗学观念的理解,应该注意重建这种语境,回到这种语境和关系中。“古史辨”学者认为汉人过于功利,以经学为本位而忽视了《诗经》的文学价值。这种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汉代诗学的确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倾向和经学本位意识。但是由此而导致对汉代诗学的全盘否定,认为汉代的《诗经》阐释和诗学观点的提出“愚笨到极点”,是全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完全脱离汉人诗说的历史语境和实际。西方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在谈到大部分孔子思想的解释者时说,不管他们是立足于西方传统,还是借用西方哲学范畴来论述中国传统,“其主要缺点都在于无法找出能明确表达支配中国传统的预设”[12]。这种“预设”被葛兆光先生视为一种存在于人们生活实际的世界中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它作为思想史写作的底色或基石而存在[13]。其实,不仅是思想史的写作,而且也是诗学史和《诗经》学史的写作,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某种常为少数思想家、文学家提出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识,绝不是只代表少数思想家、文学家的个人见解,而总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体现着一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民众的观念共识;而正是这种共识,构成了理论家、思想家提出理论观点、进行理论阐释的背景和依据。对汉代诗学,对《毛诗》、三家诗论这一类在汉代《诗经》阐释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诗学理论,我们也应该这样看,绝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四家诗学者的个人见解,而应该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看成是从先秦到两汉普遍存在的、代表一般民众和士人阶层的观念共喻和共识。比如,汉人极其看重《诗经》的政治功能,依今人的眼光看,背离了《诗经》的文学实际,可是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体现了某种观念的共识。这是因为,《诗经》是西周礼乐政治文化的产物,《诗经》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发挥着重要的礼仪文化和政治功能。这种功能在汉人那里被放大和强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诗经》的实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汉人从经学立场上看待《诗经》因而导致对《诗经》文学价值和文学性的否定,而在汉人那里,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却并不像今天这样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从经学立场出发,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否定《诗经》的文学性。还有一点也必须明确,那就是依据现代诗学标准看,《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解读为文学作品,从文学角度展开评判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当时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诗经》就主要作为文学文本存在,其价值和意义也主要是因为它的文学品格和审美功能而张显。同时,也不能因为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学品格,就因此判定说围绕这一阐释所建立起来的诗学理论,根本背离了《诗经》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精神。因为不同时代对文学和审美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汉代诗学理论,实际上是在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的矛盾张力中展开的。以现代诗学标准,特别是受到西方现代诗学影响所建立起来的以审美和文学性研究为核心的纯诗学理论的标准来看,汉代诗学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性和以诗为史、以诗为经的特色,的确是对《诗经》文学价值的一种翳蔽;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体现了一种文学和诗学话语的共识,后世诗学理论,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
第二,从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李春青在他的近著《诗与意识形态》中谈到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时认为,我们为什么研究古代诗学?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研究者看不到古代诗学研究对现代生活的意义,就认同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研究就是求真,于是揭示古代诗学话语中可以验证的内容就构成这种研究惟一的合法性依据。这种研究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是也有明显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阐释的空间。为此,他提出“对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是古代诗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的观点,认为“古代文论话语无疑是一套知识话语系统,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意义和价值系统,具有不断被阐释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对知识系统的研究可以采取实证性方法以揭示其客观性,对意义系统则只能采取现代阐释学的方法,以达成某种‘视界融合’,构成‘效果历史’”[14]。我是非常赞成这种观点的。长期以来,在《诗经》阐释的研究中,一种“求真”、视《诗经》研究就是揭示《诗经》真相、找到可以验证的事实和依据、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的做法一直非常强势。也正是因为此,汉儒那种带有主观意图的道德化解《诗》倾向就颇遭诟病,为人们所否定。顾颉刚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时说:
我写这篇文字的动机,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激,觉得这种的附会委实要不得。后来看到宋儒、清儒的《诗》学,觉得里边也有危险。我久想做一篇文字,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和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的“幸运”。[15]124
显然,在顾颉刚看来,从先秦两汉,特别是从汉儒的附会开始,《诗经》研究的真相一直被隐匿着,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15]124,还原《诗经》的真相,还原《诗经》作为文学的本来面目。在《重刻诗疑序》中,顾颉刚对汉代以来《诗经》学的历史作了回顾,将它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代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只有伦理观念没有历史观念;第二阶段是宋代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既有伦理又有历史观念;第三个阶段是他和“古史辨”学者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则是把历史观念和伦理观念分开。他说:“我们读《诗经》时并不希望自己在这部古书上增进道德,而只想在这本古书里增进自己的历史知识。”[16]在顾颉刚眼中,《诗经》只是一本历史上存在的文学书籍,阅读和研究《诗经》的目的,也就在于增进关于文学的历史知识而非把它作为道德经典作价值评判。我们当然不否定顾颉刚所提倡的这种研究的合理性。但把这种研究当作《诗经》研究的唯一途径,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具有合法性,才是“正门”,却是违反《诗经》研究实际的。在“古史辨”学者眼中,《诗经》研究就是求真,就是把《诗经》作为一套客观存在的知识话语系统,作客观知识的研究和话语还原。而在我们看来,《诗经》更应该作为一个价值和意义的系统进入人们的视野。像《诗经》这样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长期占有主流地位,进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核心,为人们所关注、所诠释和解读,主要也不在于它是作为一套知识话语存在,而在于它是作为一套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存在。而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诗经》,重视历史上《诗经》的解读,也在于它对于今人来说仍是一种价值关怀和意义找寻的对象,仍能满足我们的价值和意义需求。从对《诗经》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作为中国礼义文化之源,作为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体现,作为文学、政治、道德、宗教、历史的经典,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仍具有启示意义。
只要我们回顾历史上《诗经》的阐释和研究,回顾历史上任何《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理论的形成,就不难发现,仅仅把《诗经》作为关于文学和历史的知识话语,而否定它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意义,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古代的《诗经》阐释是一种知识话语系统,但它更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国古代《诗经》阐释以经学为本位,以经典化和道德化的阐释为特征,这当然是为找寻古人的意义和价值观念。而“古史辨”学者要求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以科学实证精神来看待《诗经》,以对历史事实的精确考证来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将道德立场彻底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选择和意义评判?在20世纪《诗经》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影响极大,那就是将《诗经》看成是以民歌为主体的诗歌创作,认为《诗经》实际上是一部反映周代民众(包括贵族和平民)内心情感的文学作品,认为《诗经》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风诗”——它来自于民间歌谣文体。这种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明确提出①,20世纪50—60年代经余冠英等人提倡后更成为《诗经》研究的主流观点,今天也不例外。而在古代,人们则不这样看,而是更看重《雅》、《颂》一类作品,比如,孟子、荀子引《诗》用《诗》的重点是《雅》《颂》,汉代的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谈到如何读《诗经》时,也认为应以雅颂为先,从雅、颂开始,王夫之解《诗》,重视的也是《雅》《颂》,这从他的《诗广传》等著作中就可以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显然与不同时代人们对《诗经》的价值评判和需求相关。在古人看来,《诗经》之所以重要,首先并不在于它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在于它处于政治礼教和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有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以这种观点看待《诗经》,“雅”、“颂”超越“风诗”的地位就不难理解。而把《诗经》看成以民歌为主体的艺术创造,更重视风诗的人,显然也是以今人的文学和价值观念来评判《诗经》,是今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又如,从《诗经》“风、雅、颂”编排顺序来看,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和人们价值观念对《诗经》意义生成的影响和作用。今天看到的《诗经》与最初的《诗经》在编排次序上是不一样的,最初的《诗经》是颂、雅、风的编排次序,而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却是按照“风、雅、颂”的次序排列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编排次序的不同,对这一点,钱穆早就有所揭示,他说:“孔氏《正义》亦言之,曰: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又曰: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其说甚是。惟今诗之编制,先风、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颂,则应属后起。若以诗之制作言,其次第正当与今之编制相反;当先颂、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风,始有当于《诗三百》逐次创作之顺序。”[17]钱穆这一说法是符合《诗经》发展实际的,这从马茂源先生整理的《上博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编排次序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显然与后人对《诗经》的价值评判与选择密切相关。因为现今看到的《诗经》版本是秦汉时代重新编定过的,而这一时期的人们更重视《诗》的政治讽谏与教化功能,所以那些赞美祖先之功德,“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的“颂”诗,不如那些“缘政而作”,具有“怨刺”和批判精神的风雅之诗,更受到人们的推重,于是就发生了《诗经》编排次序的这种改变。
承认《诗经》阐释既作为知识话语又作为意义和价值系统存在,实际上也意味着承认任何《诗经》的阐释都不能作纯客观的知识论的还原,都必然带有主观阐释的特点,承认历史上各种解《诗》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否定汉儒《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人认为汉儒的最大毛病就是过于主观化,这当然是揭露了汉人说《诗》的弊端,切中了汉人说《诗》的要害。因为汉儒说《诗》,在主观化道路上的确走得很远,他们以“美刺”说为核心,将《诗经》中几乎每一篇诗都与一定的史实联系起来,说是美某人、刺某人,这当然与《诗经》的实际情况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经》阐释可以不带有阐释者的主观观念和意图。按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11]380,都是带有理解者前见的理解,理解即是“纳入到他整个的自我理解中”,没有所谓“完善理解”,只有“以不同方式的理解”[11]381。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承认主观化对于阐释活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阐释活动要做到的不是彻底消除这种主观化,而是让这种主观前见如何与阐释对象的视阈融合。就中国古代《诗经》阐释来说,其实不仅是汉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对《诗经》的阐释,都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特征。这不仅是理解活动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也是为《诗经》这样的阐释对象的特征所决定的。虽然,今天有许多人都申言要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要找到符合《诗经》文本阐释的事实和依据,而事实上这样的事实和根据常常是打上了阐释者自身的主观意愿和意图的。我们在《诗经》阐释史上所看到的现象是,对《诗经》的阐释常常并不来自于《诗经》本身,而是来自《诗经》文本之外的信息,来自于历史上《诗经》阐释所形成的传统和批评观念的支持。我很同意一位《诗经》论者的观点:“《诗经》的解释,一直是依赖于历史文化方面的信息以及批评者的诗歌观念来完成的。所以,任何一种《诗经》解释系统都是相对性的。我们应该看到它们的相对性,尤其是对于近现代学者普遍诋疑的《诗序》与《毛传》,我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否定,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以采取存疑的态度为好。”[18]同时,我还想补充说一点,对《毛传》和《诗序》这样的作品,若从价值和意义的层面看,其态度还不仅仅是存疑,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活的精神对象,予以充分的阐发,以找出它对当代人的启示和对当代诗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第三,以同情理解的态度看待汉代的《诗经》文本研究,深入挖掘汉代《诗经》阐释中的文本意蕴和诗学内涵。今天,许多人都在谈论找回《诗经》文本的本义,而且认为只有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看才算找回《诗经》本义。对这样的看法,需要认真辨析。我们当然不否认《诗经》阐释中有一个本义问题,但是,何谓本义?能否将《诗经》的本义就理解为文学本义,《诗经》除文学本义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本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诗经》文本的意义,或者说《诗经》的本义,并非只是文学本义,它是多元的,政治、历史、文化、文学的意义都包含于其间。更重要的是,《诗经》文本意义的确定,离不开《诗经》解读视野,离不开阐释者的主体视野。吕思勉先生说:“《诗》无本义。太师采《诗》而为乐,则只有太师采之之意;孔子删《诗》而为经,则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盖《诗》固只有诵义也。”[19]又言:“《诗》有诵义,无作义。”[20]吕思勉先生这一看法,我并不赞成。因为《诗》“本义”是客观存在的。诗之“本义”,在中国古代诗论家那里,一般指向作品和作诗人之义。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曰:“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之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21]他这里所说的“正义”,就与“本义”同,是指作诗者之义,而旁义和断章之义则超出作诗者之义,是在《诗》的应用和阐释中建立起来的意义。中国古代诗学是重视“本义”问题的,从班固提出“诗本义”,到欧阳修著有《诗本义》一书明确和系统地阐发《诗》的本义问题,“本义”就成为中国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即使如此,吕先生的《诗》只有“诵义”而非“作义”之说,仍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因为《诗经》本义虽就作品和作诗人之义而发,而要真正接近和理解它,却又是无法脱离阐释者而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诗经》阐释学传统基础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虞东学诗》条的“案语”说:“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辩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可通也。”[22]章太炎在谈到《诗经》阐释时说:“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完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这些说法,均看到了《诗经》本义的理解离不开阐释者的解读。加达默尔说:“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11]380《诗经》文本意义的解读正是如此,它已远远超出作者的意图,它是在解释者观念和意图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超出,并不意味着脱离古人实际,背离《诗经》的原意和精神。陈寅恪在谈到如何理解古人学说思想时曾提出著名的“同情了解”之方法[23]。所谓“同情了解”,就是既承认古人学说真相发现之不易,承认理解应该进入古人创作的特定环境,体察古人写作之心理,又强调以现代人的思维、心胸来融贯对历史的理解,做到今人与古人的视阈融合和心灵的沟通。这些方法和原则,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精神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人的解《诗》实践中也不难发现。比如,欧阳修在他的《诗本义》中就提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也。”[24]所谓“古今人情一也”,“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就是一种“同情了解”的解《诗》方法,它亦是承认人的心灵情感的古今相通,《诗》的本义理解亦是在今人与古人、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相通中完成的。这一方法也是我们今天评价和看待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所应坚持的原则和方法。
以这种方法看待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不难发现,人们经常诟病和批判的汉代诗学理论观念,如对《诗》作政治、道德化的解读和历史化的解读,重《诗》之美刺讽喻功能,将《诗》之“比兴”看成“美刺”之别名等,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是具有重要诗学理论价值的。汉人以政治化、道德化立场解《诗》,看似很偏狭,但只要注意到《诗经》乃周代道德和政治制度的产物,与周公制礼作乐进程密切相关,早在先秦就形成了以“礼”释《诗》,将《诗》与政治、道德教化紧密联系起来的诗学传统,就不难理解。而且,诗教因情而生,不脱离情性,这是从《诗经》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孔门诗教传统,汉儒解《诗》,也不例外。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否定汉人这一立场,也不难理解汉人以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眼光看待《诗》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汉人以《诗》为史,常常将《诗经》作为历史文本来看待,也并不意味就根本脱离《诗经》文本解读的实际。《诗经》中许多篇目,特别是《雅》《颂》中的许多篇目,可以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遗篇看待,这也是学术界确认了的事实。而且,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并不始于汉人,早在先秦的《左传》和《孟子》的解《诗》中就非常明显。所以,汉人的以《诗》为史,对《诗经》做历史化的解读,并非都出于主观杜撰,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和诗学依据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解释所存在的主观附会成分,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解释方法,由于充分注意到《诗》与时代、政治、作者的关系,注意到“诗”与“史”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再如,汉人以美刺解《诗》,将《诗》看成是美刺讽谏的工具,这也颇遭后人的诟病与批判。我们当然应看到这一解《诗》方法的缺陷和牵强附会,因为《诗》乃人们兴发感动的产物,并非都是“颂美”“刺恶”之作,并不能都作道德化、寓意化的深解。但是,若回到先秦至汉的诗说语境,亦不难发现,汉儒以美刺讽谕言《诗》,将《诗》之“比兴”变成“美刺”的别名,并非都出于汉人的道德比附和穿凿附会,而是保留先秦至汉人们的观念共喻,有一种“引譬连类”的思维方式之自觉。而且,它还反映出汉人特有的一种人文和政治立场,那就是在“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郑玄《六艺论·诗论》)的大一统专制的时代,诗人“以颂其美,而讥其过”(郑玄《六艺论·诗论》),实是保留一份对现实的发言与批判权利,一份参与和干预现实政治的热情。汉人说《诗》,还喜言“灾异”和“天人感应”,将《诗》看成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的产物,认为《诗》具有“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汉书·匡衡传》)的神奇之功用。对汉人这一解《诗》立场,有不少人也不能理解,认为这是汉代谶纬迷信盛行、对《诗》任意比附和曲解的结果。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回到汉儒的《诗》说语境中,以“同情理解”的态度观照之,亦不难发现它与以“美刺”说《诗》的精神是一致的。它将《诗》与神秘的天人感应论联系起来,将《诗》灾异的发生看成是天之谴告,对《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固然是一种损害,但是,强调“诗者,天地之心”(《诗纬·含神雾》),“以《诗》为天下法,何谓不法哉”(《春秋繁露·祭义》),将《诗》之道提升到天道的高度,认为《诗》可以承担起代天而言,以天命抑止王权的政治批判角色,这无疑又扩充了《诗》的使命和功能,使《诗》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参与和干预现实的精神。
明人钟惺曾提出“诗活物”说。他说:“《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25]391又曰:“且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以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诗、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之、传之者乎?既引之、赋之、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其何故也?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25]392所谓“活物”就是承认《诗》的解释可以相对自由灵活,就是承认《诗》之本义是在历史的解读中形成的,并不因为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而变得晦暗不明,相反是“固已明矣”,“固已行矣”。也就是说,随着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其义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些阐释方法和原则的确立,对我们把握《诗经》文本意义和诗学理论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诗经》历史去今几千年,阐释的著作堆积如山,我们如果没有同情理解之心胸,不能将古人与今人的情感、认识、视野很好地沟通和融合起来,是很难把握《诗经》文本意义的,也很难说明古人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诗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第四,从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深入认识和发掘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的理论价值。不少人谈到汉代《诗经》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时,多习惯从《诗经》本身,从《诗》学而不是诗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比如,有一位论者谈到汉代《诗经》研究时就这样认为:“在两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诗经》与一般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因而关于《诗经》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经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与欣赏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之类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一种不同于经学的观念。经学化的《诗经》同非经学的诗歌创作与欣赏实践已出现分立之势……《诗经》与《诗经》之后的亡佚诗歌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前者成为政治或伦理教化的附庸,后者则变成了个人的自发行为;由此而产生了诗歌观念的差异: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者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而《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观念所体现的却是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诗经之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之间出现了差异。”[26]这一论者的基本立场是将经学化的诗学理论与“体现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的诗学理论区分开来,以建立一种纯诗学、纯文学的理论和观念,所以把汉代《诗经》阐释只看成是《诗经》之学而非诗学的研究。我们不否认《诗经》阐释有《诗经》之学与诗学的差异,也不否认汉代《诗经》阐释是在经学思维模式影响下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代《诗经》阐释的意义就只局限在《诗经》之学的范围,就只属于经学而非诗学。事实上,汉代《诗经》阐释一直在两个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一是它作为《诗经》之学,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诗经》汉学对后世《诗经》学的影响,它不仅确定了以“经”解《诗》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诗经》文字训诂、流派传授、史料勘正、《诗》旨解释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对这一点,学术界已有普遍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它在诗学史上的意义,对这一点,学术界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事实上,汉代《诗经》阐释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更为重大。朱光潜和宗白华等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思想体系形成时,都特别强调“诗”,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诗》学阐释系统的价值和意义。朱光潜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着《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27],宗白华也认为“《诗三百》是孔子、孟子、荀子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依据,它成了儒家的‘诗教’,也是中国过去两千年来文艺思想的主流”[28]。而汉代的诗学理论与实践,正印证了《诗经》之学在中国诗学理论史上的重要性。我非常赞成学术界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中国诗学中起支撑作用的,是先秦两汉确立的那些古老的理论和观念。在这种理论和观念下,潜含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人的基本诗学态度和运思方式。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诗学理论,在先秦两汉就基本建构形成,而汉代诗学理论直接承继先秦,可以看成是先秦儒家诗学理论的一个总结。美国学者迈纳曾从跨文化研究的立场提出“原创”(orignative)诗学概念。他认为这种诗学只属于某一种文化,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找不到,而《诗大序》正是这种诗学的奠基作品,“中国的诗学是在《诗大序》的基础上产生的”[29]。把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基础完全归结为《诗大序》,并非是一个准确的看法,但是说中国古代诗学许多重要命题和观念,如“诗言志”、诗言“情性”、“比兴”、“感物”、“美刺讽喻”、“诗无达诂”,等等,都是在汉代诗学文献,特别是像《诗大序》这样具有原创精神的诗学文献中形成和确立的,则是毫无疑问的。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还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致思和言说方式如“依经立义”等的形成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理解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不仅是理解汉代诗学,也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
不仅如此,从中西诗学比较的大视野看,更不难发现汉代《诗经》阐释在中国诗学史上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汉代是中国诗学理论形成和奠定的重要时期,《诗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原典和诗学原典,以《诗经》阐释为中心的汉代诗学理论的研究,必然会引发对中西诗学理论种种有价值的比较与探讨。比如,中国诗学理论生成的深层动力和机制是什么?它与西方诗学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亦可以从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研究中受到启示。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谈到孔子文学思想时说,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往往不在孔子对文学自身所表达的见解,而在于所蕴涵的儒家思想对更广泛问题的关注[30]17;中国从孔子到《诗大序》对文学问题的关注,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中国诗学理论(如《诗大序》)试图告诉人们的是“诗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诗是什么”,中国诗学理论不像西方诗学那样就“诗”的制作来讨论“诗”是什么,而是关注人的动机、目的、需求在诗学理论中的作用,中国诗学就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30]18。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示。它说明,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较之西方诗学理论来说,依赖于一个比文学、诗学更大的解释学传统,一个更大的文化关联域,以《诗经》阐释为中心的汉代诗学理论,把《诗经》主要设定为经学而非文学文本,这一立场虽然超出了《诗经》理解的文学范围,却没有超越中国诗学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国诗学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经学文本和经典阐发的支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和文化传统形成与经典阐释无关。实际上,由经典和经典阐释所构成的解释现象,也是世界许多文明民族所共有的现象。在西方,其诗学理论的建构同样不可能排斥经典的阐释,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在西方,没有像《诗经》这样的取得经学地位的经典文本的存在,也没有发展成为像汉代那样以《诗经》阐释为中心的诗学解释系统和在后世诗学中的权威地位。在西方诗学中,我们听到的不是像在中国常常听到的孔子是否删诗,《诗序》是否出于孔子嫡传弟子之手那样维护《诗》的经典地位和权威的言论,而是柏拉图对诗的指责,锡德尼、雪莱“为诗一辩”的声音。所以,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比较中西诗学的差异,是有特殊意义的。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的这一特点,如果放在当代诗学理论背景下,与西方当代诗学中的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形成比较和参照,也会为我们提供启示。今天许多人都习惯于把《诗经》看成是一部只关乎文学自身,只关乎审美的作品,并因为汉儒主要是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诗经》进行解读,就认为它根本背离了《诗经》的文学实际。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历史上的文学观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不存在着某种一成不变的文学本质。伊格尔顿说,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它“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31]。文学是人们建构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背景而存在。我们不可能用“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审美高于功利”这些产生于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要求古人。如果从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中,从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去考察文学,未必就能说汉代对文学的理解,将文学与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的观念,就一定低于今天的强调文学本质是审美、审美高于功利的观念。德里达在《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一文中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32]文学从它最基础的意义上说,应该被看成是某种社会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法则的体现,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不仅要在文学的范围中进行,在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中展开,更应该从文学与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进行。这既是西方当代诗学中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对文学的基本立场,也是我们从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那里可以得到和解读的东西。
注 释:
① “《诗》出于民间”说滥觞于汉代,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有“使之民间求诗”说,王充亦有“诗作民间”说。宋代郑樵有“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之说,朱熹有“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的说法,都明确肯定《国风》出自民间。清代崔述、方玉润等人更是强调风诗出自民间。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成为封建时代《诗经》研究的主导观点。将《诗》看成是以民歌为主体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肯定《国风》为民间歌谣的观点的形成并占主体地位,是从20世纪的古史辨学者开始的。胡适、顾颉刚、郑振铎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有的学者说得更明确:“《诗经》为当时的民间文学,尤以《国风》一类实在是当时民间恋歌。”(张履珍:《谁俟于城隅》,《古史辨》第三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冠英在其《诗经选·前言》中更加肯定了《诗》为民歌的观点,他认为“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这一观点也为五六十年代的《诗经》研究定下了一个基调,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诗经》研究的主导性观点。对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质疑,如朱东润、钱穆等人,但并没有成为主导性观点。
[1] 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16.
[2]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72.
[3]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71.
[4] 董运庭.悉信亦非,不信亦非[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7(3).
[5]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5.
[7]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4.
[8] 谭德兴.什么是《诗经》的文学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2003(3).
[9] 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40.
[10]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第三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2] 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4.
[1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3.
[14]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
[15]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6] 顾颉刚.重刻诗疑序[M]//古史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 钱穆.读诗经[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00.
[18] 钱志熙.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J].北京大学学报,2005(2).
[19] 吕思勉.经子解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0.
[20] 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55.
[21]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1954:1.
[2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97.
[23]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 [宋]欧阳修.诗本义.[M]//[清]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第7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241
[25] 隐秀轩集:卷二三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6] 高小康.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27] 朱光潜.中国古代美学简介[M]//蒋孔阳.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6.
[28] 宗白华全集: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82.
[29] 迈纳.比较诗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3.
[30]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1]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5.
[32] 德里达.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
“现当代学人研究”征稿启事
本栏目以20世纪人文科学著名学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道路、治学方法等进行回顾与总结,但求客观、公正、严谨。来稿既可是一组文章,对研究对象作较为全面的评述,也可是单篇文章,对研究对象作重点评析。文章篇幅请控制在10 000字以内,符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并提供打印件及电子文档(E-mail:hysyqhy@163.com)。
本 刊 编 辑 部
I207.209
A
1007-8444(2010)02-0236-10
2009-11-20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09BZW004)。
毛宣国(1956-),男,湖北宣恩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