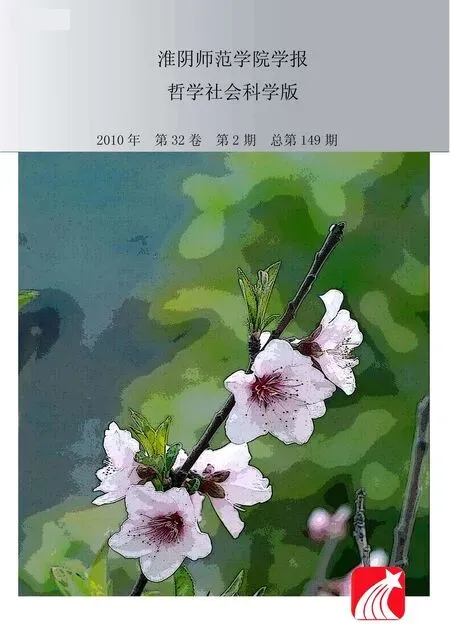从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的三教圆融思想
2010-04-11刘永海
刘永海, 许 伟
(1.唐山师范学院 政史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2.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从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的三教圆融思想
刘永海1, 许 伟2
(1.唐山师范学院 政史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2.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元代道教史籍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尤以三教圆融思想最为突出。在儒家方面,主要吸收其忠孝、诚等思想;在佛教方面,主要融摄其普度众生思想、因果报应学说、心性理论和禁欲主义思想。
元代;道教史籍;儒家;佛教;融合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教(家)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总的趋势是在一种相互矛盾,而又不断渗透、融合中发展着的。在此过程中,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作为一种思潮,“合一”与“融合”基本上是三教人士的共同主张,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大体是站在本教(家)的立场上,吸取他教与本教相一致的思想。道教也不例外。道教三教融合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进程在道经中有着清晰的记述。元代道教史籍所反映的三教圆融思想尤其丰富,值得认真研究。
一、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儒家思想包含许多范畴,忠孝、诚敬等思想则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也分布在元代道教史籍之中,充分显示出道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及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一)吸收儒家忠孝思想,丰富道教理论。
儒家以忠孝为核心,而吸收儒家这一思想最为显著的道派当属净明道。《净明忠孝全书》是反映净明道思想的重要典籍,其中吸收了很多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家们的思想,而对忠孝思想的吸纳则是《净明忠孝全书》的鲜明特色。所谓“忠孝”,本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伦理规范,指对君主的忠诚及对父母的孝顺。事实上,早期净明信仰的核心是“孝”,其崇拜者皆推崇祖师许逊的“孝悌”之行,而尚未强调其“忠”。托名胡惠超的《净明大道说》已经“忠孝”并提:“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633表明净明派教义得到充实,且信仰中心向“忠”偏移。何真公在南宋打出了“净明忠孝”旗号,并正式创立了净明忠孝道。为何该教以“忠孝”为名?元代复兴净明道的刘玉称:“别无他说……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是真践实履。”[1]635忠孝虽是儒家习见的思想,世儒却常常停留在口头,因此,净明道从宗教实践的角度强调这一思想,以正心诚意教导人们去执行三纲五常。
净明道强调“以忠孝为本”[1]630,意思是说忠孝为修道的根本,可以说是净明教义的大纲。为何要以忠孝为本?因为忠孝是为“人道”的根本,修好了人道,才可以修仙道。为了说明忠孝的重要性,刘玉对其神圣意义大力宣扬:“入吾忠孝大道者,皆当祝国寿、报君恩为第一事,次愿雨旸顺序、年谷丰登、普天率土同庆升平。”[1]640刘玉对理学诸儒十分推崇,其忠孝思想也深受儒家理学影响。因而《净明忠孝全书》中充斥着理学术语。如其云:“净明大教,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1]647,此处的“忠孝”、“去欲正心”、“净明”等词,都有理学色彩。刘玉还用“良知”、“天理”说来阐释忠孝的含义:“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1]647在净明教义中,信教者不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搞符箓斋醮,只需一心一意地去修持忠孝大道即可。这种不重视传统道教的修持内容,而主修儒家伦理道德的派别在道教史上独一无二。
在净明道看来,以忠孝为教义将会对社会大有裨益。何真公曾说:“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跻于仁寿,措四海而归于大平,使君上安而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为将,举三军之众而归于不战以屈人之兵,则吾之兵常胜之兵也。”以忠孝教义教化世人,也会收到儒家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吾之忠,教不忠之人,尽变为忠;以吾之孝,教不孝之人,尽变为孝,其功可胜计哉!”[1]646使不忠者为忠,不孝者为孝,这是儒家都梦寐以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而净明道却可以做到,难怪儒家学者每谈起净明道必大加赞赏了。张珪在《净明忠孝全书·序》中称赞:“净明之道必本于忠孝。匪忠无君,匪孝无亲,八百之仙,率是道矣。”又说:“非忠非孝,人且不可为,况于仙乎?维孝维忠,仙犹可以为,况于人乎?”对净明道之忠孝说十分推崇。赵世廷也是赞不绝口,说净明道以忠孝为名,含义深远:“设教名义,得无类吾儒明明德、修天爵之谓欤!”认为其提倡忠孝是抓住了纲常伦理的根本:“夫臣职忠、子职孝,万古良知有不可泯者……纲三纲、常五常,其惟忠孝乎!”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忠孝之道即是古代圣哲贤人之道,而净明道已得圣贤真谛:“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知大道至德之要,其在兹乎?”滕宾更是说始于许逊的忠孝道派“其功不在禹下”,净明道的忠孝说为“民彝世教之大纲大领”。推而行之,“上以续都仙忠孝之传,下以达天下后世,莫不为忠臣孝子”[1]620-622。
净明道的忠孝说教与儒学的忠孝伦理,在忠君及扶植纲常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毕竟是道教的一个派别,这就决定了其与儒家的忠孝主张有不同之处。郭武先生在其论著中指出:“元代净明道所言之‘忠孝’有着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为相当于儒家‘忠孝’本义上的社会伦理规范,确属‘人道’之范畴;二则是作为一种可与神灵沟通的、超世俗的宗教实践,实属‘仙道’之范围”[2]251-252。此说纠正了以往学界对“忠孝”一词的片面认识,抓住了“忠孝”作为宗教教旨的真实含义。
与《净明忠孝全书》侧重从教理教义上直接宣讲忠孝思想不同,《甘水仙源录》等全真教史籍则是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对全真道士行迹的记载中,因此更为直观、更为生动,也更有说服力。元代道教史籍揭示的全真道忠孝思想主要侧重于“孝”的一面。王嚞初接道徒,令其必读的经典就有《孝经》:“凡接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3]725-726全真弟子多有孝行,刘处玄、孟志源、李志源、曹瑱、周全道、李冲道、陶彦明、吕道安等人,皆以孝闻。丘处机对孝道极为重视,在给成吉思汗讲道时还谈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希望其改变国俗,使人知道“孝养父母”[4]493。道教本不讲出家修行,全真道借鉴佛教教制与戒律,建立了道士出家制度。出家与奉行孝道当然会构成矛盾,为此,全真教采取了一些补救办法,如允许道士侍亲、省亲即是其中的一种。刘处玄出家后,曾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回老家“往拜母氏,相见甚欢”[5]358。贞祐元年(1213),孟志源家人被兵乱荡散,其昆弟不知去向,家中二老无人奉养,孟志源“扶二亲就养于己所居,致孝养之力三载”。后来兄弟还乡,志源也经常回家省亲,“诚敬之礼未尝缺”[3]771。
在师徒之间,王嚞创造性地提出了“物外亲眷”的概念,他劝弟子“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人间假合尸”,“尽知常与道为邻,搜得玄玄便结亲”[5]349-350,实际上把世俗社会的“孝”道巧妙地转移到了教内。王嚞以后,其弟子恪守师训,大力宣扬师恩重于父母恩,在教内形成了尊师重道的良好氛围。所以在元代道教史籍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述:全真弟子为其师数年扫洒劳役,毫无怨言;跟随其师云游讲道,任劳任怨;为师守丧、会葬、迁葬,情同父子;请名臣硕儒为师撰写碑铭墓志,不辞劳苦。所以出家修行制度并未影响全真道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全真重“孝”,也含有“忠”的成分,晚清学者陈铭珪评论全真教“孝”的思想时说,重阳之学虽奉老子为依归,“而其教则以《孝经》称首。《孝经》言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忠孝本一贯之也”[6]128。显然,全真教对孝的重视,在客观上也可以培养教徒忠君的思想。
《梓潼帝君化书》以自传的口吻叙文昌帝君历世显化事迹,吸收了不少包括忠孝在内的儒家思想。其序文云:“延祐三年(1316),中书因太常定议……录予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7]293可见梓潼帝君是带有宣扬忠孝思想性质的神灵。该书通过宗教故事的形式对忠孝思想极力阐发。如“宁亲”条云,文昌帝君之母染恶疾,疽发于背后。帝君为母吮疽,出大脓血。后又自剔股肉,烹而供之。[7]295此处,《梓潼帝君化书》移植世俗社会“吮疽”及“自剔股肉以奉父母”等传说,宣传忠孝思想。其他如“尽忠”条云帝君多次冒死谏君,“忠显”条云其为国效忠,“刑赏”条云有孝子吴宜肩尝为父疾刺血写佛经卷,“训逆”、“诛悖”条云其对不孝者进行惩罚,等等。其客观效果比单纯说教要明显得多。
《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为唐、五代、宋、元时期有关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迹之汇编。采访真君为庐山之神,或称九天使者、庐山使者等,为监御万灵之贵神,巡查三界、赏善罚恶之总司。其中也吸收了许多忠孝思想,如其强调为人臣子者,应该“尽事君之忠,事亲之孝”[8]694。“建炎退张遇寇”、“开禧诛逆曦事”两条,通过采访真君帮助政府剿灭叛乱,宣扬了忠君报国的思想。“文孝子取肝救父”宣讲的则是孝道思想:江州文彪笃学至孝,“元丰七年(1085)父病垂死,彪诣采访殿祷告。归家剖腹取肝为剂二十四粒,杂他药进之,父病即愈”。又,“乾道五年(1170),彪之兄子解亦刲股以愈母疾。时司马知白为二人作《文孝子传》”。由此可见,元代道教史籍中,有关忠孝思想的内容很多。道教汲取了本属于儒家的忠孝思想并加以消化,从而充实了本教的理论。
(二)对“诚”的思想的吸收和借鉴。
“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从辞源上来看,“诚”字在春秋时期已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作为范畴而言,由《中庸》最先提出,在孟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深化。唐宋儒者李翺、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对其作过更深入的阐释。但儒家之“诚”,仅限于道德层面的构筑,而缺乏制度化建设。道教融合儒家“诚”的思想,纳入自己的教义之中,强化了其约束功能。早在三张创五斗米道教时,已把“诚信不欺诈”写入科戒。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一书始终把诚心立志皈依神仙道教,当作长生成仙的前提。唐代司马承祯《坐忘论》论及修道步骤,首推“敬信”,其云:“信道之心不足,乃有不信之祸及之,何道之可望乎?”又云:“修道之要,敬仰尊重,加之勤行,得道必矣。”[9]892也是在说诚敬修道,才可得道。元代道教史籍也宣扬“诚”的思想,而且较之以往更加重视“诚”在宗教实践上的意义,因之更有研究价值。
《净明忠孝全书》对“诚”格外重视,刘玉称:“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1]635“净明”只是“正心诚意”,意味着净明道将儒家的内心道德修养引进了自己的修道实践和终极理想。“正心诚意”才能“真忠真孝”以扶植纲常,才能达到无私欲、心澄明之理想境界。赵世廷引用先儒之论云:“凡一意弗诚则非忠,一念不敬则非孝,由存诚持敬为入道之门”,认为净明道以诚“导民忠孝,有脗乎大中至正之道”[1]620。黄元吉初收徐慧为徒时,令其读《净明忠孝(全)书》,后数日问其心得,徐慧以“万法为空,一诚为实”作答,黄则“首肯之良久”,并谓之曰:“子资质颇近道,当宏吾教。”[1]622徐慧独以此句赢得了黄的赞赏,是因为其把握住了净明道学说的真谛——外事外物的形态不过是一种不值得执著的假象,重要的是“诚”的态度。为《净明忠孝全书》作序的彭埜对“万法皆空,一诚为实”的说法非常推崇,他说:“斯言也,是真能体认都仙之旨以为教矣。”又云:“抑岂特为都仙之旨,正吾夫子之旨也,亦尧舜以来精一执中之旨也。”[1]622都仙即许逊,彭埜认为“诚”最能体现净明教旨,这一思想是许逊、孔夫子,乃至尧舜思想的精华。
当代学者吕锡琛指出,刘玉将“诚”这一儒家所强调的个体道德作为行持道教方术的基础,认为一切斋醮科仪均可简略,只要行法者有诚意。为了消除人们过于迷信符箓、科法的弊端,他甚至否定法术,认为“万法皆空,一诚惟实”。这样,“道德的功能就不仅限于精神的领域,而且对道教方术祈福消灾等功能性活动具有关键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提高道徒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持恒性是十分有益的”[10]。吕说极是,传统道法多讲究画符念咒的形式,而刘玉则重“心法”,其云:“凡我法子臻精真之极者,当于未举笔以先体究,一念才动,便属后天。盖天人相与靡间,一息至诚,所感知如矢中的。”又云:“科法中建斋行道,只是积诚,以期醮祭之时天人应答。”[1]646刘玉将道法都转向心中的至诚一念,而不借助于外在的符箓科仪,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变革。不过,刘玉并不完全否定科仪、符法,只是本着“简而不繁”[1]630的原则革新其内容,而突出“诚”的作用罢了。
从元代道教史籍可以看出,全真道十分重视“诚”的作用。著名全真道士张好古评价说:“全真之道,一言可以尽之曰:诚而已。诚者,实之谓也。”他还说:“历观重阳祖师以下诸仙真,或立观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积功累行而令名无穷,非诚实无妄,其孰能与于此乎?”[3]791元代著名学者王奂评论全真道“其要自正心诚意始”[3]807。在全真教看来,“诚”是一种修持方法,全真道士李道纯云:“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欲全其气,先要心清静;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心身合而返虚也。”[11]502其中,“意诚”是“三元至要”之一,是学神仙之法的必要环节,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佚名撰《重阳成道宫记》指出,重阳祖师以下,得其传者,一动一静,皆“诚而已。诚者,心斋也,古之人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天地之神不违者,其得所应之枢乎?”[12]712-713将“诚”视为王嚞之真传,是“应天地之神”的修道方法。全真道士特别重视“诚”在宗教实践中的作用。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全真高道王志谨经镇市,应帅曹德禄邀作黄箓大斋,远近会者不下数千,其井仅供二三十人。德禄忧之,请于师(王志谨)。师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静席覆之。历一昼夜启,其泉汹涌,用之不竭。四方传诵,师不以为异,曰:“无他,彼以诚告,我以诚应。诚意交孚,天地可通,况其余乎?”[3]756王志谨祭神的方式虽然很简单,却能感召神灵,主要是“诚”的作用。可见,关于全真教以诚立教、传教、修道的思想,已成为教内外人士之共识。
对修道者而言,“诚”之与否,是有无造化、能否得道的关键。因此,仙真高道在度化弟子时常以“诚”试其心,惟其通过各种各样的关口与磨难,才会向其秘授道要乃至传授法印。《仙鉴》记载,魏伯阳率领三弟子入山作神丹,丹成,令弟子试,两弟子因心不诚,未得成仙;另一弟子诚心服之,与师俱得仙[13]179。这里,宣传的是诚则为仙、不诚为俗的观念。据说钟离权(云房)传道吕洞宾前,为其设定了多种假象。吕洞宾面对“家人皆病死”、“盗匪将家财洗劫一空”、“美貌女子自愿以身相许”、“船至中流,黑风巨浪打翻渡船”、“无数恶鬼杀伐不止”等五次考验,心如止水,不动声色,顺利通过测试。钟离权慨叹“仙材难得”,遂下决心度其为仙。[14]707全真道士收徒时也经常以“诚”试之。王嚞在山东传教时,“愿礼师者云集”,王嚞“诮骂捶楚,以磨练之”,大多数求道者心无诚意,纷纷散去,最后得道者仅“马、谭、丘而已”[3]724。张志素等人一同到东莱拜丘处机求道,丘氏“嚼齿大骂,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惧,皆逡巡遁去”,唯有张志素“留请益恭”,长春噱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备庖爨之列[3]757。丘处机看重的就是张志素难得的“诚”的品质。
茅山道士朱象先则把历史上国运兴衰与统治者向道“诚”之与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之诚恳,有感通天地之理”,“商高宗恭默思道,梦帝赉之良弼,果求而得;传说明皇每礼谒真容,故感而见梦,此其诚之形而著者也”。至于“唐玄宗开元中,治几三代,且多善瑞,而天宝后以逸豫致乱,国步阽危。何先后大戾邪?”在朱氏看来,皆君主诚或不诚所致。其云:“先贤有言,‘有其诚则有其神’,此政尚清静,亲注老经,研精覃思,故有是非常之应。又曰‘无其诚则无其神’。此诚人或衰,衰则殆生,故灾乱亦以之而作。必然之理也。”[15]560-561认为同为唐玄宗,开元时诚心向道,故大治;天宝时诚意渐衰,故大乱。
在世俗社会中,许多信道者并无系统炼养工夫,也未见入道修仙经历,只是为了现实功利而奉道求仙。对这些人灌输“诚”的观念,对道教的传播更为有利。《玄天上帝启圣录》记述了一百多件民间信士崇奉真武的事例,绝大多数是在揭示“心诚则灵”的理念。如卷六“天赐青枣”记述饶州乐平县江州团练判官朱牧并无男女,其父临终时嘱告他必供奉真武。牧谨遵遗命,“凡遇每月下降,至诚供养,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备供养三份,精虔祭献”[16]615。终感动真武,如愿得子。在大量的虔诚信众得到神灵帮助或福祉的事实面前,人们自然会产生对神仙的依赖感和敬畏感、对神圣力量的惊异感、接受神仙保护的安宁感、违教亵神的罪恶感、与神交通合一的神秘感。通过《玄天上帝启圣录》的神异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诚”的思想在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忠孝”和“诚”之外,道教从儒家思想宝库中还吸收了多方面营养。如金元之际出现的太一道“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净明忠孝全书》规定的净明“八宝”除了忠、孝外,尚有廉、谨、宽、裕、容、忍,多为儒家学说[1]646。元代道教史籍对这些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此处不再一一论述。
二、对佛教思想的融摄
佛教与道教自汉魏之后一直处于一种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中。佛道之间的斗争虽然一直很激烈,但互相吸收利用,特别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地方甚多,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仪礼规范等,都从佛教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这一思想倾向从元代道教史籍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尤以普度众生思想及重视心性修炼、提倡禁欲主义等方面最为突出。
(一)对佛教普度众生思想的融摄。
普度众生是佛教提倡净化人间,使六道众生悉皆度化、脱离苦难的一贯宗旨。道教产生之前的方士和神仙家一般只热衷于个人成仙,或帮助帝王、贵族成仙,而对救度普通人没有多少兴趣。道教产生后,这种追求“自度”的神仙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更为精致的、对成仙充满自信的“自力本愿”的神仙思想。然而,作为一种旨在济世救民的宗教,仅仅局限于“自力本愿”的“自度”,是很难赢得信徒、扩大影响的。因此,道教吸收佛教普度思想,融入自己的教义中。如灵宝派重要经典《度人经》宣扬“普度天人”,把道教历来以自己修炼功成得道为主的教义,发展成必须积德行善、普度众人后才能成仙的思想,显系受佛教大乘经戒的影响。从此以后神仙也有了救苦救难的责任,更能号召一般民众了。元代道教史籍中普度思想更为丰富,尤以道教神仙传记和碑铭集最为集中。
“度人成仙”一直是道教传记的一个重要主题,而神仙度人时大都不考虑受度对象的出身,而以“仙缘”、“道性”为依据,基本上符合“普度”的特征。《仙鉴》继承了《神仙传》、《续仙传》、《洞仙传》、《墉城集仙录》等道教传记的这一主题思想,以道教中人的角度记述了大量的官宦、商贾、平民、隐逸、道士乃至奴婢得道为仙的故事,其中不少是被先天真圣或后世神人度化成仙的。如卷三十五太上真人度唐若山,卷二十二多位神仙度王可交,卷三十七许宣平度老妪为仙等,不一而足。《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汇集吕洞宾的各种显化传说,基本上也是普度主题,只不过受度之人多是得到现实实惠,而非羽化升仙罢了。吕仙曾说,愿“度尽天下众生,方上升未晚”[14]711,足以显示其普济群生的情怀。而其度化重点又集中在客商、郎中、小商人、妓女等社会中下层民众,拥有更为广泛的信众,也更能体现普度众生的思想。
全真道史籍所彰显的普度思想也比较突出。有关全真道士建观度人、苦己利众的事迹充溢于《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等书之中。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途中主持了数次斋醮活动,表现出其救济苍生的愿望。在大雪山,规劝成吉思汗“不嗜杀人”是丘处机的重要话题。东归路上,他谓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3]809其中虽有发展本教的用意,但悲天悯人的情怀显而易见。此后,为了救民众于刀兵之中,全真教徒四处营造道观,传戒度民。全真道士度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从精神和肉体上拯救教化世上之人,为之清心疗疾;或建斋设醮,超度荐拔死去的亡魂,或著书立说传播道教义理,运用智慧悟性为他人指点迷津。当然,度人的同时,也包含度己,即通过自身的修炼,广积善德以达与道合真,得道成仙。对于“普度”的意义,全真道士有深刻的认识。元代著名儒者王鹗曾向王志谨询问,为何其年已八十,仍为度化信众四处奔走,王志谨曰:“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辈遗嘱,富贵者召之亦往,贫贱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请亦往,千里来请亦往。急于利人,不敢少安以自便耳。”王鹗又担心所接触之人,多不知底细,“岂无恶少博徒,无乃为累乎?”王志谨答:“全真化导,正在此耳。使朝为盗跖,暮为伯夷,则又何求?”[3]756由此可见,全真道士已经把普度众生的思想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其宗教实践之中,这也正是全真教由无到有、由全真七子到万朵金莲,再到“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3]789盛况的内在原因。
(二)借鉴佛教思想,渲染业报因果之说。
佛教认为自种业因,自收业果,亦即造业是感果的因,受报是造业的果。善业善果脱离苦海,能进天堂;恶业恶果永遭轮回之苦,要进地狱。道教对这种思想早有吸收,如南北朝时期所出的“灵宝经”,宣扬所谓“灭度”、“轮回”的成仙步骤,即要经过几死几生、若干轮回之后才能成仙。受此影响,元代道教史籍也充斥着丰富的业报轮回思想,较前世道教史籍更为生动。这种思想以《梓潼帝君化书》最为典型,该书通过梓潼神话,宣讲扬善惩恶、因果报应观念。如卷三“口业”条云:龟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常讥笑、疵毁、轻侮、鄙薄他人,对别人过失增饰传扬,以一为十,当众侮辱、诅骂。有如此恶业,自然有恶报。祝氏中年得舌黄之饥,使人砭刺出血。不数日又作,寻复治之。大约一岁之间,疾五七作,不下出血一二升。梓潼帝君命功曹又严惩之,令其“自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于地,观者千百。使自宣其过曰‘人之口业,不可作也’。如此月余,舌枯不能食而死”[7]311。该故事旨在阐扬人生在世,口业非轻,切莫妄语邪言的思想,否则不需死后入地狱,眼前即会遭受砭石、犁舌之苦。同卷“东郭”条云:东郭人黎永正以造权衡为生,有智数,多机变,巧于求利,“有欲深斗重衡为嘱者,倍取其值而与之;其欲减勺为升、减合为斗、省铢为两、省两为斤者,亦如之”。因久业于此,不欲顿废,终有恶报,“育有二子,生而即盲”,其本人亦“双目失明,别无生理。五指朝伤暮残,脓血甫干,肌肤未平。寻复指节零落,不能执持”。二子亦相继死去[7]312。此等故事在《梓潼帝君化书》中尚有不少,如“回流”、“驯雉”、“感生”、“返火”等条讲善报,“天威”等条讲恶报等,主要思想不离乎佛家善恶有报、因果轮回之套路。
这些思想在其他元代道教史籍中也有反映。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丘处机西行路上以诗示道众云:“生死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4]483他还填词一首,有“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枯荣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兴一废常如此。死去生来生复死,生死轮回变化何时已”之句[4]489,阐述了天道、社会轮回报应之说,慨叹生死轮回不停的痛苦。《净明忠孝全书》也宣扬罪福因果思想。有弟子问:“罪福因果之事,有之乎?”黄元吉答道:“大凡作善者,譬如下五谷种子,分明是春种秋收;作恶者,譬如弯弓入阵,决定有报箭来。”[1]652此说与佛教自种业因、自收业果之说如出一辙。可见佛教业报思想对道教影响很深,亦足证元代道教史籍对佛教思想摄取之普遍。
(三)受佛教禅宗影响,重视心性修养。
中唐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讨论有无、体用问题的本体论转入探讨心性问题的心性论。一般认为,道教的心性论是受佛教心性论影响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又直接促成了道教修仙理论向重心性修养的改变。这一倾向可以从元代道教史籍中显现出来。《净明忠孝全书》受儒学影响很深,但也吸收了佛教心性思想。基于净明道对终极理想的设计,其修道过程可分三步骤:“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1]647即以儒家的忠孝伦理作为修道之基,然后再采用去欲正心的修道方法,最后以复归人的本心净明之境为修道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在其修道三步骤中,以“去欲正心”为核心的修道方法显然深受佛教的影响[17]。禅宗比较强调道不可修、佛无待求、无心任自然即一切圆满。受此影响,净明道也对传统道教所执著的种种修道方法作出变革,强调“正心”的重要性,而所谓“正心”,就是“夙兴夜寐存着忠孝一念在心”,认为只要“平居暇日,存守正念”,时刻以忠孝德性立本,就可使“心如镜之明,如水之净”[1]636-638。如此,则欲自然去,道自然成,方寸自然净明。因此,净明道的“去欲”以“正心”为要。心正,欲即可去。正心去欲,即谓解脱真人。根据这种“正心”而“明理复性”的内在超越理路,净明道也像慧能禅宗那样,破除对出家、诵经等各种外在化、形式化的修行方式的执著,强调修道应该在心上下工夫,追求心的解脱。所谓“道由心悟,玄由密证,得其传者,初不拘在家出家”[1]652。因为在家、出家仅是修道者生活方式的差异,关键在于修道者是否能够以忠孝立本,是否能够“去欲正心”,从而觉悟本心之净明。又云:净明之道“贵在乎忠孝立本,方寸净明”[1]634。可见,净明道“去欲正心”的修道方法飘逸着浓厚的禅化色彩。
佛教将贪、嗔、痴视为众生沦于生死苦海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净明忠孝全书》也将“忿欲”看作人达到净明之境的主要障碍。其云:“人之一生,本自光明,上与天通,但苦多生以来渐染熏习,纵忿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为人之道。”[1]635即是说人的心性本自净明,但生活在尘世之中,因“纵忿恣欲”而受蒙蔽,难以显现。其中论述“人性本明”的思想带有佛教的痕迹。此外,黄元吉在释“净明”时云:“若能深明性地,不染一尘,动静俱定,应酬无伤,是名真净”;“澄湛心愿,冰壶水月,映彻万象,寤寐恒一,是谓真明”[1]649。既然心地已“不染一尘”,恐怕忠孝德性也没有附着之地,这与其师忠孝立本、纯然天性的思想是相背离的。但是,引进佛教性空思想来解释“净明”的迹象非常明显。
其他元代道教史籍也部分地论及道教心性学说。如《仙鉴》卷四十九《张用成》,比较道释性命之学,言简意赅:“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又云:“性命本不相离,道释本无二教。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故号曰金仙傅大士。”[13]383张用成不仅道出了道释性命学的差异,而且指明道释合一,别无二教,揭示了二者的联系,堪称的论。《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汇集吕洞宾传说故事,因吕氏修仙路径,兼摄禅宗,故《妙通纪》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禅道思想。书中极力阐释死生之说,性命之理:“万里融通则心朗彻,七情宁息则性圆明。此心澄息,自然本性玉虚”,“性一太空,寂明寥廓。了无生灭,何死生之虑?”字里行间透露出禅家意蕴。又说吕洞宾经过神秘羽士点化愚蒙,“顿然彻悟,万幻皆空,一真洞晓”[14]706。在“慈济阴德”条中,吕仙慨叹凡人“自心昏迷本性,致使贪恋幻物、悭吝钱财,而生嗔怒憎爱”,并主张佛教抛弃名利、潜心修性之说。所谓“十载文章尽饼,三场事业空花”,为人当“粉碎幻化形骸,冰消音声色相”,“拂开名利网,超出是非丛”,以求得“清净法身,圆明坚固”,使本来之心“亘古亘今,真常不坏”[14]706。其说皆禅宗明心见性的法要。
重视心性修炼是全真教义的突出特点,全真高道留下了许多著作,对心性之学多有论述。在元代道教史籍中,直接阐述本教心性理论的内容不多,但在一些碑铭集中留下了一些大儒或高道的评论性文字,可以帮助我们对全真心性学说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如徐琰概括全真教宗旨说:“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3]740基本上指出了全真教道禅合一的特性。王磐亦云:“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3]758其对全真教的认识与徐琰大体一致。元好问记述秦志安事迹云:“正大中(1224—1233),通真子遂置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稍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要,既而于二家之学有所疑。”[3]783此可印证秦志安的心性思想主要来源于道释二家。李国维对毛养素评价甚高,认为其“识性命之理,了斯生之事”,堪为“百年以来,能继重阳、七真之风”者[3]777。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全真高道“明心见性”的特色都很认同,并以其为得道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吸收佛教禁欲思想,提倡忍辱苦修。
世界上许多宗教都视人间的物质诱惑和生理欲望为罪恶的根源,佛教即是其中之一。它以禁欲主义为修持手段,要求人们克制欲望,绝欲弃智,习作苦行,以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道教神学理论承接老庄思想,与道家无为之旨本来相通,具有清静寡欲的特征,主张节欲,但不倡导禁欲。南北朝时陆修静、寇谦之等整顿、改革道教,已经汲取佛教禁欲之说。但道教史上真正奉行禁欲主义修持方式的只有全真教,其教制规定教徒须断酒色财气、忍辱苦修。《重阳立教十五论》明确规定:“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18]154王嚞本人及全真道士正是此教义忠实的执行者,元代道教史籍通过记述全真高道言行的方式对此作了充分的印证。
全真道士苦修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水平,摒弃一切物质欲望,以磨炼意志。王嚞对马钰说过:“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3]727全真教视食、睡、色三种基本生理需求为修道障碍,对其刻意减少,甚至禁绝。王嚞度化马钰,即以此历练其心志:“祖师令师锁庵,斋居百日,日止一餐。虽隆冬祁寒,唯笔砚几席、布衣草履而已。”[3]729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也是“人馈之食则食,无则已”,“虽祁寒盛暑,兀然无变,如是者六年”[3]739。王处一的苦修一向为人称道,其“志行确苦,尝俯大壑,一足跂立”,致使“观者目瞚毛竖,舌挢然而不能下”,时人称为“铁脚仙”。他曾洞居十年,制练形魂。丘处机对其苦修精神深深折服,赠诗颂曰:“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3]737丘处机本人在磻溪穴居期间,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人谓之“蓑衣先生”[3]734。后来的全真道士也继承了这种禁欲苦修的修持方式。王志坦行化之时,“日丐一食,虽蚊蚋嘬败,亦不屑弃。匪茆而居,不计何地,遇昏暮则止”[3]776。这些都是全真教徒奉行苦修思想的例证。
全真教以禁睡为修炼功夫,丘处机在磻溪修道时,“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龙门山七年,如在磻溪时,其志道如此”[3]734。即使在西行讲道路上,仍然恪守禁睡教规,丘处机写道:“日中一食哪求饱,夜半三更强不眠。”[4]489据说李志明事长春真人后,至诚修道,“至肋不沾席者十余年”[3]774。云阳子姚玹得马钰真传后,“目不交睫,肋不沾席十有余年,深入大妙”[19]520。蒲察道渊在汧阳期间,“于吴岳五峰山凿石以处,日只一餐,昼夜不寐者七年”[19]537。这些全真高道都以禁睡修持闻名于世。元好问亦云:“吾全真家禁睡眠,谓之练阴魔,向上诸人有肋不沾席数十年者”,并记述了离峰子于道显在许昌时“通夕疾走,环城数周,日以为常”[3]750的情况。可见,减少睡眠确为全真道士的重要修道方式。全真道士的苦修对儒者触动很大,几乎颠覆了他们心目中已有的道士形象,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元好问甚至认为全真道的苦修已经与苦行僧无异。其云:“予闻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老佛之间,故其寒饿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头陀然。及其有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事颖脱,戒律自解,心光烨然,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3]750
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全真道认为色欲为修道之大碍。此与早期道教及同时期的正一、净明教义甚为不同。许多记述全真高道的传记、碑铭特别强调这些道徒在入道前都誓不婚娶,以彰显其禁欲向道的决心和与生俱来的仙缘道性。如然逸期素有向道之心,“及其长也,淡然寡欲,乐慕玄风”,父母欲妻之,反而激发其出家为道,“誓而弗许,遂礼清阳子桃花陈先生为师”[3]782。孟志源提及婚事即悄然离去,“父母与议婚事,公遁去”[3]771。潘德冲在家人为其娶妇前,也是偷偷逃走:“潜往栖霞滨都观,请谒长春。”[3]810类似的全真高道还有王志谨:“甫冠将娶,不告而出。”[3]755夏志诚一心为道,父母只好默许:“甫弱冠,不愿有室。自求出家,父母亦知不能夺其志,从之。”[3]763
[1] 黄元吉.净明忠孝全书[M]//道藏:第2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 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4]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道藏:第3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5]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M]//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6] 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M]//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7] 佚名.梓潼帝君化书[M]//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8] 佚名.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M]//道藏:第3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9] 司马承祯.坐忘论[M]//道藏:第2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0] 吕锡琛.论净明道吸纳儒家伦理的方式及其意义[J]世界宗教研究,2003(3).
[11] 李道纯.中和集[M]//道藏: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2] 佚名.宫观碑志[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3]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M]//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4] 佚名.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M]//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5] 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6] 佚名.玄天上帝启圣录[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7] 孙亦平.论净明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J].世界宗教研究,2001(2).
[18] 王嚞.重阳立教十五论[M]//道藏:第3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9]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B958
A
1007-8444(2010)02-0214-08
2009-11-05
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指导计划项目(SZ070503);唐山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刘永海(1968-),男,河北遵化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道教文献的研究。
责任编辑: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