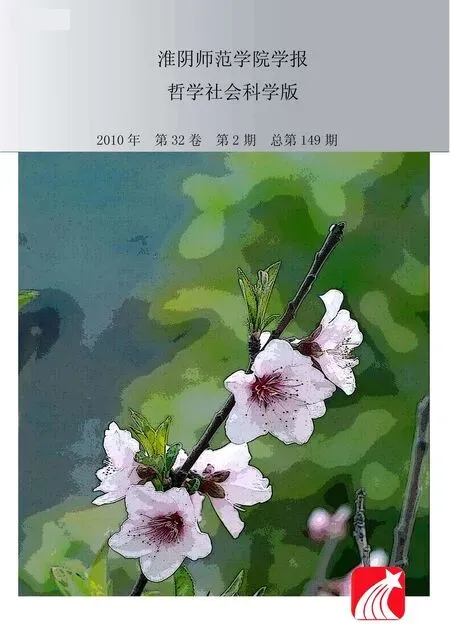近代物理学革命中的问题还原
2010-04-11沈健
沈 健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近代物理学革命中的问题还原
沈 健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问题还原是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问题。文章梳理了近代物理学革命中的一些典型问题还原案例,从而为问题还原的现实存在提供了新的案例支撑。同时,凭借这种案例分析,笔者认为问题还原与科学革命其实各属不同的范畴,但二者本质上并不绝对是互斥。
近代物理学革命;问题还原;科学革命;关系
科学源自人类对自然的惊叹,这些惊叹在科学家那里便是一个个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永不穷尽,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然而,这些科学问题之间的关联结构究竟如何呢?事实上,在科学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发展中,不同的科学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还原性,这种还原性就是托马斯·尼克斯所谓的问题还原。本文将展示近代物理学革命中的典型问题还原案例。借此,一方面为问题还原的现实存在提供新的案例支撑;另一方面,借助这种案例分析,笔者将对问题还原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一、近代物理学革命起源中的问题还原
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源于古典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内存的诸多问题。按照柯依列的观点,这些问题聚焦于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抛体问题(抛体为什么运动)(P1),二是落体问题(加速下落问题)(P2′)。其中,后者包容于前者之内,因为任何抛体运动本身就包含了上升运动和下落运动,因而抛体问题便分化为上升运动问题(P2″)和下落问题(P2′)。由抛体问题转去关注落体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分裂式的问题还原。
P1:抛体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亚里士多德运动学理论与具体科学事实的矛盾: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抛体运动为受迫运动,而被迫运动“需要与运动物体相邻的动因的不断作用”[1]12。亚里士多德不承认什么远距作用,他认为“所有运动的传播都暗示着接触”[1]12。另一方面,抛射体却在没有动因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运动。
P1的解决:对于P1,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一种解决方案——媒介反作用推动理论(T1)。他认为抛射体周围存在着媒介的反作用推动,抛体运动源于抛射体周围媒介的反作用。但是,这一回答却颠倒了原因与结果的顺序,因而也与我们的直接感觉相违背。
P2′(博纳米科):落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另一更棘手的问题,即物体下落为什么速度越来越大?这一问题在亚氏物理学体系中由于被归属于自然运动,因而不成为问题。但是,对于后来的中世纪学者而言,下落加速度究竟来自哪里,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自然运动,如何会产生出变化的效果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属于P1的子问题,是P1的一种分裂。
P2′的解决:通常存在三种解决方案。第一,认为下落加速度源自媒介阻力的减小(1T2′);第二,认为同抛体运动一样,下落运动也源于媒介的反作用(2T2′,其中2T2′=T1);第三,认为存在着冲力(3T2′:冲力理论)。
P3′(贝内代蒂):贝内代蒂首先考究了反作用解释理论(T1或2T2′)的合理性,并提出了新的问题P3′。他认为反作用只能推演出抛体速度的减小,而不能推导出速度的增加,但抛体刚开始阶段却存在一个加速过程,这便存在着矛盾。
P3″(贝内代蒂):对于冲力理论3T2′,贝内代蒂认为,冲力这种运动力作为运动物体固有的运动的原因,其本质并不清楚,因而冲力这个新概念成为迫切需要解释的问题。此外,冲力否定了媒介的运动作用,也就是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T1或2T2′(T1或2T2′否定了真空和真空运动的存在),因此真空运动是完全可能的。但真空中的物体做什么样的运动呢(1P3″)?它具有什么样的速度呢(2P3″)?实际上,1P3″是P3″由推演出的一个特殊情境问题,而2P3″是1P3″的进一步具体化。
P3″的解决理论T3:伽利略对冲力做了界定,他认为外加的运动(冲力)像热或冷一样会内存于运动物体之内,成为诸如物体轻或重的内在性质或特征,“动因以不同的方式将运动的性质或力加在运动物体上”[1]44。在伽利略看来,这种冲力是逐渐减小的,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运动要依靠运动过程中逐渐减小的驱动力来维持(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惯性原理不兼容)。
P4:伽利略的冲力理论T3,存在着与具体事情的矛盾,因为诸如大炮炮弹之类的受迫运动在一开始却是加速的,这与伽利略的“随着运动进行,速度总是要减慢”相矛盾。此外,对于落体问题,伽利略认为物理下落是由于一恒定的力(重力)所引起的,因而物体将以恒定速度下落,而且这个下落速度的快慢仅取决于下落物体的重量,这也与具体事实不符。尽管,后来伽利略对上述回答做了改变,认为下落运动开始是加速的,在到达合适的速度之后将做匀速运动。但为什么一开始运动是加速呢?而合适的速度又是什么?
P4的解决理论T4:伽利略认为,任何物体都同时内存轻性和重性,对于一个抛射体,轻性存在一个缓慢的耗光过程,而自然的重性是不变的。这种轻性和重性的差值决定了物体速度的变化,而一旦轻性用尽,只剩下重性,则物体将做一种匀速运动。在伽利略看来,不同物质接受和保存冲力、运动的性质以及轻性的能力是不一定相同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取决于它的相对重量,而不是绝对重量。
P5:尽管伽利略的运动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宇宙概念也被他打破,空间也被几何化了,好似惯性定律就在眼前。不过,伽利略本人并没有完全走到底。因为要达到惯性定律,必须放弃运动作为结果的思想、自然运动和受迫运动相区别的思想、位置和空间的思想。在伽利略的思想里保留了宇宙中心、特殊位置的古代宇宙思想的痕迹。
P5的解决理论(T5):布鲁诺、牛顿等后继者所提出的理论。其中牛顿对抛射体问题提出了如下的观点:“抛射体,只要不因空气阻力而被减速,或因重力而被向下拉落,就永远保持在它的运动之中”[2]36,牛顿对抛射体问题的解决才真正体现了惯性定律的精髓。
上述所有问题的转化,可以用一种形式化的图式来进行概括描述,如下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问题之间的一些还原关系,从P1到P2′和P2″,存在着分裂式的问题还原,所谓分裂式问题还原就是“问题的分化”[3],一个问题分化为几个子问题。这里分化的根据不是源于T1或T1的内部逻辑不一致,而是依据一般的简单性原则,即按照P1本身的特点,对它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划分。相反,从P2′到P3′和P3″,也存在着分裂式问题还原,不过这里的问题还原需要依赖中介2T2′和3T2′,因为P3′和P3″分别因2T2′和3T2′而起。对于P3″,存在两种问题还原的路径:一是P3″→P4,二是P3″→1P3″→2P3″,这说明同一个问题可以处于不同的问题还原之中,即问题还原具有多维性。
问题还原的多维性,在笔者看来,可以形成一种问题还原有核网络模式,该模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基本问题为核,众多与这几个基本问题具有还原关系的从属问题在问题核的周围形成一种立体网络结构。用“网”来形容这种结构是为了强调不仅基本问题与从属问题具有还原关系,而且不同分支的从属问题之间也可能存在着问题还原。纵观近代物理学革命,抛体问题P1和落体问题P2′就是问题核,围绕着对这两个问题核的解决,便演化出一张纷繁复杂的问题网络。其中,这张有核问题网的每个结点——各个问题之间——是依靠还原关系而衔接起来的,同时,外围的问题存在一种不断向外拓展的生长趋势。对这张网上所有问题的探索和解决,便架构起了近代科学革命演化的宏伟体系,包括轰轰烈烈的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最后由它们各自所推演出的推论也聚焦到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上。可以这样说,在壮观的革命过程背后,其本身都是由一个个科学问题所串联起来的,即问题还原最终演变成一次近代的物理学革命。柯依列就认为,近代科学革命中惯性原理提出的历史显示了“人类精神顽强地对付着那些相同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撞击那些相同的反对意见和那些相同的困难,慢慢地和艰难地锻炼手段和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使人类精神最终可以跨越所有这一切”[1]130。在笔者看来,柯依列称的那些“相同的问题”、“相同的反对意见”、“相同的困难”事实上有两重理解:一是指所有的争议都围绕着不变的那两个问题核,即抛体问题和落体问题;二是诸多“问题”、“反对意见”、“困难”柯依列之所以称为“相同”的,其实暗指它们之间内存着一种还原网络,它们之间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可通约性。
二、惯性定律提出过程中的问题还原
惯性定律的提出也涉及众多问题的转化和还原,这些转化和还原可具体分析如下:
P1:哥白尼认为,从几何学的角度看,托勒密的均论和本论过于繁复。那么,“行星应该有怎样的运动,才会产生最简单和最谐和的天体几何学?”[4]172在W.C.丹皮尔看来,此问题是哥白尼心中最重要的问题。
P1:的解决理论,即哥白尼的t1:太阳中心说——大地在运动,太阳保持静止,太阳是宇宙的灯,是宇宙的心,是宇宙的统治者。这种新的天体运行理论相比托勒密的均论和本论结构具有高度的简单性和谐和性。哥白尼理论不仅改变了之前的宇宙观念,而且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信仰。
P2:托勒密及其支持者认为,地球假如运动的话,以24小时旋转一周计算,这个运动将使地球分崩离析,并且早就飞离苍穹;一切生物和可以活动的重物都不可能静止稳定P2;自由落体不可能垂直到达它的预定地点;云和所有浮在空中的物体将在任何时候都向西运动。
t2(哥白尼及其支持者对P2的解决):主张圆周运动是天体的自然本性,由于一个自然运动会破坏运动物体的自然本性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不会产生地球分崩离析的情况。地球表面的物体、甚至那些没有直接与地球相连的物体都受到地球的拖曳,这些物体在物理上是附着在地球上的,它们参与地球运动,因而都属于一种自然运动。宇宙的运动比地球快得多,大小也比地球大得多,难道天穹就不崩溃吗?
在上述反驳观点的基础上,哥白尼进一步认为,不仅是土,以及和地球在一起的水元素跟着地球在运动,同样,空气的一部分和所有其他与土和水元素联系的物体也都跟着地球运动。即提出了物体参与地球运动的思想。哥白尼把天体力学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地球上的现象,从而拒绝了月下区和月上区的划分。
P3:哥白尼的上述回答存在着这样的可质疑之处,“如果自西向东的运动是所有土性物体的自然本性,怎样能够承认这一自然倾向对生物由东向西的运动会没有任何影响?”[1]136事实上,哥白尼的推理概念是不明确的,他提出的是一种虚构的重物参与地球运动的解释,其推理不是一种物理学的解释,准确地说不是一种力学的解释,而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认识。如何提出一种较为深邃的推理概念和一种系统性的物理理论呢?这一问题是哥白尼理论首先要解决的。
t3:对于哥白尼的P3,布鲁诺发展出一种物理学系统的概念。地球上的物体参与地球的运动,不是因为其自然本性,而是因为这些物体被动参与地球的运动。事实上,运动物体是力学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力学系统的内涵就是物体和地球参与共同的运动。布鲁诺以船的运动和地球的运动的相似性阐明了他的力学系统的思想,进而认为同一地点可以参与不同的力学系统来实现各种不同的运动。力学系统对处于其中的物体的驱动效能或力(冲力)足以说明那些即使没有接触而存在的持久联系。力学系统概念引出了运动的相对性原理,依此原理得到了空间无限性的思想,而空间的无限性可马上推出占据宇宙中心的太阳将失去它的特殊位置。空间无限性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空间的完全几何化。
t3的革命性:t3的提出是极具革命性的。布鲁诺的宇宙无限性、自然统一性、空间的几何化、处所的否定、运动的相对性,激起了否定传统宇宙和物理实在观的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这一革命在柯依列看来已经十分接近牛顿了。开普勒以引力概念取代哥白尼的自然一致性概念。认为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个力存在于组成这些物体的物质微粒中,这个力在石块中,也在地球中。
P4:然而,如何用一种理论体系去解释重物下落、地球转动、行星绕太阳做圆周运动?仅仅停留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另外的新物理学来取代它,布鲁诺的形而上学是泛灵论和反数学的,因而急需一种新的物理学。
t4(P4的解决):牛顿提出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使P4得到了解决,尤其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即“每个物体继续保持其静止或沿一直线作等速运动的状态,除非有力加于其上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2]36,第一次真正从物理学的规范意义上吹响了近代物理学大革命的序幕。
简言之,从P1到P4的还原模型就是:
P1→t1→P2→t2→P3→t3→P4→t4
可以看出,从P1到P4,形成了一条问题不断转化的还原链。沿袭这一还原链,我们看到了研究的不断深入、问题的不断明朗。从最开始哥白尼下意识地反对托勒密体系的庞杂,到最后将问题明确限定为仅仅是要寻找一套规范的物理理论体系,随之而来的是问题的不断明确、无关问题的不断被剔除、深层和基本问题的不断被挖掘。这种不断转化的问题链,一方面说明了科学家在寻求理论过程中的曲折和随机,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活动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因而这些科学问题的转化具有一种非控制性,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不断涌现的非控制性问题直接指引和限定了科学家的探索路线。许多时候,科学家的研究路线的选择是不自觉的,他的研究范畴将被限制在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相关问题里。所以可以这么说,牛顿之所以能担当起建立经典力学宏伟体系的使命,与其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如说是巨人们留下的问题逼着他去提出解决理论;同时,碰巧的是,巨人们的那些问题又恰好已经发展到能够建构经典力学体系的那一步。问题还原的这种特性说明了在科学的突破上也存在着“时势造英雄”,同时这种特性也很好地解释了某个时代为何经常出现科学发明和发现的优先权之争。
三、伽利略、笛卡儿、牛顿三者思想脉络中的问题还原
通常认为,伽利略物理学是关于重力的物理学,这里的重力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下落,笛卡儿物理学是关于碰撞的物理学,牛顿的物理学是关于力的物理学。在伽利略那里,他关注的问题只是下落运动的本身,即下落运动的规律,但并不知道重力到底是什么,因而在他的物理学里,只谈论重物的运动,但是回避谈论重力。在笛卡儿那里,他关注的是由接触而生运动的问题,他提出一种漩涡理论,认为通过接触可以产生运动的漩涡,这种漩涡论处于伽利略运动理论和牛顿物理学之间,按照丹皮尔的观点,“这比伽利略所想象的、后来通过牛顿加以系统解释的超距作用产生加速度的力,容易了解得多”[4]205。不过,同伽利略一样,笛卡儿也没有对这些力的成因和作用的方式加以说明。只是在牛顿那里,才真正建立起了力同运动的关系,“运动的改变和所加的动力成正比,并且发生在所加的力的那个直线方向上”[2]36-37。进一步,牛顿还将其力学原理从地上转到天上,通过其万有引力定律,从均匀散布于天空中的物质推导出了新的宇宙结构。
通过对这三位科学家所关注的科学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存在一种还原性。伽利略作为这三人中的先锋,着重关注了一个具体性的问题,即落体问题,落体是伽利略物理学的主线。笛卡儿所关注的问题已经开始涉及普遍性的运动问题,也就是关注因接触而产生的所有运动问题,这比伽利略的问题要更为宽广。而牛顿的物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要比笛卡儿又更普遍些,因为他不仅关注运动,而且还关注力以及力与运动的关系,不仅关注地上运动,而且还关注天上运动。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PG(伽利略所关注的问题)、到PD(笛卡儿关注的问题)、再到PN(牛顿关注的问题)存在着一种还原性,它们内含了一种范畴的不断拓展、问题域的不断扩大,以及问题的不断基本化。在这里,每一问题的前继问题最后都成为它的子问题,这正符合还原论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科学思维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这样一个自然发展历程。这其中,前继问题就是从属问题,紧接其后的问题则是该前继问题的基本问题,基本问题对从属问题具有一种外延上的包容性。此外,鉴于问题还原的延续性,从属问题和基本问题存在着一种相对性。例如,PD对于PG是一种基本问题,而对于PN,则只能属于一种从属问题。
从问题还原的角度上看,伽利略、笛卡儿、牛顿这三人所关注的科学问题是具有还原性的,他们的思想之间保持了一种连续性。柯依列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伽利略的有保留的和谨慎的叙述之后,在伽桑狄的含糊不清的解释之后,在托里拆利的那些令人佩服地清晰但却枯燥的完全的数学的公式之后,我们达到了笛卡儿的简明扼要的陈述。”[1]128这正表明了近代物理学革命的背后保持了一种科学的连续性和可通约性。
四、问题还原与科学革命关系的新讨论
对近代物理学革命内含问题还原这一事实的展示,势必逼迫我们否定科学哲学界一个占主流的观点:问题还原与科学革命保持着互斥性。笔者认为,问题还原与革命事实上具有如下的关系:
宏观层面的革命
这一图式说明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问题还原与革命并非互斥。革命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两个小理论的变革,而是整体的一种颠覆,因而在时间上不是瞬时的,所涉及的面也不仅仅只是一、两个小理论,它包含了内蕴于科学之中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变化。而问题还原只是这种整体革命之内的阶段性、部分性演化。整体而言,问题还原是包含于革命之内的。在近代物理学革命中,颠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建构起的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换位就是革命,但是内蕴于这两大理论体系换位之下的是诸多问题与问题的还原和转换,比如上面我们所揭示的问题还原都内蕴于这种革命之中。从这里,我们得出结论:革命是诸多问题还原的整体效应,相对于问题还原,它是一种宏观性的;而问题还原却是革命之下的一种精细分析,相对于革命,它是一种微观性的。由此,革命与问题还原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互斥性,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正如史蒂文·夏平所言:“过去并不是在任何个别瞬间转变为‘现代世界’的”[5]7,这里的“个别瞬间”就是问题还原,而“从过去转变为‘现代世界’”就是革命。
其次,问题还原与革命分属不同的范畴。依照库恩的观点,革命应该是外在的人对某段同样的科学历史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范式时,对同一段科学历史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认识;二是指不同(身处范式)的人对同一段科学历史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牛顿时期的科学成就,那就是一次巨大的革命,但假如以牛顿时期的某位科学家的眼光去看当时的科学发展,在他眼里,可能那段同样的历史并不会有现在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壮观。史蒂文·夏平就认为:“我们讲述的关于伽利略、玻意耳、笛卡儿和牛顿的故事,多少反映了我们20世纪末的科学信仰和我们对这些信仰的评价……事实上,17世纪人口的压倒性多数并不生活在欧洲,也不知道他们生活在‘17世纪’,更没有意识到一场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5]7这种不同时期的人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认识就是库恩所谓的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库恩的革命是一种“人”与“自在发展的科学”的交互作用所共同激发出来的一种观念变化。由于问题还原涉及的是自在发展的科学中的某些连续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描述,其本身并没有将外在的人搅合其中,只是力求描述科学发展的自身。所以就这一点来看,科学革命与问题还原原本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中的概念,二者甚至没有可比性,故更谈不上对立性。问题还原是具体的、实在的,是关于自在科学内部变化的描述,它关注的对象就是科学发展的本身。相反,革命具有抽象性和非理性,它是人的观念对某件同样事物在看法上的非连续性跳跃,它揭示了人与科学历史诠释的相关性。
最后,问题还原与科学革命的互补性说明了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在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上具有互补性。事实上,还原和革命分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因此还原与革命的互补性实则蕴涵了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互补性。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自身微观演化的精细分析,历史主义则跳出科学本身,注重人、社会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从它们关注问题的差异性来看,这两条路线其实是互补的两条哲学思考进路,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互斥和对抗。
[1] 柯依列.伽利略研究[M].李艳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2] 牛顿.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M].H.S.赛耶,编.王福山,等,译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 沈健.量子革命与问题还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89.
[4]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史蒂文·夏平.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M].徐国强,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N031
A
1007-8444(2010)02-0174-06
2010-01-15
2009年梅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应学院科研项目“量子逻辑里的问题还原探究”(2009SK15)。
沈健(1974-),男,湖南溆浦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量子力学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