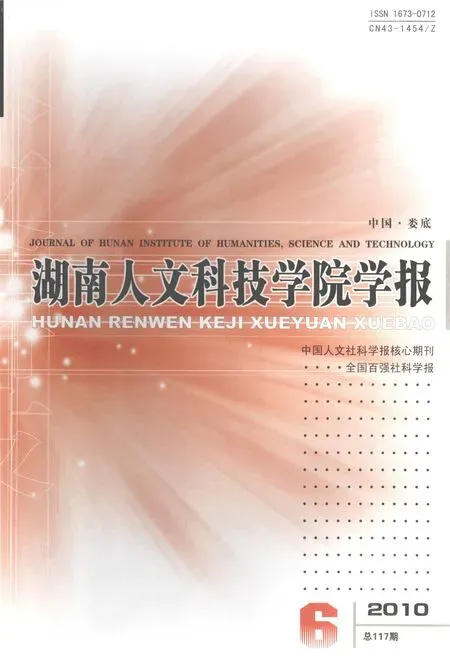朦胧诗命名的意义及其限度
2010-04-07郑加菊粘招凤
郑加菊,粘招凤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朦胧诗命名的意义及其限度
郑加菊,粘招凤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1970年代末,朦胧诗以异端的呐喊给那个时代带来了难得的思想冲击力。朦胧诗的命名表达了当时诗歌的外在美学特征,暗示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的艰难,而且展示诗歌内容揭示了人内心的隐秘、直接指向心灵的品读的特质,命名在这些意义上很好地传达了它自身的涵义。但是当时代过往,朦胧本身的含混意指使得其之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难以逃越它的美学牢笼,成为新诗歌发展的桎梏。回到朦胧诗命名的现场,考察朦胧诗命名的内涵、直击命名活动本身,可以清晰地触摸诗歌发展的脉搏,有益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困境进行更好的思索和考量。
朦胧诗;命名;意义;限度
朦胧诗以异端的呐喊给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带去了难以想象的思想冲击力,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等作为诗歌的一代表形象屹立在诗文化的长河里。朦胧诗这个概念
也在读者和批评家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涵义。“三崛起”、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等等话语不断地出现在许多评论文章里,渐次形成了对朦胧诗这个概念的基本叙述和评价方式。然而,由于时代风尚和人们阅读经验的变
化,以至于文学研究者也感叹“对某种文学现象所作的概括,提出的概念,它的有效性是很有限的。”[1]65进入当代,许多文学研究者开始对一些习焉不察的现象和概念进行质疑,比如关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命名是否合理,“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指涉等等。当我们在为朦胧诗后诗歌的不振扼腕痛惜时,除了归罪于市场经济这个客观因素和诗歌本身的发展之外,笔者也在思考朦胧诗这样的命名是否对其之后的诗歌形成一种牢笼,一种限制,也由此相信这样的考察对当代诗歌的探索会带来一些帮助。
一
回到命名的现场,直击命名活动的历史状况,更能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那涌动的诗坛的脉搏。从而来考量这一命名活动的意义所在。1979年,诗人公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文章里说到顾城的几首诗让他大为惊骇,认为应该对这样的年轻诗人进行正确的引导,随即掀起了关于这时候的诗歌的论争。第二年,章明刊发了《令人气闷的“朦胧”》,对那些“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诗,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便称之为“朦胧体”。同时,顾工也气愤地指出“我越来越读不懂我孩子顾城的诗,我越来越气忿……”[2],可见,老一辈的许多诗人都在诗歌的“不懂”上表现出自己的不解和焦虑。随后,朦胧诗这个概念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许多评论文章里被引用,它意外地适应了在其初创时期,只是朦胧觉察到的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如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臧克家《关于朦胧诗》,周良沛《说“朦胧”》,艾青《从朦胧诗谈起》等等。在这些评论文章里,他们认为诗意是清楚的,就不能算作”朦胧诗”,总之,还是在“不懂”上发感慨。臧克家甚至严厉批评“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3]把诗歌功能上升到社会功用上。连备受年轻诗人所期待的老诗人艾青也认为写诗“首先得让人能看懂”。即使到了1984年,公刘依然重申《诗要让人读得懂——兼评<三原色>》。透视1980年代初对朦胧诗的批评的景象,不得不注意,朦胧诗之所以遭质疑和批判,归根而言,罪魁祸首在于它的晦涩难懂。
与此同时,朦胧诗的支持者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认为:“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情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孙绍振先生坚信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起之秀徐敬亚认为“一首诗重要的不是联贯的情节,而是诗人的心灵曲线,一首诗只要给读者一种情绪的感染,这首诗的作用就宣告完成。”[4]当事人顾城在回答关于“懂”与“不懂”的认识时,也谈到“对于诗和人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由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来决定的。”[5]并且提到每个人都有审美的阶段性,它是随着人类进步,个人成长而不断发展的意识。侧面地回击了反对者。19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副教授郑树森遥说“在西方,意象派的试验早已被吸收为现代诗的常规而不再引起注意了;就是曾极力借鉴西方的台湾现代诗中,这种集中的色彩意象也已被认为过时了;而顾城的诗在中国大陆却正在引起某种‘不熟悉’的感觉和种种否定的评论。这就是朦胧诗派现象的反讽意义。”[6]海外学者从外部环境来考察中国当时的诗坛状况,更多指明在诗与读者之间,大多是读者的问题,而非诗的全部过错。当时的批评家所设定的“衡文”标尺,更多的来自于他们的阅读经验。
朦胧诗这个命名的由来大致如此,人们常常只是记住了谁第一次提出了这个称谓,而实际上,命名的活动本身是一个不断地折中和累积的过程。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及诗评家都无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话语表达。不难看出,命名表面上的简单、明确,给许多读者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个名称对当时的诗歌而言首先是一种贬低。诗论者大多以诗意是否清晰来品评一首诗歌的好坏。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一诗,不但写得不朦胧,而且还很新颖。“顾城同志的《远和近》,怎么读也读不懂,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写这样的诗。”[7]他们大凡只是单纯地从诗歌表面上的晦涩难懂这一点来进行解读,拘囿于诗歌难懂背后的社会意义,而较少分析诗歌在美学上的意义。这种评价上的分裂,说明了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分化”。而朦胧诗本身的社会批判性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后来对朦胧诗的指责消失了,舒婷的诗歌被选入了课本。朦胧诗在最大程度上使读者的审美意识和阅读视野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在相继地论争中不断地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朦胧诗在一开始作为权威批评家眼中的异端,但是在相继地论争中也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窥见当时的权威性已经有所旁落,先前的文学评价机制也已经有所坍塌。朦胧诗成为打破国家话语方式的一个开始,同时也开始了一个追寻个人话语表达和选择的过程。
二
在当前的学界,有持续的“评价”的冲动,命名活动更是频繁。本雅明说“人在语言之中传达着他自己的精神存在,而人的语言是通过语词来言说的。因此,人是通过对其他事物的命名来传达其精神存在。”[8]命名的名称如何向我们传送,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因为命名同时包含着一种精神存在。可见命名对于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性。反过来,人也只有通过命名这一活动,才能更好的向他人表达自身。
朦胧诗这样的命名首先最直接地表现了它的外在特征,其次也暗示了当时诗歌的语言环境的艰难。按照朦胧诗的支持者的理解,他们认为朦胧诗最直接呈现了它的美,朦胧美。孙绍振说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内核”,他一再强调习惯问题,认为新的习惯必须向旧的习惯借用酵母。朦胧,在传统上的意思是具有朦胧美,“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诸如这首诗表现的就是读者所理解的朦胧意境,美不胜收。孙绍振先生的用意或者正是借用传统的这些合理的内核,顺势推出了朦胧诗这种美学原则。命名的直接性,易懂性显示了这个命名更好的向他人传达自身,给人们更加深刻的印象。朦胧诗这个名称首先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时过境迁,当人们提到何为朦胧诗,便可以从这个名称本身阐发诗歌的应有之义,也可以由此推及诗歌当时的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本质内涵。
同时,朦胧诗的命名也展示了诗歌内容揭示了人内心的隐秘、直接指向心灵的品读的特质。朦胧诗的难懂性关键也就在于其内容上的模糊、晦涩。因为朦胧诗是指向诗人自我心灵的独白,非得有类似的人生体验不能理解,非得静下心去体会不能理解,非得有必要的知识水平不能理解,非得在朦胧中体会出清晰不可。
正如朦胧二字本身的含义一样,模糊、含混,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的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因为朦胧而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如果在解读上把它单纯化或单一化,就势必会削弱朦胧诗的艺术本性,朦胧诗也就不再是朦胧诗。如果说,“当代文学”老让人觉得是“当前”的文学,这导致了语义上的含混,那么朦胧诗这个概念也总让人觉得只要是朦胧的诗歌,都可以归为朦胧诗,而含混了这个名称应确切表示的内涵。因而,这个命名实际上过于宽泛了。当时评论者把大量的具有僭越传统的异质性诗歌统统纳入了讨论的范畴,而且直到现在,关于朦胧诗的许多作品,诗人以及概念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叙述方式、叙述体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这也反映了命名的有限性和研究与思考的局限性。而这种有限性在朦胧诗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
在人性刚刚得到舒解的时候,朦胧诗以叛逆性的姿态宣告一个质疑时代的到来。他们自觉承担起历史和现实苦难的双重书写,追求宏大的叙事和主体上的真实,多采用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手法并擅用鲜活的意象群,所有这些皆增加了语言的所指性难度系数,大肆地冲击了当时诗歌阅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受心理。同时也造成在当时的许多诗人看来这些诗歌晦涩难懂。甚至谢冕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对朦胧诗进行总结时,曾从“看不懂”的角度对朦胧诗的某些方面有所批评:“例如某些诗篇过于夸大破碎形象的偶然拼凑,甚至浮表地满足于浅层次的象征和繁荣的装饰,相当数量的词语不合常规,无节制地使空茫的意象充斥诗中,而作品的可感性达于低点。”[9]这个特点是朦胧诗的特质,也是它在一开始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有趣的是,第三代诗歌,有些写得十分直白,有些却把这一缺点放大到极点,很多出现了“看不懂”的现象。第三代诗人们试图通过打破习惯性词语的组合模式,追求词义的幽秘和多义,从而颠覆一体化的词语霸权,达到心灵的自由抒写。以钟鸣的《树巢》为例:风吹过草原,我们两眼茫茫,血,在碑额上停止无用的奔流。羊群在最后一线烛光中遭到女巫炽热的语言放逐。光明,无畏黑暗者最初的光明。树巅上神秘的叶子在头顶消失,牙在阴影里恢复,石麒麟和玉蟾蜍,优美的乱伦,人类的俗气?鱼鸟各有各的卵,各自的统治,各有各的巢,无论是庭前的玉树,还是在死者身上找到的没有光泽的徽章,或者以仁义为剑,或道德为胄,这些都无法使他摆脱死者,一根硕长的金指甲,以鸡鸣树巅上,在火苗里,在采采服饰上为他徒劳地讲授庸俗的地理学。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繁杂密集的词语展览,毫无规律可言的纵横散乱的扭结组合,互相碰撞覆盖,激起一片奇异怪诞的喧响。很难找出贯串一致的内在含义,词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被彻底切断。不能不说,第三代诗歌在选择了以朦胧诗为反叛目标,虽然在命名上与朦胧诗廓清了关系,但是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美学特质却实实在在地因袭了朦胧诗美学特征的一方面。本雅明还说:“人给予语言的名称取决于语言是如何向他传送的。”[8]8那么,第三代诗歌这样的命名应该取决于诗歌给人的美学感受是如何向他传送的。反过来说,第三代诗歌给我们的美学感受也是多义性,含混性,可否说属于它的命名应该也是朦胧诗。问题到这里就出现了先后的关系。朦胧诗在先,而第三代诗歌在后。朦胧诗是一个具有多种解读性的命名,借用本雅明先生的一个说法“过度命名”,用在朦胧诗这个命名上是很自洽的。所谓“过度”指超越适当的限度。朦胧诗的过度命名使它的适用性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超越了命名所该有的指向性。时过境迁,它的超时代性的命名仍一直笼罩着第三代诗歌。第三代诗歌必须为自己命名才能划清与反叛目标的界限,走上一个新的高度。而朦胧诗的出现是时代使然。但是这种朦胧诗宽泛式的命名最终使这个命名带来的涵义走出了一个时代,又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很显然,它也一同包括了第三代诗歌的难懂性。这种过度性的命名使得其之后的诗歌一直很难摆脱它的美学圈套,那么,其之后的诗歌就更加无法形成自己命名下的美学原则,从而也就难以具有不绝的生命力。当一种命名涵盖了另一种命名下的创作,命名本身便失去了一定的意义。后一种命名可以为前一种命名所取代,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存在或者说美学原则却有部分重合。当试图彻底反叛的结果造成是精神上因袭的压力,作为对一种美学原则的反拨时,却出现了相同的价值取向。不能不说,这种命名的有效性是很有限的。
三
在对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潮流的研究和评述中,文学研究者常常喜欢用一些概念来拢括复杂的互有差异的体验和具体性,用概括来替代具体分析。洪子诚在编写《中国当代新诗史》时,把牛汉诗人1980年代的诗歌编在章节“七月派”的诗群里面。牛汉发言说:“我根本就不是‘七月派’,‘七月派’早就不存在了;50年代‘七月派’就不存在了,我就是我,为什么还把我放在‘七月派’里头?”[1]45我们看到了,概括自身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这压力不仅是对自身,更是概括以后对后来者产生的影响和压力。对一些思潮的命名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动,有些命名显示出了影响的尴尬,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重复命名的现象。诸如对一个诗潮的命名,单对朦胧诗后的诗歌就有各式各样的命名,目前看到影响较大的就有“新诗潮”“后新诗潮”朦胧诗“后朦胧诗”“前崛起”“后崛起”“第三代”“新生代”“实验诗”“现代诗群”“现代主义诗群”等等。这看似喧闹的命名活动,实际上也体现出研究和评述本身的些许无奈。
“朦胧”诗,“朦胧诗”?实际上当朦胧诗成为一个确切的命名时,它也就挤压和掩盖了之后同征诗歌的命名空间,甚至是生存空间。纵观我们史学上的朦胧诗后的诗歌,其最明确的特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朦胧”。或者说,朦胧诗后的诗歌仍然是“朦胧”诗,其美学内涵和精神存在在读者的第一印象中仍然是“朦胧”,至于其他的特质,就被掩盖在这背后。另外,细致思考如“第三代诗歌”等的命名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无力突破的妥协,第三代诗歌的特质是“第三代”?这显然无法给读者以直接美感的牵引,而成为一种无奈的提示。
命名本身就意味着研究者的独到发现,独特的命名正是体现研究者研究实践的价值核心,其内在包含研究主体的创造性思考、艰辛性求索和特殊性见解。其一,一个独特的命名往往指向一种独特的研究思路、观察视角。其二,一个独特的命名往往包括研究主体艰辛的探究的过程,是对其艰辛劳动的科学总结。其三,一个独特的命名就是研究成果的展示,是对研究的独到发现的合理概括。然而,历史不断发展,新旧更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一个命名越过了它命名的时代,它便常常成为一个旧物,甚至成为一种新事物诞生和发展的桎梏。
当然,对这些已经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名称,我们不能无视也不能轻易抛弃。轻易抛弃的话,会使很多具有体系性的概念和叙述消失,而一些重要问题也因此而消失,这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找寻这些名称、主张和“语境”之间的关联,辨析它们特定的内涵。同时,对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不要过于着急为它命名。缺乏时空的一定距离,研究者获得超眼界会比较困难,容易就事论事。身处其中,情感、经验上的一些因素,也会成为一种束缚。而一旦一种名称已在不断地被论述中成为一种既定的表达方式,那么它自身的限度也就开始显露出来了。
因此,在还没有特别看清楚事物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妨先让时间来“荡净”一些假象,从而更好地为文学把脉。在朦胧诗发生后的20多年,我们继续对这段历史进行探讨,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相信对今天和明天的文学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启示性意义。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5.
[2]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J].诗刊,1980(10):28.
[3]臧克家.关于朦胧诗[J].河北师院学报,1981(1):56.
[4]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J].当代文艺思潮,1983(1):78.
[5]顾城.朦胧诗回答[J].文学报,1983:82.
[6]郑树森.论《“朦胧”诗》[J].艺术争鸣,1987(4):47.
[7]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N].光明日报,1980总汇.
[8]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2):5.
[9]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J].文学评论,1985(5):108.
(责任编校:光明)
Significance of Naming Misty Poetry and Its Limitation
ZHENG Jia-ju,NIAN Zhao-feng
(Literature Institut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In the late 1970s,misty poetry exerted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ideas of the age with unusual cry.The naming of misty poetry displayed the external esthetic features,and implied the hard environment of creation at that time.What’s more,it also showed the traits that the contents of poetry could be directed at the mind to reflect the secret inner world of people.In these senses,the naming expressed itself well.However,as the time passed by,due to the ambiguous implication of the misty poetry,it is hard for the later poetry to break the bonds of the esthetic conventions in some aspects,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creation.Back to the scene of naming misty poetry,inspecting the meaning of the naming and the naming activity itself,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oetry development clearly,which is beneficial to better consider and speculate on the plight of contemporary poetry development.
misty poetry;naming;significance;limitation
I206.7
A
1673-0712(2010)06-0053-04
2010-10-26.
郑加菊(1985—),女,福建漳州人,南充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