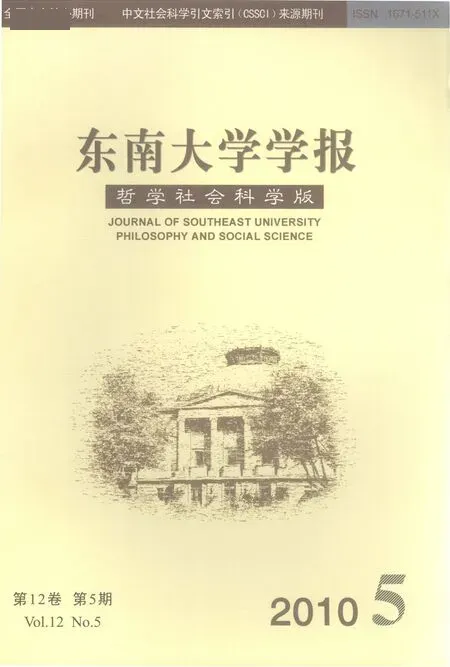天地境界
——杜诗中的人伦、人道、人格
2010-04-05林继中
林继中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63000)
天地境界
——杜诗中的人伦、人道、人格
林继中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63000)
本文从人性角度切入,重评杜甫与儒学之间关系。杜甫取儒学的人道精神,又借重道家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追求,形成自家具有个性的人文关怀,在实践中以己饥己溺之亲历去亲证“一国之心”,由是在现实的人伦之际保留“真我”,进入既有道德又超越道德的“天地境界”。杜之真性情使其能“以我为诗”,推动诗歌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新变。
天地境界;杜诗;人伦;人道;人格;以我为诗
杜甫与儒学之关系,是个古老的话题。然而在经历了长期对中国文化精神作沉痛反思后之今日,它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本文拟从人性的角度切入,略陈管见。
一
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将个体自我定位在人伦关系中,把他看成群体的分子,社会的角色;在西方视角中,至今被视为是个体缺乏主体性的一大弱点。然而人性中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更是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文化史家庞朴认为:
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韦伯);用中国的观点看西方,可以说西方人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的人格①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同。。合理的观点,也许是两者的统一;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分子,既是演员,又是角色[1]234。
这种合璧自然是令人神往。不过中国传统文化对“独立人格”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应忽视。
我们就从个体的定位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体定位于人伦之际,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仅仅是起点,并非终结。《论语·学而》有云: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泰伯》又云: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将个体定位于伦理秩序中,无非是为了促成社会道德的自觉,达成和谐社会。孔子将孝悌的礼制人性化,培养人伦日用的道德情感,从而使血缘关系超越特定的氏族社会的历史局限,成为“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孟子进一步明确指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 ·公孙丑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人伦正是通过个体的互动,跃入人道。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个体的人格。诚如李泽厚所指出:“与外在的人道主义相对应并与之紧相联系制约,‘仁’在内在方面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2]29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有云: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个体由是又独立于人伦之际。这才是中国人所认可的独立人格。这固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主体性”,但现代“独立人格”之建构就与之不相容吗?就人性的本质而言,个体自我的独立人格不应当置于脱离乃至与社会绝对对立的境地上。
笔者正是居于这一认识来探索、肯定杜甫的道德情感与独立人格。
二
杜甫对妻儿、兄妹、族人、朋友之挚爱,为历来论者所乐道,可不必再议。至其民胞物与,泽被瘦马病鹤、鸡虫蝼蚁,也广为人知,同样可不必再议。萧涤非先生曾以“人道主义”概括之,认为“这是杜甫的基本思想”[3]49。涤非师一方面指出杜甫这一主导思想来源于儒学,同时又指出另一方面:“但他却不像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出现。为了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的。”[3]50先生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新制布裘》二诗作了比较,认为杜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与白居易“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境界不同,“白只是推己及人,杜则是舍己为人”[3]50。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一部杜诗,便是杜甫‘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实践。”[3]51这正是杜甫与一般儒者的重大区别,是个性化的“人道主义”。杜甫只取儒学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其推己及人并非儒家道德教义的演示,而是以社会底层一分子的身份在苦难的现实中以己饥己溺之亲历去亲证“一国之心”。也就是说,其人道精神并非从取儒学经典“涵养用敬”、“格物致知”,或作内心的“理欲交战”中得来,他的人道精神既是无我的,又是有我的。只是他的“我”,与当时苦难大众之心是相通的,是为“己饥己溺”。浦起龙于此似有会心,其《读杜心解·读杜提纲》乃谓杜诗“慨世还是慨身”。
如何是“慨世还是慨身”?细读杜诗,不难发现:老杜对世事发感慨,无不与自身经历、处境息息相关,筋连着骨,十指连着心。不必举《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与“三吏三别”诸名篇为证,即以被朱熹判为“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及王夫之讥为“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例,亦可看出杜甫慨世与慨身之间的血肉关系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跋杜工部同谷七歌》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王夫之《诗广传》卷1云:“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之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嘑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兹列二诗于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云: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鴐鹅后鹙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同谷七歌,长歌当哭,撕心裂肺。逢此绝境岂能不仰天一呼,感慨万端:“胡尘暗天道路长”、“杳杳南国多旌旗”。男呻女吟的妻儿,存亡未卜的弟妹,乱世罹难的大众,尽在慨身慨世之中。卒章乃感慨曰“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无奈中的愤激语,正与《秋兴八首》云“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同,而朱熹竟责之“叹老嗟卑”。噫!施鸿保《读杜诗说》卷九斥之曰:“朱子特未遭此境耳!”痛快。“遭”与“未遭”间,是道铁门槛。唯有“遭此境”者才能慨身即慨世,不以“救世主”自居,在亲历亲证中直觉“一国之心”,将“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诗序》)。《奉赠韦左丞丈》言抱负不作谦语,直指“致君尧舜上”,言困顿不讳狼狈,直云“残杯冷炙”、“朝扣暮随”。是真性情,也是当时一大批失意寒士的真境况。杜之所以卓然特立者,乃在于困顿中不弃理想。毕杜一生,“此志常觊豁”(《咏怀五百字》),体现了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弘毅精神,是上引“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贫贱不能移”之“大丈夫”精神。这也是杜甫“叹老嗟卑”、“悲辛杯炙”之与嗟来之食者迥异之处。
应提醒注意的是:杜甫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单向的“推己及人”,杜诗中还表达了对他人的“推己及人”的感激之情。如《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云:
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且遇王生慰畴昔,素知贱子甘贫贱。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沈年苦无健。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兼求富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脚轻欲漩。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
穷愁潦倒如此,杜甫尽情写出,言人所不屑言、不愿言、不敢言,为的是表达感激之情,更是要肯定、歌颂人世间尚存的那点温情。唯有“遭此境”的杜甫,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之可贵,它是道德的,又是超乎道德的。典型如《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袴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至如《奉赠王中允维》,对迫授伪署的王维更是在同情中包含着宽容:“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这与刻意以道德律人而不恤者是不同的。这种情怀使其“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的爱憎分明的性格更为丰满细腻。出自公心,且能带一种体贴他人之情(恻隐之心),这就有很高的人生境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评“曾点气象”有这么一段话: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道德情感能在伦常日用中随处充满,自然流出,便是所谓的“天地境界”。哲学家冯友兰对此作了详尽的发挥,认为此境界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之上。蒙培元《理性与情感》将此四种境界概述为:
自然境界中的人是没有自觉的,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都是有自觉的,但是又有不同。功利境界中的人的自觉是有私的或求利的;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自觉是无私的,为公的;天地境界中的人的自觉则更高,他既是无我的,又是有我的,无我者无私我,有我者,有真我。他不仅是为公的,而且是超越道德的,是“天地万物一体”的[4]。
我于哲学,向无“觉解”,但观此自觉而又自然,无我中有我,初无用意却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不难体会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使我不禁联想到涤非师解读杜甫的《又呈吴郎》,于此我体悟到杜诗中的无我、有我与真我。原诗如下: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涤非师说,第一句“任”字很重要,要让“无食无儿一妇人”放手去打枣儿吃,爱打多少就打多少。杜甫写这首诗,仿佛是在对吴郎说:朋友!对这样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穷苦妇人,你说我们能不任她打点枣儿吗?紧接二句又叮嘱说:如果不是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心怀恐惧,我们更应该表示亲善。于是第五、六两句转落到吴郎,十分委婉地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心存戒备,未免多心了,但你一搬来就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含蓄的提示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味太重,反有可能引起吴郎的反感。联系题目《又呈吴郎》,须知此草堂本是杜甫所有,只是让后辈的吴郎居住,反用了一个表示尊敬的“呈”字,好象和对方身份不相称,其实这些正是为了让吴郎较容易接受劝告,体现了杜甫“不以救世主自居”,极尽体贴他人之真情。结句也是全诗的结穴,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流泪[3]205-209。这不就是上面说的那种很高的境界吗?
三
冯友兰言四种境界之分别,认为在自然境界中,人不知有我,其行道德之事是由于习惯或冲动;在功利境界中,人有我,即行道德之事,也是为我,将它当作求名求利之工具;在道德境界中,人无我,其行道德之事,是因其为道德而行之;而在天地境界中,人亦无我,不过此无我却是有真我。“有我”有二义,一是有私心,一是有主宰。尽心尽性,皆须我为。“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所以天地境界中人,不惟不是无我,而是真正地有我。这种“真我”,是依照人之性者,得以完全发展①详见《冯友兰选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82-28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依此,我粗浅的体会是,所谓“天地境界”,应是人性的“全”:人不但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他的一切行为,不但要合乎道德,而且这种道德规范已然内化为道德情感而无处不在,自然流出,毫无矫情,其外在形式正与自然境界同。所以冯先生又说:
尽人职尽人伦底事,是道德底事。但天民行之,这种事对于他又有超道德底意义。张横渠《西铭》,即说明此点。《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余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此篇的真正好处,在其从事天的观点,以看道德的事。如此看,则道德底事,又有一种超道德底意义。[5]347
以此观杜诗,岂不“正蹋着杜氏鼻孔”(浦起龙《读杜提纲》语)!且看杜甫《题桃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宋人赵次公笺注引陈恬语云:“参得此诗,乃知杜公作诗之妙处。”次公又云:“题止谓之题桃树,非是专题咏桃,盖因桃树而题其所怀也。此诗含仁民爱物之心,与夫遏乱喜治之意。……公后有《[又]呈吴郎》诗云:(略)。意与此合。”[6]745-746明末清初人黄生《杜诗说》卷九又有所发挥云:“本题桃树,乃因实及花,因人及物,复因一室及一方,因一方及天下……观其思深意远,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弄鸟之际。”赵注云“此诗含仁民爱物之心”比黄笺云“寓民胞物与之怀”更贴合杜甫“初无作意”的情怀。与《又呈吴郎》合读,的确能发露杜甫仁民爱物之心。不过黄生的推导更觉细密:“因实及花,因人及物,复因一室及一方,因一方及天下”。连类而及,民胞物与打成一片。如果说任桃树遮径而不忍芟其枝,与“总馈人食”尚有功利的联系,那么帘户通燕、莫打慈鸦的愿心则更纯然是对生命的爱惜。故黄生《杜诗说》卷九又云:“此诗与五言‘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同意,所谓‘易识浮生理,难加一物违’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依相待之“理”,岂不是“道德底事,又有一种超道德底意义”?而此种意义,又岂能囿乎儒学一家之说?
事实上,道家所谓的“道德”,就具有超越儒家从人伦之际所确定的“道德”之意义。《老子》有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徳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三十八章)高亨认为,上德之“德”,指自然德性;下德之“德”,指人们创造的“仁”、“义”之类[7]89。仁义之类的道德要次“法自然”之道德一等。《庄子》也认为:“乘道德而浮游”“,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此是“道德之乡”。冯友兰认为:“我们所谓天地境界,用道家的话,应称为道德境界。”[5]84可见天地境界是包括儒道二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共同构成了“人与天地参”的精神境界。其中,庄子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描述,无疑丰富、强化了儒家“独行其道”的人格本体论。而儒家弘毅的人格力量加上道家求“全”(人性之健全)、求“真”(真性情)的人性诉求,便是杜甫极具张力的情感结构的两大资源。老杜卓尔不群处,就在于他一直是在人伦秩序中捍卫着个体人格的尊严,取嵇、阮之狂狷而不流于诞,取陶潜之质性自然而不避现实,以真性情为“独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就了一部沉郁顿挫、风格独特的杜诗。清代叶燮《原诗》有云:
“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叶燮可谓道尽杜诗中的道德境界,却尚未道尽杜诗中的天地境界。倒是性格复杂、情感丰富的苏轼,早早便看出杜甫健全人性之端倪。他一方面指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另一方面又欣赏其“闲适诗”《,书子美黄四娘诗》有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轻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东坡题跋》卷二)“轻狂”二字直道出老杜与嵇、阮、陶之间的同异。日本学者宇野直人曾统计过从《诗经》到鱼玄机的诗中出现的“狂”字的使用频率,其中李白现存997首诗中“狂”字出现27次,杜甫现存1450首诗中出现26次[8]45。李杜有力地开拓了“狂”字的表现内涵。作者举杜诗:“痛饮狂歌空度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等例,认为杜诗中狂的状态多半伴随着酒和歌,含有失意、避乱、自隐、感愤、不得已而为之等意味[8]51。所言甚是,但尚不足以包涵苏轼所谓的“轻狂”。先读苏轼“喜而书之”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的二首: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这种“狂”与狂歌痛饮之“狂”有相当大的区别,恰好是老杜草堂定居后的一种新心态。《江村》一首道出其中缘故: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仇注云:“燕鸥二句,见物忘机。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这是一种人性复归的感觉。再取《客至》、《遣意二首》、《漫成二首》连片读去: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
与杜甫在两京忍辱负重、无可奈何的日子相比,杜甫在田野闲适生活中相当惬意。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春水花径,邻翁野老,相处十分融洽。其原因一则有“故人供禄米”,二则“眼边无俗物”,不必再“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秦州诗)。老杜此际之“轻狂”,是与“真”相联系的。
真,是包含着善而又高于善的健全人性。自晋人“以山水明道”以来,开发了“人的自然化”的意境,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是自然美与人格美同时被发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9]183它使一些士大夫在大自然的感召下,暂时忘却名利得失,使人性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这是一种“真”。老杜成都草堂诗也往往得此意境。然而这仅仅是其“真”的一个方面,杜甫之真,更多的是率真,近乎王充“疾虚妄”之真(《论衡·佚文篇》)。兹举数例: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
物白讳受玷,行高无污真。(《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长任真。(《狂歌行赠四兄》)
将“直取性情真”与“驱驰丧我真”合读,更能领会老杜“思朝廷”与“忧黎元”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天宝末,杜甫就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道出这种尴尬: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乾元二年(759)杜甫决然踏上远离朝廷崎岖西行之路,“不忍便永诀”终于不得不诀。其原因不但是长安饥馑,还因为对朝廷不明是非的失望①笔者另有《杜诗的张力》一文。。入蜀后杜甫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地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咀嚼人生经验,进行深刻的反思。其独立之人格也因此而展现在诗作中更具一种自由精神: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欲填沟壑”竟有雅兴从容流连于雨荷风竹间,这正是老杜后期“轻狂”本色。与当日在朝“避人焚谏草”(《晚出左掖》)相比多少自在!真,就要“吾丧我”,不断舍弃“假我”、“非我”,渣滓日去,真吾(我)日来。在这点上似与晋人近。但杜并非玄学式从摆脱人际关系(人伦)中去寻求个体独立,而是儒学式仍在人伦之际确立个体之价值。然而这种确立又并非从“涵养用敬”、“理欲交战”的内省功夫中来,而是放下社会面具,不矫情、“疾虚妄”,以真率之丰沛感情去贴近现实,进行反思,从体验中来。在这点上又与后来的宋人远。这种态度使杜甫在远离朝廷时能“以我为诗”,开辟诗国新天地。王嗣奭《杜诗笺选旧序》说得透彻:
(杜诗)每一阅之,别是一番光景,转阅转妙,如探渊海,珊瑚、木难,在在皆是,而不能穷其藏也。然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情与境触,其变无穷,而诗之变亦无穷也。(《杜臆》卷首)
的确,杜甫后期“以我为诗”极具创造力,其深刻的反思性,其历史意象之丰富,容另文专论。这里只就其因率真而开创的新题材、新意境略作讨论。
涤非师非常欣赏老杜《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认为诗人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刻划了田父直爽、豪迈的性格“,他完全陶醉在这位田父的精神世界之中了。……这种农民形象,是在所有古典诗人的作品中绝难找到的。”[3]80原诗如下: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田父率真粗豪的性格跃然纸上。正是这种士大夫所缺乏的率真使诗人陶醉。《唐书》本传称杜甫在成都草堂“与田父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杜甫亦自称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寒食》)正因其亲近,所以写来亲切“,未觉村野丑”。此亦杜甫卓然独立之人格非仅从儒学“内省功夫”中来之证。更要紧的是,这种在艰难时世中与下层民众“相狎荡”的实践,促使杜甫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儒学在人伦之际建立的等级观念,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其“超道德底意义”(须知儒家的“道德”是有其强烈的阶级性的)。请一读《示獠奴阿段》: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褭褭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病渴三更廻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獠《,杜诗镜铨》引《困学纪闻》云:“北史:獠者,南蛮别种,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謩、阿段。”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的少数民族奴仆,其社会地位之低下可知。然而正是这位年轻人在天旱时不与人争水,默默地独自上山寻水源,解除了病中诗人及其家人的危急。诗人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来记述这件事的:“病渴三更廻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在这里,真便是美。涤非师曾指出:“杜甫以前,几乎没例外,七律一般都是用来作‘奉和’或‘应制’这类阿谀的官样诗体的,杜甫却大大扩充了七律的领域。”[3]31以七律为仆人作传,岂不是前无古人?而这正是在杜甫真性情推动下诗歌从题材到形式的创新。真性情之于杜诗,好比能溶化一切的溶剂“,情与境触,其变无穷”,无往而非诗。试读《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应接丧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飞来两白鹤,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损伤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经矰缴勤。三步六号叫,志屈悲哀频。鸾皇不相待,侧颈诉高旻。杖藜俯沙渚,为汝鼻酸辛。
开首则曰:“畏人嫌我真”,是老杜对自己独立人格之自觉。以下拉杂写来,但以真性情贯之,则“民胞物与”之情自然流出,浑然一体。
天地境界也许并不那么玄妙恍惚,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健全人性。当然,它有它的历史规定性。
[1] 庞朴.蓟门散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3] 萧涤非.杜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0.
[4] 蒙培元.理性与情感——重读《贞元六书》、《南渡集》[J].读书,2007(11):23-24.
[5]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 林继中 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 高亨.老子注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8] 宇野直人.柳永论稿[M].张海鸥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I206.2
A
1671-511X(2010)05-0097-07
2010-06-08
林继中(1944-),男,福建漳州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