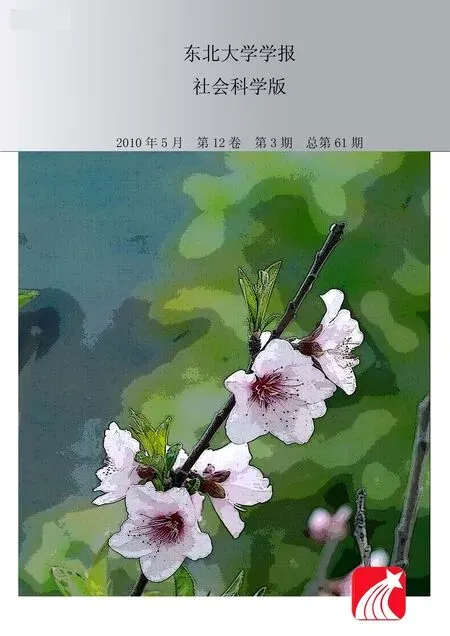跨越时空的契合
----张爱玲和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比较
2010-04-04蒋书丽
蒋书丽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 116085)
张爱玲之所以得到广大读者,包括一些学者的充分肯定,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她不仅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特美学韵味的文学世界,也用她冷峻而富有穿透力的目光发现了中国女性的特殊的历史命运。她对女性问题的发言尽管只是寥寥几句,却道出了不可颠覆的真谛,那就是,女性作为一个个体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历史条件,或者说,女人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过程,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同样,对于婚姻的本质,张爱玲也提出了和波伏娃相同的看法,即婚姻具有一定的交易性质。所以说,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已经达到了世界性的高度。在波伏娃的映衬下,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张爱玲的深刻。
一、 女人是后天形成的
这是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表达的主要观点。《第二性》被称做是妇女的“圣经”,是波伏娃的女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波伏娃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的、生理的、神话的等各个角度探讨了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角色。但对于女性的历史成因,她非常明确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的文明”[1]309。这是波伏娃对女性本质的根本性定义,并被广泛接受。波伏娃还详细解读了女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即女人被形成被塑造的过程。在论述女人的生成过程中她运用了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即“他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明中,女性一直处于客体的处境之中,和以主体自居的男性构成了二元性的冲突,男人希望通过女人印证自己的男性气质,通过女人把自己变成偶像和永远的神话,并确保自己的主权地位。而女性却一直以来甘于自己的客体地位,通过向男性的认同获得自己存在的理由,包括用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修饰自己,千方百计使自己符合男性的口味。这样女性就把自己囚禁在“他者”的处境内,因为“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1]185。于是,女人就成为男人的欲望的对象,不再可能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即女性被异化。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尽管没有如此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但并不影响其思想的光芒刺破深沉的暗夜,和另一个半球的思想者遥相呼应。张爱玲的《谈女人》发表于1944年,而波伏娃的《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就女性的历史形成来说,张爱玲的看法与波伏娃是一样的。在《谈女人》中,张爱玲很明确地写道:“女子的劣根性都是男子一手造成的”,“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为了在男权的社会中求得生存的根基,她们不得不学会献媚、世故、精明,以求得自己一点可怜的、稳固的地位,如同波伏娃所概括的女人的所谓“特性”:她“沉迷于内在性”,“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1]673。 然而女人的这些特点,全是由环境所造就。张爱玲对其笔下的女性之所以充满了理解,原因即在于此,也“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倘若她们没有如上的特性,她们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无论是父母的家庭,还是自己的家庭,是她们唯一的栖身之地,她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一生要紧紧地攀附在父母或丈夫的肌体上汲取生活的养料。所以女性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便是取悦于男人,这成了她一生的事业,用波伏娃的话来说就是,“‘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控制’他则属于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需要有相当大的能力才可能胜任的职业”[1]533。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即是掌握了这样一门艺术的女性。尤其是葛薇龙,她学习“抓住丈夫的艺术”非常认真,“居然成绩斐然”。
二、 关于婚姻的交易属性
在20世纪的西方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角度对女性进行一种社会学和哲学般的考察,而在古老的东方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性,则用形象、虚构和故事书写对女性的观察和理解,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一致,比如上面谈及的女性的生成与处境。对于女人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她们同样有着惊人的一致看法。在张爱玲看来,那些“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即“世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的职业”----妓女。这样的表达,尽管残酷,但不失真实。婚姻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就如同卖身一样是一种生存之道。对同样的问题,波伏娃是这样阐述的:“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1]489。 同时,她还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1]629。 这和张爱玲的话如出一辙。在张爱玲作品的女性中,只要是涉及到了婚姻的问题,经济是女性考虑的首要因素,为了这个目的,不惜荒废自己的青春,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不仅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如此,张爱玲本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身处幽深的封建贵族大院中的女性来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更具一种扑朔迷离感。这种写作,非张爱玲这样的女性不可。唯有她,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她们的处境和她们的情感意志,因为她是她们中的一员。女性写作对于真正地认识女性、全面地了解女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也是众多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写作的意义并提倡女性写作的重要原因。张爱玲的创作不仅在为我们认识女性解放的复杂性方面提供了理解的文本,也是对女性写作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另有意义在,她关注的是同她一样身份的都市女性。这些都市女性程度不同地经受了五四以后欧风美雨的熏染,但又仍旧保持着同宗法制度、小农意识、封建家庭等血浓于水的亲缘。她们的人数远不及身处广大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农村妇女多,但在一个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里,她们的二重性反而更有代表性。在张爱玲笔下,一度受到走出封建家庭的理想鼓舞的女性们,选择了重新回到男人的羽翼下,这既是当时中国女性现实状况的写照,也是对中国女性求解放的历史道路的反省,虽然这条道路从五四算起不过走了短短二十几年。我们看到,对这些多少接受过西学和新知识的女性来说,男人依然是她们生活的轴心。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不多的中国女性进行过文学创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她们多数人被浩瀚的文学史所淹没,更不可能书写自己。五四以后所开始的女性写作,才将写作这根探针伸到女性的意识深处,触及到她们的欲望、灵魂、思想以及她们的处境。对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来说,这种共同的处境就是两性关系和婚姻,她们对于自身的考虑和计划全是围绕着在这种关系中她们的位置和获益,所以婚姻或两性关系对于她们是一种手段。对于自身,不再有心灵、精神层面上的诉求,完全不同于五四一代。因此,“张爱玲的人物大都缺乏深远哲学性思辨能力及习惯,然而各别具有独立自足的生命。作为一个小说家----而不必是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她在一种传统中国女性的视野上,捕捉着生动传神的故事”[2]。
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实也有大多数男作家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但那无疑都是他们理想中的女性,并大多把这些女性放置在了革命的背景之下,形成了典型的“革命+恋爱”的书写模式。美国学者刘剑梅在其《革命加情爱》一书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许多左翼作家对“新女性”的想象,就是“把‘男人的阳刚性’转变成一种隐喻,象征着支配权、群众、集体、铁的纪律以及不可抗拒的革命运动”[3]。
相对来说,张爱玲对女性和婚姻的理解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基础和意义。获得所谓美满的婚姻既是女性生存的基础,也是女性存在的意义。所以白流苏费尽心机要捕获范柳原,因为“如果她要获得人的全部尊严,赢得她的全部权利,就必须戴上一枚结婚戒指”[1]494。 尽管婚姻是要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但男人并不须要通过婚姻实现自身价值,对于男性来说,结婚只是他们完成社会和传统以及家族要他们承担的一项使命,他们在社会上是独立自足的,所以婚姻对于“他”的意义和对于“她”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也需要婚姻,但不进入婚姻并不妨碍他在社会上的生存和获得性的满足,而对于女性则不然,没有婚姻的保障,就要过着更低等的寄生生活,而婚姻中的寄生对于她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女性很早就要在母亲和长辈们的教导和传授下学会如何获得男人的欢心,如何抓住一门合适的婚姻,而这个“合适”,并不完全是对男女两个人彼此性情而言,而更多是从经济上、从门第上加以考虑。这是女性获得“现世安稳”的唯一渠道。
婚姻不仅仅是对于传统女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张爱玲般的现代女性同样如此。即便如张爱玲本人,尽管她在经济上已经完全能够自立了,但花男人的钱还是让她觉得开心,“只有一次他给了她一点钱,她用来做了一件皮袄,自己设计的样式,做得宽宽大大,她心里尤其欢喜,因为这是用丈夫的钱做的”[4]。张爱玲尚且如此,何况像葛薇龙这样的尚没有自立的女学生,她选择了结婚而不是到社会上做事,很显然是把结婚当做和做事一样具有获得生存基础的一件事,把结婚当做了一种职业,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为女人准备多少职位的社会中,通过结婚获得供养就必然成为女人命定的选择,而男人则不同,结婚对于他们只不过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却不是一种命运。
女性从婚姻中获得供养,一方面显示了她的附属地位,同时也使她具有了某种物品甚至商品的属性,是男人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而女人却全然不同,只能通过婚姻才能获取生活的资格,而婚姻实则不过是一种买卖关系。由于婚姻所具有的传统赋予性,女性十分甘于接受这样的一种命运。婚姻的成功与否成为衡量女人一生命运好坏的唯一因素。而法律和习俗是支持女人在婚姻中的这种被养的地位的,即便是今天,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和习俗中,离婚时女人都可获得一笔不小的费用。在这种保护女人的外衣下,实际上间接承认的是女人的附属性。
在张爱玲的时代里,期望她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显然是不符实际的。在波伏娃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和地位尚且如此,何谈还处于封建余流中的中国女性。所以,不同于波伏娃的理性考察,张爱玲的写作中总是会透露出自己的宽容来。因为她明白她们的处境,所以对于她们追求金钱物质她是充分理解的。尽管有些悲哀的意味。《等》中的众多女人,《有女同车》中的感慨,《留情》中的“千疮百孔的感情”,都能够感受到作者那内心悲哀和些许的讽刺。作为女人,她非常理解“经济上的安全”对于这些女性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波伏娃还是张爱玲,都触及到了女性生命中的最根本的生命线,那就是她们的经济地位。自从母权让位给父权,就开始了女性的附属地位,甚至今天仍然大量存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性,更不用提在社会上她们是空洞的能指,她们的身份始终是女儿、妻子、母亲,摆脱不了“从父、从兄、从夫”的一个“从”字。对于女性的这种命运,张爱玲是很冷静客观的,她认识到了积存在女性身上的这些几千年的传统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日……”。但是,女性认识到自身处境并致力于改善这种处境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就是社会为女性的独立自主创造必要的条件。遗憾的是,我们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对自身处境和命运有清醒认识的女性,更不消说为反抗这种命运而进行抗争的了。这是张爱玲的作品笼罩在浓重的苍凉感中的本质原因,是对女性命运的一种深刻体验,而不仅仅是作者的一种审美选择。但这种苍凉感并不妨碍作者构想理想的女人形象,这个形象来自于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大神布朗》,“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缓,踏实,懒洋洋地象一头兽。她的大眼睛象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5]。这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没有任何依傍,这和张爱玲对女性的期望是很匹配的,在同篇文章中,她对女人是如此概括的:“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就婚姻对女性的实质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来说,张爱玲和波伏娃的认识可谓殊途同归。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似乎都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制着,被牢牢地绑附在男人和婚姻上面。事实上,张爱玲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根绳索就是金钱。经济上的不独立,必然的结果就是造成人格上的不独立。张爱玲从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中出发,认识到了金钱对女性从思想到人身的完完全全的钳制,并最终异化了女性。
所以,从历史的、世界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她的女性意识就会有更大的发现,她对前人的超越也就更显而易见。从她的创作,我们看出了女性的彻底解放将需要一个遥远而艰难的过程。
三、 结 语
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分析张爱玲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独特的女性意识,越发觉得她的深刻、尖锐以及她的历史超越性。她对女性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历史作场景,既没有悲壮感,也没有悲剧感,而是全从平凡琐碎入手,全从日常男女入手,铺展开的却是无尽的苍凉和悲哀,这是渗透到女性骨子里的苍凉和悲哀,直到今天,这种苍凉和悲哀还浓重地笼罩在广大女性的头顶。这是张爱玲所给我们的启示。如她所言,“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诚然,张爱玲视界的狭隘和她的审美选择,决定了她的创作只限于她所生活过的上海和香港,只限于那些平凡的小人物,没有英雄,没有人生的飞扬,没有力度。然而这也正是她的美学追求,因为在她看来,“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6]。应该说,正是由于张爱玲稳稳地踏在这坚实的底子上,才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历史,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但这种进入,已经是选择了另一种的角度,即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借助张爱玲的视角,人们发现了在女性命运背后那沉重的历史负担,并从张爱玲的犀利目光中,照见了现代女性仍然没有摆脱的羁绊。
自从张爱玲“浮出历史的地表”以来,对她的女性意识的考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她的创作是五四以来女性创作和女性意识所不可跨越的,张爱玲用她独特的审美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苍凉凄艳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女性的历史命运何其曲折艰难,更关键的是,我们发现了又一个张爱玲,因为“评论是一种发现,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发现你正阅读和评论的人是怎样看世界的方式”[7]。张爱玲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既不是揭露,也不是表现,而是一种述说,在她的述说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女性世界。历史进展到今天,女性的传统意识仍旧盘踞在心头,一方面争取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的苦闷、彷徨仍纠缠着女性,尤其是对于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主体意识的女性来说,这种苦闷尤为强烈;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又难以割舍,即便是在经济上已有一定独立自主能力的女性,依附意识仍然十分突出。因此,“嫁个有钱人”依然是大多数女性的热切追求,尤其是在女性千方百计美化自己暴露自己的背后,无法掩盖的是取悦男人的赤裸裸的目的,而在女性解放的张扬的外表下,掩盖不住的仍旧是对女性的骨子里的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弃虐女婴、买卖妇女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女性身体的再一次物品化、商品化,在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背景映衬下,形成了极其悖谬的社会怪现象。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说的那样,“父权体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之间,女性的角色消失了,并非消失于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于充满暴力的摆荡之中,如此的游移置换,正是‘第三世界的女性’限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形塑过程”[8]。所以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面对的是一种空前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女性意识和地位的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是努力寻求向男性的归属,甘愿将自己商品化、物质化,因此,女性真正“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仍需要“假以时日”,这也就是张爱玲留给我们的“苍凉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2]金宏达. 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166.
[3]刘剑梅. 革命加情爱[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63.
[4]宋明炜.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188.
[5]张爱玲. 谈女人[M]∥张爱玲文集:第4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71.
[6]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M∥ 张爱玲作品集·流言.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174.
[7]西蒙娜·德·波伏瓦. 萨特传[M]. 黄忠晶,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239.
[8]周蕾.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