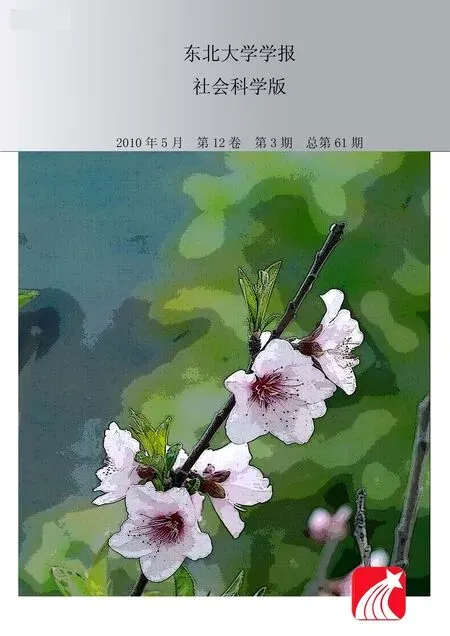逃离与复归:《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移民社区书写
2010-04-04李道全
李道全
(1.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 100084;2.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AHouseontheMangoStreet)1984年在美国出版,次年获得著名的前哥伦布基金会美国图书奖,1989年被收入《诺顿美国文学作品选集》。小说长期畅销,被誉为美国当代成长小说经典。
小说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成长在芝加哥贫穷的移民社区。受政府资助,她接受了大学教育,而爱荷华大学研究生写作班的经历,让她寻归族裔文化的宝藏,确立创作方向。对此她曾评论:“我认为我在爱荷华经历的文化冲击很重要,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他者属性,让我有意识地选择了创作主题。”作为芝加哥拉丁裔社区长大的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勇敢地执笔,书写她曾经栖居的移民社区。独特的女性视角,让她笔下的芒果街与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街》几分相似,却又明显不同。虽然两部作品都关注边缘群体的苦难,但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对女性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怀。《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成功,帮助作家摆脱经济窘境。尽管她实现了个人的突围,逃离芒果街的空间羁绊,但是她饮水思源,不忘养育自己的族群,正如小说中所言,“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1]150。作为成功走出族裔空间的女性,作家重返族裔地带,以边缘的书写镌刻族裔经验,改造族裔生存的空间。
一、 芒果街:边缘的族裔社区
随着美国社会和文坛对族裔、性别等问题的关注,少数族裔女作家异军突起,为各自的族群发出铿锵有力之声,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文学“去中心、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作为西语裔在这一潮流中的领军人物,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以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向主流文化挺进的少数西语裔作家之一。虽然少数裔女作家对于边缘的书写,帮助她们获得事业成功,但是逃离并不等于切断她们与族裔社区的情感与历史关联。边缘社区的苦难,吸引着她们再三地返航、创作与书写。边缘的苦难记忆滋养她们的创作灵感,是她们写作的素材宝库。移民生活的居无定所和社会地位边缘化,使得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与她的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经历相似的成长之苦。作为成功走出族裔社区的人,作家深谙边缘社群之痛。通过《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家回望她成功逃离的空间,书写边缘社群中的苦难。
“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故事写出埃斯佩朗莎一家的颠沛流离。不断地迁徙,不停地换房子,给小女孩埃斯佩朗莎一种漂泊感。他们一家都在渴望一所大房子。幻想中的房子是那么的美好,与现实中芒果街的小屋形成反差,而学校嬷嬷对小屋的惊讶反应更加让她羞愧。此外,随着他们的迁入,芒果街原有的居民回应冷淡。“猫皇后凯茜”的故事就写出了美国白人对于少数族裔的反感与不屑。对于少数族群的迁入,白人更多地选择搬离而不是共居。凯茜是生活在芒果街的白人,说自己是“法国皇后的远房表亲”。因为“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杂了”,所以她们一家“要从芒果街向北搬迁,离开这里一点路,在每次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不断搬进来的时候”[1]15-16。凯茜一家的刻意疏远反映出白人高傲的态度。面对他们的抉择,埃斯佩朗莎甚为敏感,倍感尴尬。然而芒果街没有因为凯茜一家的搬离而冷清。纷乱嘈杂中埃斯佩朗莎逐渐认识了芒果街的居民:露西与拉切尔姐妹,经营旧家具生意的黑人吉尔,摔断胳膊的么么·奥提兹,波多黎各的路易一家,玛琳,阿莉西娅,遇难的杰拉尔多,田纳西的埃尔,还有女孩萨莉……。这些生活在芒果街的男男女女,犹如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小镇畸人》,苦中作乐,演绎着各自的悲欢。身处芒果街,他们不能像凯茜一家那样飞往法国继承遗产,也无法规避空间的束缚。族裔身份上的他者地位和空间上的边缘化状态,阻碍了他们实践各自的梦想。虽然作家希斯内罗丝以幽默的笔触缓缓道来,但是这些悲剧人物的凄凉人生不禁引人欷 。
在美国社会,少数族裔遭受了边缘化的命运。边缘化和排斥的经历,以及由这个过程创造的空间被转换成一种战略资源[2]。在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笔下,这种战略资源得到充分开发。边缘性赋予芒果街魅力。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蓓尔·瑚克斯(Bell Hooks)在《渴望》(Yearning:Race,GenderandCulturalPolitics)一书中也同样指出:“边缘的空间”是“一个创造力和权力的场地”[3]152。正是空间上的边缘性,使得芒果街的苦难生活别具一格。但是,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Theory,2004)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边缘性如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指的那样丰饶、具有颠覆性,他们为何想要废除边缘性”[4]。此番洞见可谓是道出了边缘的矛盾境地。空间的边缘性虽然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但是相对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与中心,边缘还是处于非常不利的方位,遭到歧视与偏见。于是作家以手中笔为武器,“写芒果街女人与男人的故事,让白人主流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为改变西语裔的生存状态击鼓呐喊”[5]。作为少数族裔移民社区成长的女性,希斯内罗丝在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倾注较多的笔墨,书写夹缝中的苦难女性。
二、 族裔女性:夹缝中的生存
生于芝加哥贫穷工人家庭,希斯内罗丝有六个哥哥,是家中独女。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影响,她从小受到哥哥们的冷落,因此她很小就有了性别意识的萌芽。移民社区的成长经历更是让她意识到,在西语裔族群的文化传统中,女性没有独立的自我和身份,她们只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或母亲。同情女性的命运,她的作品也较多聚焦女性的坎坷。在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家极为巧妙地运用了女童的视角,关注芒果街的女性生存状态。
埃斯佩朗莎个性敏感。她继承了曾祖母的名字,但是她不想继承曾祖母的命运。“我要取一个新的名字,它更像真正的我,那个没人看到过的我。”[1]11从命名权可以看出,小女孩早早地萌发了女性自我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指引她敏锐的观察。她将芒果街发生的点点滴滴纳入眼中,而最让她触目惊心的是芒果街社区女性的遭遇:来自波多黎各、等待别人改变命运的女孩玛琳,期望真命天子通过婚姻带她去远方的大屋,然而美梦未遂她就被婶婶送回;因美貌而被丈夫囚禁的拉菲娜;拒绝讲英语、思念故土的玛玛索塔;因早熟而遭受父亲暴力的萨莉;遭受丈夫虐待的密涅瓦;聪慧却因家庭生活而平庸的埃斯佩朗莎的母亲。这些边缘社区的女性,不但承受了族裔群体的集体苦难,还因性别而在族群内部遭受压迫折磨。虽然她们不乏才艺,但是性别的弱势使得她们只能重复女性的历史轨迹,演绎着女儿—妻子—母亲的生命故事。
目睹了芒果街上的女性惨剧,埃斯佩朗莎决定做一个新女性:“我是那个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来,也不拾起碗筷来”[1]120。这样的宣言道出了她的心声:她不愿身陷家庭事务的牢笼,不愿做一个传统乖顺的妻子。因为诸多的见闻使她深刻感受到处于美国文化边缘的西语裔,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困境、挣扎与无奈,她决意改变自己的命运,冲破阶级和性别的樊篱,成为作家[6]。对于小女孩的写作天分,卢佩婶婶也鼓励她继续写作,因为那会让她自由。对于写作,法国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明确指出: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闭的巨大的身体领域[7]。在这里,写作因此也被赋予了解放的力量。
凭着写作,埃斯佩朗莎渴望“一所我自己的房子”。这也写出了作家对私人空间的向往:“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不是哪个男人的房子,也不属于爸爸”。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肯定了空间对于女性书写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8]。可以说,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种观点。但有别于伍尔夫的那个时代,移民社区女性的空间诉求有着独特的语境与历史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在新的时代把这一空间的诉求进一步发展延伸。然而,如何能将空间诉求现实化?小说中小女孩埃斯佩朗莎带着社区诸多苦难女性的期望,走出了移民社区,然而,逃离移民社区是否就能万事大吉?现实中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则选择族裔空间书写的回归之旅。这一逃离与复归让作家更加敏锐地把握社区的症结,以书写为武器,重构移民社区的压抑空间,为苦难女性争取更加包容的生存空间。
三、 族裔空间:复归与重构
为了那些不能离开的人,作家对移民社区的精神复归,让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饱含伦理关怀。这样小说也写出了西语裔社区的独特风景,特别是移民社区空间的特质。总体而言,小说中多篇故事都涉及到空间问题,展现移民社区中芸芸众生的生活状态。爱德华·索亚在《第三空间》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政治相关性[9]。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其中后殖民批评更是关注殖民体系瓦解后的世界空间格局。伴随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间移民活动的频繁,空间的意义将愈发显现。
栖居于空间之中,人类对各自生活的场所作出了情感上的回应,也即所谓的场所感。场所感指的是一个地方对内部人(居民)和外来者(来访者)所激发的主观情感[10]。 芒果街的场所感也因人而异。对于那些卑微沦落者,芒果街在地理方位上处于美国,带给他们希望。然而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芒果街无奈边缘化;对于暂居芒果街的白人,他们对西语裔怀有恐惧和敌意,总是迫不及待地搬离芒果街;对于来访者,故事“那些人不明白”写出了他们的感受:“那些不明白我们的人进到我们的社区会害怕。他们以为我们很危险。他们以为我们会用亮闪闪的刀子袭击他们”[1]34。 通过来访者的视角,芒果街移民社区在主流社会中的负面形象暴露无遗。芒果街因为移民的到来,变成罪恶的是非之地,他者之境。后殖民研究专家罗伯特·扬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1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移民的差异,但是面对少数族裔的差异,美国社会表现为惧怕,采取了一种同质化的政策。“别说英语”的故事写出了少数族裔移民在美国同质化过程中的苦痛。思念故土,玛玛索塔拒绝讲英语,可是她对讲英语的孙子只能泪如泉涌。背井离乡的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在美国社会该如何生存,融入主流社会还是固守自身的特异性?应对美国同质化的政策,后一种选择也必然带来冲突,必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他者。此外,作为女性,作家也不苟同族裔社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芒果街众多女性的悲剧进一步增强了她的这一意识,激发她去寻觅一个独立的自我空间。写作事业的成功,帮助作家成功走出西语裔移民社区的压抑空间。走出移民社区,逃避了移民社区对女性的歧视与压制。回望芒果街,她的成长经历提供了较好的视角,正如蓓尔·瑚克斯所言,我们既从外面往里看,又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关注边缘也关注中心。我们两者都了解[12]。这种双重的视角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着眼点,让她能审慎明晰地看待曾经栖居的芒果街。
透过作家的笔触,美国社会少数族裔移民的尴尬境遇毋庸置疑。芒果街的典型例证就从空间角度,突出反映族裔群体的劣势。流离失所的移民来到美国后,大多居住在城市边缘、族裔集中的移民社区。空间上的边缘化让移民及其后裔处于尴尬境遇,导致身份与归属感的危机。然而正是这种危机感促生了文化反思。虽然空间上的边缘化带给少数族裔困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但是也有学者明晰地指出边缘的优势。蓓尔·瑚克斯就将边缘视为战略资源,指出“我所说的边缘性,不是人们想要丢失或弃绝的,相反是人们想要置身其内,甚或牢牢依附的,因为边缘性滋生抵抗的能力”[3]149。 转换角度,边缘也能孕育出抵抗的力量,突破主流社会的规约与界定,从而最终实现“去中心化”的目的。在现存不平等的空间格局之下,这样的思维将有力地化解边缘族群的身份焦虑和自卑心理,激发他们的自觉抗争意识。从这个层面而言,认识边缘空间的潜能与颠覆力量,对于少数族裔移民社区的发展也极为重要,有助于他们走出一味逃离的被动局面。并且,是否逃离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作家的经历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由于大量移民的到来,美国的文化属性也更加驳杂,同质化与差异化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这一现象愈加明显。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专著《文化的定位》中指出,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断地处于混杂的过程[13]211。混杂化成为多元化时代抵抗主流文化同质化政策的有力武器,而边缘社区的群体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因为“去中心化”之后,中心的成分已经驳杂,使得传统的“非此即彼”空间划分观念不再适用。变革的力量呼唤以崭新的视角,审视因混杂化而产生的新型社会空间,最终实现空间格局“亦此亦彼”的开放与转换。这一切希望都被寄托在所谓的“第三空间”,因为“这第三空间移置构成它的历史,建立新的权威结构、新的政治选择”[13]211。“第三空间”的概念提出,让边缘社区的族裔群体也看到希望。正是如此,通过书写边缘,作家也将族裔经验播撒进主流社会话语,混杂传统的中心地带,为重构包容的空间秩序开辟了道路。随着这一趋势的演进,边缘群体也可能会丧失边缘特性和原有的抵抗战略资源,引发忧虑与惶恐。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发展进程也将给他们带来机遇,给边缘群体一个重新建构自身的机遇,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强势文化所设定的格局。这样,昔日的边缘社区才能更好更平等地为下一步的发展谋划。若是在这一趋势之下,移民社区固守边缘,那就是缺乏辩证的眼光,机械地理解边缘与自身特性,会阻碍移民社区的发展。
如何解决族裔社区的症结,新一轮的空间重构或许将会是一个契机,让移民社区的苦难女性参与进来,挖掘自身资源,积极介入重构的过程。因此,这样的重构就不再是过去那样被动接受同化,而是把自身的特性播撒到重构的空间格局。如果说移民群体遭到同化,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同化的势力也已经驳杂不纯,留下了族裔群体播撒的痕迹。总体而言,这样的重构试图建构更平等的对话和交往体系。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女性或许才可以实现自身的空间诉求。虽然这一过程可能也充满未知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它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四、 结 语
《芒果街上的小屋》以诗体小说的形式,展现西语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的边缘状态。族裔经验滋养了作家的创作,助她逃离移民社区的压抑。然而,逃离不代表忘却族裔历史,相反她精神上复归移民社区,书写社区中的苦痛,并谋求救治苦难的济世良方。透过小说的文字,作家强烈的责任感与深厚的伦理关怀也就不言而喻。伴随着小说的经典化,作家的策略也将启示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与美国其他族裔的文学一道形成“冒现的文学图景”。有了这样的文学作品铺垫,今后的族裔写作也就能够进一步推进,探讨新时期新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芒果街上的小屋[M]. 潘帕,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
[2]Smith S. Society-Space[M]∥Cloke P, Crang P, Goodwin M.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9:20.
[3]Hooks B.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M]. London: Turnaround, 1991.
[4]Eagleton T. After The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19.
[5]石平萍. 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析桑德拉·西斯内罗丝的《芒果街的房子》[J]. 外国文学, 2005(3):25-29.
[6]石平萍.“奇卡纳女性主义者”、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J]. 外国文学, 2005(3):16-18.
[7]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194.
[8]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
[9]Soja E. Thirdspace: Joum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Oxford: Blackwell, 1996:1.
[10]Cresswell T. Place[M]∥Cloke P, Crang P, Goodwin M.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9:226.
[11]罗伯特·扬.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M]. 容新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63.
[12]Hooks B.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ix.
[13]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