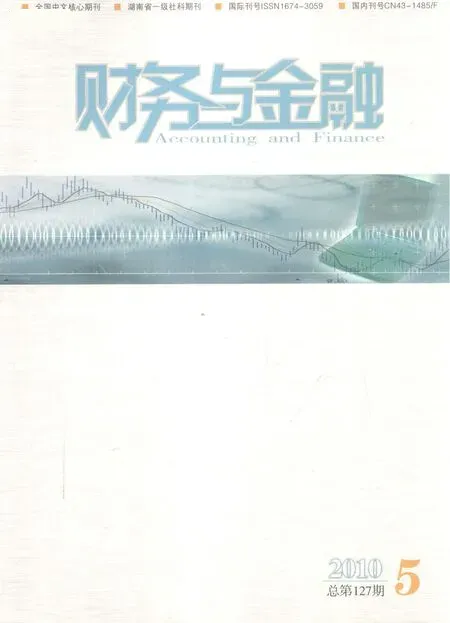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
2010-04-04陈飞翔
陈飞翔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
陈飞翔
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入手,研究土地银行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本文研究发现,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对土地产权的交易更容易产生“败德行为”,并加深“二元经济”的对立;不完整的产权制度造成了比较混乱的“多中心主体”的利益格局,出现“弱化一方,增强另一方”的经济权利的现象,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土地货币”却是政府对土地定价权独占的衍生物,通过控制“土地货币”的发行量来增减财政收入。但它们严重地妨碍了土地资本化的深化,并且不利于土地银行业务的拓展。
二元经济土地银行产权多中心主体土地货币
一、导言
所谓的土地银行就是专门用于土地及其土地附属物抵押的金融机构。世界上最早的土地银行成立于1770年的德国,迄今已有240年之久,这个名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的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图是普鲁士王朝为了解除高利贷的盘剥,需要引导大量的资金流入农村以振兴农业。1852年法国成立了“法国土地信贷银行”,它是一所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承担着实现法国政府住房政策和发放长期优惠贷款的业务。随后,西方很多国家开始成立土地银行,为土地流转、抵押、住房贷款以及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台湾也在1946年成立了土地银行,但它属于官营银行,其主要职能在调剂农业金融、配合政府推行国民住宅和都市平均地价政策、办理土地开发、都市改良、社区发展、道路建设、观光设施等一系列的金融业务办理,同时还经营一般银行的存贷款、汇兑等业务。2008年12月22日,中国大陆第一家土地银行现身于四川彭州市,这为农村土地的确权以及资金融通提供了试验的渠道。这家土地银行出现的背景是因为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大面积摧毁了城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作物,重建资金的巨大缺口必须寻求新的融资渠道,当地政府开始尝试成立土地银行来解决部分土地的流转问题,从而集聚更多的发展资金。2009年伊始,成都也相继在“土地银行”与“田间股份制”领域进行探索,主要是在一定区域内把农民承包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拆院并院”之后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分类整合,“零存整贷”,加快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
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相比,我国土地银行的成立还不到2年时间,显然稚嫩的多。特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中国的土地改革以及土地资本化带来非常独特的经济现象。很多同类文献对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土地问题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几乎没有,要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本文试图从经济分割时的产权交易、“多中心主体”的土地资本化以及“土地货币”等视角去分析我国土地银行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二元经济”的土地产权交易
黄宗智(2006)从过密型农业角度阐述了中国农业因“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用地的“半工半耕”现象,并且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化下来。实质上,这种“半工半耕”现象是一种未彻底的农地工业化。要改变这种未彻底的农地工业化可以通过土地资本化而促成。土地资本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土地产权的真实交易,另一种是土地产权的部分转移,比如土地的抵押与土地证券化。换言之,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以农村土地为例。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剥夺了农民利用土地产权流转带来巨大收益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阻隔了农民成为收租阶层的通道(2009,刘雅灵)。即使农民通过灰色通道成为收租阶层的一员,但相较城市居民的收租群体而言,其租金远远低于他们,并且还面临被其他未能成为收租阶层同一农民群体投诉的风险。低租金与被投诉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农民把手中的土地或者土地附属物转化为活财富的制度风险,这种制度风险以水平和纵向的两个方向同时出现,这对土地资本化极为不利。同时,这也对农村土地银行的成立与业务上的扩展注入了制度性的风险,但对城市土地资产的拥有者以及房屋业主权利的扩展似乎不加限制,甚至还有放大之嫌,农村与城市土地使用权利的不对称,严重造成了新的阶层之间的对立,即“土地收益的暴富者与土地收益的丢失者”。近几年,法院的土地纠纷的诉讼显著增多,并且涉及的土地利益往往是群体性的。
自从中国立法者在1984的宪法修改中,正式确立了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后,农村土地的主体从国家转移到集体的身上了,但城市土地的主体身份仍然是国家。由此,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济契约关系亦随之转移,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转向村集体与个人,这种立法的后果为后来的城市化快速扩张带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村集体的掌权者可以跳过个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直接把地卖给土地开发商,从而带来卖地腐败与村民冲突。这种奇异的产权交易大大加深了中国“二元经济”的快速扩张,既得利益集团深知,只有把农业用地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才能带来超额利润。中国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虚位”产权制度还派生出了一种奇怪的发展路径: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利用不仅包含经济绩效,还存在政治绩效。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分配的效率,还包括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姚洋,1999),而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而言更为重要,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是在农村或者“城乡接合部”的地方,那么社会保障对于农村的稳定至关重要,而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然而,最要命的是土地的经济绩效通常是和政治绩效相冲突的,土地的关系者,不管是村集体还是地方政府,都想从土地的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们通常是跳过那些“虚位”产权的土地拥有者——农民或者郊区居民——直接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这种利益冲突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愈发尖锐。这种“虚位”的产权制度还带了一个可怕的后果:由于土地产权的不彻底性而导致产权交易的“匿名”特征(2005,赫尔南多·德·索托),那些手握土地审批权柄的官员可以不需要公开他们的产权交易关系,这就为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责任通过隐形的方式规避起来了,这也有意无意地减少了他们更加肆意妄为的“败德行为”扩张的风险。
这种由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扩大了不同身份的群体在享用土地权利的鸿沟,另一方面人为地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冲突。这两种交错出现的问题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为土地资本化,特别是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农村土地银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
三、“多中心主体”的土地产权资本化
土地银行的实质是土地产权的资本化,通过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抵押或土地证券化来实现资金周转。如果土地产权不是全部的,而是部分的,甚至是“虚位”的情况下,土地抵押或土地证券化该如何处理?这也是中国土地银行面临的重大挑战。要在部分产权或者“虚位”产权的条件下,实行土地抵押或土地证券化,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去实现。一种途径是立法者重新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产权拥有者全部的产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土地产权的交易或者部分转移;另一种途径是以国家的名义承担部分产权或者“虚位”产权下的完整产权市场交易,然后再返回部分收益给产权部分持有者或“虚位”所有者。
我国土地产权“虚位”制度,给市场交易者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如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那么产权的拥有者就变成了“多中心主体”的格局,村民、村集体、当地政府、用地开发商都需要从中分配一定的利益,至于哪个主体分配的利益占优,则完全成了一个多重均衡的利益博弈。从现实情况来看,强势的政府与用地开发商往往占优,其次是村集体,最末的当属村民了。正是这种“多中心主体”的土地产权交易格局,在土地及其附属物抵押或者土地证券化方面出现了一个两难冲突:如果法律不能公正的保护“多中心主体”每个主体利益的话,那么受损者就会反对土地资本化,但得益者会极力推行土地资本化。除非立法者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虚位”所有者的完整无缺的产权,那么“多中心主体”的格局就会演变成“单极主体”格局,但从现有的情况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立法的可能性不大。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农村的宅基地以及房屋不可充当抵押物,而城市的土地及其附属物是可以抵押的。在这种立法的实践中,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资本化的演进路径就会忽视农村,偏向城市。除此之外,农业用地一旦被转化为工业用地或者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得益者大力推进土地资本化的过程。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家法律规定,土地一旦开发成房地产,那么商铺的产权最高期限是50年,城市居民的个人住房的产权最高期限是70年。如果政府把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来出让给房产开发商之后,地产商只要房产开发成功,地产商这个中间人就相当替政府发行了一种免还本息和的50年或者70年的长期政府债券,政府不但不要还本付息,而且还要征收购买房产者相关的税收。如果房地产商在两年之内没有开发土地,政府还可以强行收回,再次拍卖。如果我们把政府征来土地的成本假定为发行这种“特殊债券”的发行成本的话,那么政府再把土地转卖给房产开发商的价格就是这种“特殊债券”的收益了,若再减去它的发行成本,则变成了纯收益。我们再假设这种“特殊债券”的贴现率用最近10年银行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的简单平均利率作为贴现率的话,那么这种债券的未来值将是巨大无比,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土地及其房产的升值带来的收益。这种土地产权的“多中心主体”格局,表面上土地资本化好像是政府通过征地把土地卖给地产开发商,实质上是政府变相发行了一种以土地为载体的“长期政府债券”,这种“长期政府债券”不但不需要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而且还不需要还本付息,等到土地的使用期限一到,政府还可以再收回土地,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发行这种特殊债券了。
正是这个奥秘,“多中心主体”格局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在土地资本化的推进过程中,深受强势部门的欢迎。由此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若农村土地资本化通过土地银行这个金融中介运转时,土地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需要。
四、“土地货币”与中国土地银行
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即使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中国社会仍然面临土地问题的约束,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对人类的人口膨胀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面临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所引发社会冲突的隐患,另一方面,在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政府通常在解决这些关系到社会全局发展的改革试验时,一般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局部试点”方式进行,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向社会大面积推广。即使是在“局部试点”的过程中,要是真出现很多问题,则高层可通过叫停或者修正的方式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整体风险。2008年2月22日,中国内地第一家土地银行的成立,则可视为土地改革的试验前哨。
古代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中记载过:“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吴晓波,2010),奸富就是靠奸诈与投机致富。换言之,土地财富是从古到今都难以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土地银行的本质就是把古代的“本富”通过金融的渠道,更轻松、更高级地把土地的财富最大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因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土地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可交换的资产,还是一种“土地货币”。当然,土地在古代仍然可以成为“土地货币”,但古代的政治基础、社会条件、制度设置以及经济发展都不足以允许土地成为“土地货币”。
中国土地产权的特殊性——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很容易将土地交易后的“多中心主体”的弱势主体的利益边缘化,从而使得强势主体的利益显现化。这个强势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及其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一旦获取了土地的支配权,就像掌握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一样,通过分配“土地”,对居民的资本收入进行再次分配,通过资本收入的跨个人转移将更多的社会财富移植到地方政府手中,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给自己印钞票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印钞之后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却因房产的购买者给消化掉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房价的高企。这就是中国不完整土地产权制度下出现的“土地货币”的独特现象,但是“土地货币”的发行者——地方政府——却是相对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也为不同地域的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土地货币”的定价权带来了差异相当大的激励机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县际之间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要是撇开不同地方政府制定有差异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说,其实这种县际竞争的本质是不同地方政府掌握了不同定价权的“土地货币”的激励机制。“土地货币”定价权的弹性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达程度与高层政府的政策支持程度。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对“土地货币”的流转频度很高,其价格也被抬升得很夸张。中心大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房价高得离谱,其实是这些地方的“土地货币”的价格奇高的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现象。
如果地方政府将“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转化成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后,购买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业主就等于购买了一种能够规避政府力量的避险工具,其实是把政府的“土地货币”变成了个人手上持有的“类货币”了。由此可见,土地问题在中国变得尤为复杂。问题也就来了,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而“土地银行”却能把这种发行权与定价权从政府手上逐渐地转移到银行身上去了。基于“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可能发生的转移,地方政府与“土地银行”之间就存在特别的矛盾之处:“土地银行”业务的拓展的确能够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带来高效率,却稀释了地方政府所掌握“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土地不完整产权制度的利益生态。如果四川省彭州市的那家“土地银行”的试点成功,那么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银行”的应用了。这种大面积的“土地银行”的推广将会很好地抑制地方政府提供巨大的“土地货币”供给,这对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遏制房价过快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据媒体报道,住建部也在某些场合公开承认了大量的土地闲置、房屋拆迁以及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不当使用土地或者不恰当的政策有关。要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货币”的发行权与定价权仍然具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么要让土地价格下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并且会增大个人投资者对土地及其房产的多重需求,一重投资的需求,一重规避政府力量的需求(避险的需求),另一重炫耀能力的需求。事实上,房产的多少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多元化的享受功能却正在削弱。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土地银行”时,不去深入研究土地在中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所承载的利益导向如何,直接去研究“土地银行”对土地流转的利用,特别是农村土地的利用,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就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变得更加迫在眉睫了,“二元经济”的结构亦正在撕裂社会的均衡发展。
五、结语
本文对“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银行”研究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其中很多结论还缺乏实证的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土地银行”才刚刚起步,既缺少现实的金融数据,又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就只能做些定性的表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三重大转型”,其中土地问题伴随着这“三重大转型”的全过程,而且这三种不同方向转型的叠合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领域的改革罕见地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土地问题,才能对中国的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地审视,才能提出真问题,去掉伪问题,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真实的源动力。
中国的“土地银行”问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问题,那就是金融中介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同时也通过金融服务为提供土地资源的人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机构所能想象的复杂。其复杂之处就在于土地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核心问题所在,也是各方利益博弈者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本文从很多独特的视角去关注土地及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来看待中国“土地银行”可能存在的问题。
文中所提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土地产权交易的最大的恶果是土地交易者的“败德行为”以及加深了“二元经济”的对立;不完整产权制度造成了比较混乱的“多中心主体”利益格局,在其土地产权资本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是弱化了土地产权最初拥有者的经济权利,反倒增强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经济权利,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土地货币”的超量供应固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有关,但很大程度上却是政府对土地定价权独占的衍生物,“土地银行”可以看作是抑制公权对“土地货币”的独占,扩大私权,增加“多中心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收入的救济性手段。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就是严重阻碍了土地资本化的进一步深化,也妨碍了“土地银行”业务的全方位拓展。当然了,要好好研究中国处于“三重大转型”下的土地及其土地银行问题,还需要更多有志于促进中国社会改良的仁人志士的加盟。
[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2006(2~3)
[2]吴介民、刘雅灵.什么是“中国模式”.台湾社会学杂志. 2009(12)
[3]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WorkingPaper.1999
[4]赫尔南多·德·索托(秘鲁).资本的秘密(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司马迁.西汉.史记.货殖列传.查阅网上图书馆资料所得
[6]刘正山.“土地银行”之考辨.中外房地产导报.2000(12)
[7]张五常.揭开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网易财经.2008年
[8]引言里面有关“土地银行”的综述来自网络资料的整理
Research of Land Bank under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Dual Economy”
CHEN Fei-xia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Guangdong,Guangzhou,510520
Land issue is the core of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From China's"dual economy"structure observation,studying land bank is a very significant issue.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dual partition could be easier to have a"moral hazard"for property transactions,and deepen the"dual economy"of the opposition.Incomplet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led to more confusion,appearing"multi-center subject"interest pattern,that is"weaken one,enhance the other"on economic rights,the result is that the low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s.While"land money"is the government monopoly on land pricing derivatives,by controlling the"land money"issue volume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revenue.But they are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the land of the deepening of capital,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xpansion of land banking.
Dual Economy;Land Bank;Property;Multi-center Subjects;Land Money
F83
A
陈飞翔,男,江西永新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中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场转型;长沙,41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