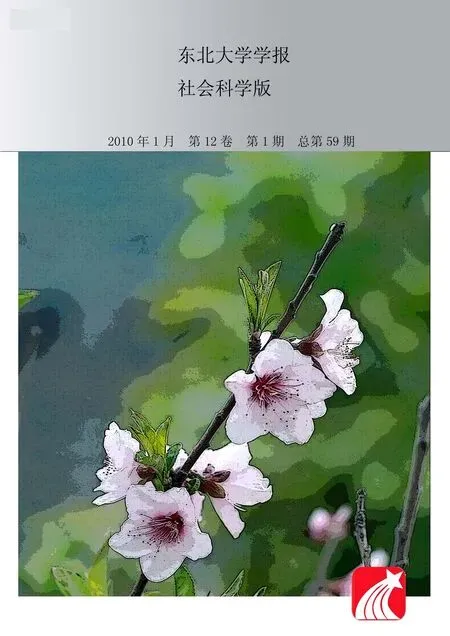改编的通俗性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2010-04-03原小平
原小平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一、 改编与文学经典化的关系
文学名著,尤其是文学经典,一直是改编的热点。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据统计,自电影诞生的1895年到1971年,世界上大约有450部电影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而成[1]1,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其他作家的作品难以企及的改编数量。中国文学以四大古典名著为代表的经典之作,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话剧、金庸的小说等,被改编的频率也相当高。比较而言,一般的文学作品,被改编的几率明显小得多。笔者曾对1935—1994年间所有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人拍摄的获得过世界大奖的电影作过统计,共有282部,其中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有46部,而这46部改编之作中,有36部可以被划为文学名著,也就是说,来源于名著的改编约占78.3%①以上四个数据,是根据张骏祥、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3—1443页)所提供的资料,统计得出的结果。,这个比例和我们日常的经验大体吻合:名著比一般文学作品更能吸引改编者。
改编基本上是由文字文本转变为表演艺术,由相对高雅的文学转变为更通俗的视觉艺术或口头艺术,呈现出一种经由改编者到改编本接受者的阶梯式接受过程。这个接受过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改编本的接受者,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感受原著的艺术魅力。当然,由于间接接受,原著的意蕴不可避免地有所流失和变异,这是其不足之处。不过,如果改编本很成功的话,可以有效避免原著精华过多流失。更重要的是,这种间接接受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通过改编,可以将文学名著最大限度地普及到普通人群之中去,甚至让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机会对名著有所了解----这正是文学改编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劳伦斯·奥立弗所言:“把莎士比亚的伟大舞台剧本搬上银幕是一种艺术上的妥协,但由于渴望看到这些剧本的精彩演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难偿宿愿,所以还是值得这样做的。”[1]106即使那些通俗文学作品,也需要改编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受众面。金庸小说的通俗性和受欢迎程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中,可以说绝无仅有。据199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称:“光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个亿。”[2]但对于动辄数亿的电视连续剧观众而言,金庸小说的读者,仍是一个相对小的群体。
接受美学认为,传播与接受是文学作品艺术生命史的一部分,没有读者的接受,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个摆在那儿恒定不变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存在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因此,读者的理解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3]。那么,对于经典性文学作品来讲,改编这种强有力的通俗性传播过程,会对原著产生什么影响呢?
最大的影响在原著经典性的建构方面,即对原著的经典化过程发生巨大影响。因为文学经典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拥有足够数量的不同时空中的读者,在于其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持久性。文学不是科学,科学的使命指向自然界,探索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注定了科学永远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精英才能理解和掌握的东西。文学的使命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理解主要靠直观把握和心灵顿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普通人对最深刻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都会有悠然神会之处。更重要的是,科学的价值在于改造自然的过程之中,而文学艺术,其价值显然就在读者的会心一笑和熏浸刺提之中。因此,我们固然不能说最通俗、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就是最经典的,但真正的文学经典必然有其通俗性的一面。如果一部文学经典总是以拒绝读者的姿态出现,那么,它的经典性就很可疑,至少其经典性还不够纯粹。宗白华曾论述:“人类第一流作家的文学或艺术,多半是所谓‘雅俗共赏’的。像荷马、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文艺,拉飞尔的绘画,莫扎特(Mozart)的音乐,李白、杜甫的诗歌,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说;不但是在文艺价值方面是属于第一流,就在读者及鉴赏者的数量方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为其它文艺作品所莫能及。这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当的‘通俗性’。不过它们的通俗性并不妨碍它们本身价值的伟大和风格的高尚,境界的深邃和思想的精微。所奇特的就是它们并不拒绝通俗,它们的普遍性,人间性造成它们作为人类的‘典型的文艺’(Classical Arts)。”[4]显然,宗白华所言的“典型的文艺”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文艺。从本质主义的观点来说,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它自身必然需要具有能够成为经典的潜质,这是经典的基础和内因。但一部潜在的经典最终成为经典,就需要传播和一定数量读者的认可,这是经典形成的外因。通过读者的公认,经典最终确立,才是作品经典化过程的彻底完成。
当然,某些改编尤其是颠覆式改编,有时会消解作品的经典性,这是一种逆向的经典化过程,也被称为去经典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影《大话西游》在中国大陆放映,虽然起初一度票房收入低迷,但是不久就受到了以大陆高校学生为主体的众多观众的热烈追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它标志着60年代起源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发生了实质性影响。后现代主义鼓励文化渎神,以消平深度、打破中心、拒绝权威、解构经典为特色。此后,“大话”“戏说”“水煮”类作品不断涌现,潮流所及,不仅四大古典名著遭到另类改编或改写,而且建国后的一批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当代名著,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也遭到低俗改编。200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红色经典” 低俗化改编热,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狠刹乱编乱改红色经典之风,所有“红色经典”电视剧要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这说明了颠覆式改编已经动摇了某些名著或经典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造成了很大不良影响,以至于国家相关部门认为只有通过行政的力量,才能遏制颠覆式改编对某些名著经典性的解构。这类改编对经典作品的冲击,还影响到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威力量),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对“经典”和“经典化”的热烈讨论。迄今为止,“经典”仍旧是文学理论界的热点之一。2005年5月27—30日在北京召开了“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来自欧美亚不同学术经历和民族背景的专家学者对“文学经典”展开了讨论,著名的荷兰学者杜卫·佛克马的开场白是:“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5]。可谓一语中的。文学研究对经典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流行的颠覆式改编,对文学经典的解构,已引起了知识界焦虑,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名著改编对文学经典化的巨大影响。
颠覆式改编主要是一种解构力量,缺乏建设性,在名著改编中,不是主流。主流的改编追求表现原著的精神实质,追求对原著的正面普及,因此,文学改编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建构,是一种促进的力量。一部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需要社会中所有阶层,即统治阶层、知识精英阶层、普通民众阶层的一致认可。其中,普通民众的认可是经典化最根本的力量。普通民众虽然艺术鉴赏力较弱,往往会受时尚的影响,但如果一部作品长久地被大众所喜爱,那么,一定已经不仅仅是时尚了,它至少已具备了可成为经典的特质。民间流行的文学,往往语言不够精粹,要进一步成为经典,还往往需要知识精英的参与、润色,需要文化权威的承认和最终定位,所以经典化往往是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合谋的过程。经典的通俗与高雅的特性,也由此生成。统治阶层往往是从政治而非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他们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多是基于利用和权宜之计。因此,虽然在特定的时段,政治因素会对某些文学作品经典化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影响,但长远来看,政治对经典化的影响是微弱的、可以忽略的。建国后,鲁迅、郭沫若、茅盾,曾被确立为文艺战线上的三面旗帜,但仅几十年时间,郭沫若许多作品的经典性,已不大被人们承认,茅盾作品的经典性也不断引起人们质疑,即使鲁迅的作品,人们对其经典意义的理解也和“十七年” 、“文革”时期大不一样。从来没有哪一部真正的经典是靠政治权力来确立的。有人曾认为鲁迅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主要是由于政治的神化,然而,在鲁迅早已走下神坛的今日,2003年6月由新浪网与国内17家强势媒体共同组织的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动----结果显示:鲁迅仍是最受人们推崇的作家(其次分别为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这说明,鲁迅作品具有真正的经典意义,它们和政治的提倡与否,关系并不大。
由于文学作品经典化主要是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的互动过程,那么联系着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文学改编就成了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并由此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这在文学经典的生成和确立阶段都有明显体现。
二、 改编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中外许多文学经典在创作前,往往在民间有一个曾长期流传的“本事”或曰相似的故事,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根据意大利民间故事写成的一部爱情悲剧,《李尔王》则取材于古代英国的历史传说。歌德的《浮士德》的内容,来源于德国16世纪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我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成书之前,也都有一个在民间长期流传演进的过程。凡能在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不论多么粗糙,一定具有某些超越性的意蕴和突出的原型意味,具有经典性的内核。这种内核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得到强化,并最终会为经典作品的创作铺平道路。《水浒传》、《三国演义》在作者署名中强调“编次”,正说明了成书前民间流传的故事对这两部经典的奠基之功。民间故事的流传形式,一是口头文学(或根据口头文学记录下来的一些文本,如中国宋代的话本就是当时民间艺术“说话”的底本),二是表演性的演出(如中国的戏曲)。两者往往先后产生,相互影响,关系密切,后者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对前者的改编。王国维在论述宋元戏曲和“说话”的关系时就说:“此种说话,以叙事为主,……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6]显然,被改编成表演性艺术的内容,只能是民间故事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一般来讲,还应该是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也就是说,改编本身就是一个对民间口头文学的选择(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生发),使其更加经典化的一个过程。这些戏曲的内容往往会被后来的经典作品所吸收,成为其核心部分。
典型的例子是元代大量的“水浒戏”和《水浒传》创作的关系。关于宋江对抗朝廷的事迹,早在南宋已有民间流传。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自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7]96这说明了南宋“水浒故事”虽内容引人注目(“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但形式还很简陋(“街谈巷语,不足采著”)。元代汉民地位低下,强烈呼唤宋江之类的英雄豪杰,以解倒悬。加上元代长期废除科举,大量读书人流落下层,他们就把南宋以来的“水浒故事”大量改编为当时异样发达的杂剧。仅元初戏曲家高文秀一人创作的水浒戏,就达8种。这些被改编成的水浒戏,至少在三个方面,为《水浒传》的出现做了准备:第一,对南宋“水浒故事”中的英雄形象进一步强化。据《大宋宣和遗事》可知,南宋“水浒故事”主要叙述的是四件事:杨志卖刀、劫生辰纲、宋江杀惜、征方腊。其中人物主要是“盗寇强人”形象。在元代水浒戏中,梁山好汉宣称“替天行道”,所为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事,这就使得南宋故事中的水浒“强寇”具有了解人危难的江湖侠士身份。侠士化的草莽英雄,不但形象更为丰满,还和流传在中国底层的传统墨家文化中的游侠文化对接起来了,从而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为《水浒传》的经典性作了进一步铺垫。第二,语言具有了精练文雅的特色。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通俗化并不是粗俗化,真正的通俗化也需要文从字顺和适当的文采,需要民间文人的参与。由于下层文人的参与改编,元代还出现了像《梁山泊黑旋风负荆》这样的杂剧精品。语言艺术上的提高,自然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条件,这也增强了水浒故事的艺术魅力,扩大了它的流传范围。同时,这也会吸引更多更有才华的文人关注并进一步参与《水浒传》的经典化过程。第三,元代杂剧繁盛,而当时大约平均每上演20个杂剧,其中就有一个是水浒戏[注]现存元代杂剧剧目约530多种(见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其中水浒戏约25种(见陈建平著《水浒戏与中国侠文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页)。。这一方面进一步普及了水浒故事,另一方面在改编者和民间观众的互动中进一步塑造了典型的水浒英雄形象。如李逵的形象,在宋代“水浒故事”中并不突出,但在元代有关李逵的水浒戏数量最多。李逵后来成为《水浒传》中最为金圣叹所称道的人物形象,元代水浒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郑振铎曾分析说元代的水浒戏创作:“是跟了当时的民间嗜好而走去的。民间喜看李逵戏,作者便多写李逵,……至于其他很可取为剧材的‘水浒故事’,他们却不大肯过问了。”[7]103在元代水浒戏中,李逵天真快乐、疾恶如仇、勇猛鲁莽,是个可爱的人物形象,并没有后来《水浒传》中描述的抡着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的嗜杀倾向。武松打虎的故事在元杂剧中也都有表现,而这在作为南宋说话人底本提纲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却没有提到。
由南宋水浒故事改编的元杂剧,在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所具有的艺术成就,都成为了后来《水浒传》创作的重要资源,《水浒传》中的一些章节内容,和元代的水浒戏在情节和人物上基本雷同,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另外,长期民间流传,使《水浒传》天然具有很强的通俗性,这也是那些纯粹由文人创作的文学经典所难以做到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水浒传》类似,经典化都经历世代累积和孕育,其间曾有大量三国戏和西游戏的改编和流传。世代累积型的经典一旦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创作成型,凭借其长期形成的高度艺术成就和巨大社会影响力,最终被知识精英阶层接受并被文化权威赋予经典地位,就是顺理成章、或早或晚的事了。
三、 改编与文学经典的确立
世代累积型经典基本产生在古代社会,因为当时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不受文人重视,少有文人从事此类创作。封建社会后期,文人独创型经典才逐渐增多,《金瓶梅》、《红楼梦》是其中的代表。晚清以来,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逐渐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中心地位,受到文人重视,越来越多的文人积极地投身其中,其后的文学经典几乎都属于文人独创。文人独创型经典,在被社会接受前,只是潜在的经典,如果没能得到流传,是不能视为经典的。如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虽已完稿,但毁于战火,不可复见。根据老舍对其内容的描述和由《大明湖》改写的中篇《月牙儿》来分析,这个在《骆驼祥子》前创作的小说,很可能是堪与《骆驼祥子》相媲美的经典之作,但现在谁会说《大明湖》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呢?因此,近代以来,作品完成后能否广泛流传,就成了其经典化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文人独创的文学经典,在现当代也有通俗和严肃、娱乐性和启蒙性之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拥有文学欣赏能力、机会和闲暇的人比例很小,所以即使现当代文学中那些最通俗的作品,从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小说,再到建国后的“红色经典”、港台金庸和琼瑶的小说,它们以纸质文本形式流传的范围,主要还在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中学生以上)之间。由于这种流传方式缺少民间普通民众的互动,有时候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巨大干扰,由此形成的所谓现当代文学经典,实际上经典化往往并不充分(缺少民间的认同),导致它们的经典性常常相当暧昧,往往游移不定。有些作品曾在某些阶段被奉为经典(如“红色经典”、“样板戏”),现在看来是名不副实的。也有些作品,曾长期受到批判和冷落(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穆旦的诗歌),现在看来它们又极具经典意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些作品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普及到民间,民间的失语使得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地位相当脆弱,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玩偶。真正根植于民间的经典(像《水浒传》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但在当时显然仍被视为经典之作),是任何外在力量都难以动摇的。现当代文学名著中有些作品,因为特殊机缘而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曾被改编为电影《小二黑结婚》和《李双双》,在普通民众中产生过很大影响----这当然也证明了原著具有相当的经典性,因此它们的经典地位就相对牢固些。尤其是《李双双小传》,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不足很明显,但所有的当代文学史都无法将它绕过,甚至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还对它和电影《李双双》进行了专节的对比分析。显然,电影《李双双》对小说原著的经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使得原著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艺术和内容上都对原著有所升华(人们公认电影《李双双》比原著艺术成就为高)。
影视改编对金庸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1962年前,金庸尽管已创作出《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射雕英雄传》(1957)、《神雕侠侣》(1959)、《雪山飞狐》(1959)、《飞狐外传》(1960)、《倚天屠龙记》(1961)、《鸳鸯刀》(1961)、《白马啸西风》(1961),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还远达不到洛阳纸贵的地步。纸质文本对金庸小说传播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60年代前期,是电影改编金庸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注]参见林保淳《解构金庸》,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1958年到1994年间,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共49部,其间有三个改编高峰。一是1960—1965年间,二是1977—1984年间,三是1990—1994年间,三个时期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数量分别为15部、15部、14部,共计44部。,其后,金庸小说在香港的流行面才迅速扩大,金庸当时“大量的小说读者是由电影观众转变而成的”[8]。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接受史,情形也类似。1985年金庸小说在大陆流行,受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热播影响明显。有研究者对此考察后曾说:“不能忽视的是金庸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热播,也反过来促进了金庸小说的销量,几乎达到一纸风行的地步。”[9]
正是金庸小说的大面积流行,才使得一些大陆的文学研究者,逐渐开始深入思考“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新文学批评和排斥的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钱理群曾表示:“说起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的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10]相似的意思严家炎、陈平原都表达过。严家炎在其专著《金庸小说论稿》开头,先列举了金庸小说作为“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的四个特点:“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很大”、“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这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他的研究源于金庸小说的流行。此后,大陆文学研究者对金庸小说研究不断深入,其经典性逐渐被知识精英阶层所认识和接受,金庸小说才在90年代被确立为文学经典。
严肃的启蒙性新文学经典,改编数量也相当可观。据统计,到2007年为止,鲁迅小说的戏剧、影视、连环画改编本至少有38种之多[注]根据葛涛的《鲁迅文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中所列的改编情况统计。;巴金的小说《家》改编至少有33次[注]根据李存光的《〈家〉〈春〉〈秋〉版本图录·研究索引》(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中所列改编情况统计。。还有论者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老舍是迄今为止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而且质量最高的一位。”并称之为“老舍现象”[11]。这个论断不一定精确,但老舍的作品被大量改编则是事实。沈从文的作品,一方面解放后长期在大陆被禁,另一方面由于故事性不强,被改编的条件比较欠缺,即使如此,小说《边城》仍有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出现的两个改编电影。从改编的频繁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某一部作品受到的推崇程度----那些经典性最强的作品才容易受到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文人重视,从而获得较大数量的改编。从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人作品的被改编数量来看,不仅他们的总体改编数量突出(当然由于各自作品风格的差异,他们作品的改编数量也并不平衡),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最经典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比他们的其他作品改编频率要高的多。如鲁迅小说中改编数量最多的是《阿Q正传》,至今各类改编约有20种,而《祝福》虽说在鲁迅小说中改编数量处于第二位,却只有约8种改编本。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家》的改编本约有33种,数量最多,而《春》和《秋》的改编数量在巴金的所有小说中,虽仅次于《家》,却各自只有6种改编本。此类现象,也可以在老舍、茅盾、沈从文的小说改编中得到印证。一部作品的每一次改编,都是改编者对它的一次肯定,它连续地在不同时代获得改编,就是不断得到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的肯定。这不断被肯定的过程,就是作品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改编由此促进了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四、 结 语
当然,应该看到改编只是经典普及和名著经典化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能将其夸大和绝对化。对于不同题材的经典,改编参与名著经典化过程的程度并不相同,如影视改编对叙事性的小说和戏剧更方便些,改编散文和诗歌就困难些。因此,改编对散文和诗歌的传播和经典化作用,显然并不明显。尽管如此,由于真正的文学经典,民间性是其应有之义,而改编作为通俗性传播方式、一个普及经典的方便桥梁,就和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种种关系。因此,改编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中一个永远难以绕开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罗吉·曼威尔. 莎士比亚与电影[M]. 史正,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2]张琦. 金庸在西方[N]. 文艺报, 1997-01-28(3).
[3]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87.
[4]宗白华. 常人欣赏文艺的形式[M]∥艺境.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75.
[5]杜卫·佛克马. 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M]∥童庆炳,陶东风.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7.
[6]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6:40.
[7]郑振铎. 水浒传的演化[M]∥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8]宋伟杰. 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40.
[9]李云. 迈向“经典”的途径----“金庸小说热”在大陆:1976—1999[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1(3):1-8.
[10]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2.
[11]高思新,朱杰. 传媒时代的经典----老舍作品的影视剧改编[J]. 理论月刊, 2005(10):14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