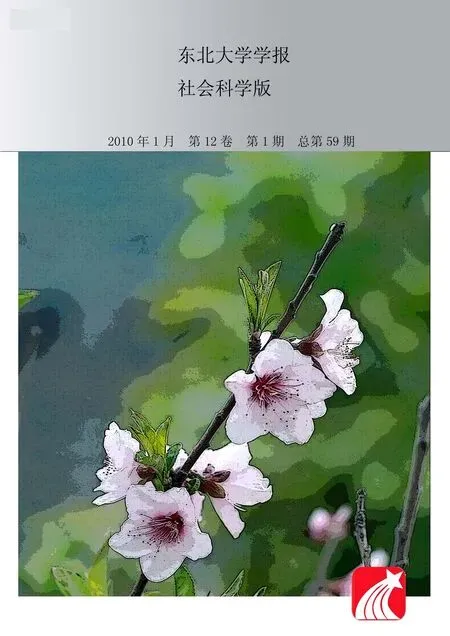市民社会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基于近现代历史的考察
2010-04-03王文奇
王文奇
(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12)
一、市民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选取与界定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最初是表示社会和国家的一个一般术语,与‘政治社会’同义;后来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1]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市民社会的多重含义,但是不够确切和详尽。
市民社会的最初含义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阐释的市民社会即为城邦,也就是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文明社会。此后,市民社会的含义经过了三次发展变革。第一次发展变革的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的兴起。在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中,认为在人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社会诞生之前存在着自然状态,按照洛克的看法,自然状态本质上是和平的,但是仍然有缺陷,如缺少公允的仲裁者来维持正义等,于是人们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这便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原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2]。在洛克那里,市民社会就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基本等同于国家。
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二次发展,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完成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这里的市民社会不再与自然状态相对立,而是产生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相分离的二分法,并且基本上等同于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在现代进行了第三次蜕变,产生出了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在这种三分法中,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共领域是开放性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在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在集会、结社自由以及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交谈时,他们便是以一个公共团体的身份在活动,就缔造出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曾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4]。
诚如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种市民社会的界定都有其时代背景在内。尽管对市民社会的阐述不同,背后的市民社会精神却是一致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和目的都在于通过市民社会治理当时的社会,促成人的天赋权力的实现,促成人的自由发展,使社会趋向于善和正义。可以说,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市民社会的外延,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市民社会精神。
本文考察的是近现代历史,因此,本文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是:市民社会是处于政治权力控制之下的民众,为了民众自身或人类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首先为促进自身合理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为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而组成的集团、组织及其所采取的行动。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目标是摆脱超经济强制,求得民众自身的经济自由及发展,这是人的基本权力,也是社会得以合理发展的前提;第二阶段目标是在第一阶段目标实现的基础上,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努力。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界定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国际体系。所谓国际体系,一般是指由彼此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的一个整体。“国际体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们的活动总是会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可以被称为系统。”[5]
国际体系最早是行为主义者的核心概念。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将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系统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发了“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莫顿·卡普兰在其《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中,按照一体化的程度进行排列,区分出六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系统[6],也就是国际体系。
行为主义学派的这种体系分析方法,被后来居上的其他学派相继吸收。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将系统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结构是系统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才可能设想单元组成一个体系,而不同于简单的集合。在另一个层次上,系统包括互动的单元。”[7]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基欧汉也重视系统分析,“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异军突起。同样,温特也是从国际体系入手进行研究的。“国家很少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大多数国家置身于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之中,体系影响到国家的行为。”[9]
但是,真正对国际体系作历史性分析的,要数英国学派。而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所创建的国际体系理论对于我们来说最有裨益。这是一种真正重视历史,在史实的基础之上提升出的一种国际体系研究方法,而此前的体系理论在从理论转向实践方面存在着困难。作者开篇就指出:“我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以来350年间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主流国际关系学通常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国际体系起源的标志。”[10]1正是这种历史视角的考察,使我们能够将国际体系与市民社会结合起来进行探究,发现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在本文中,笔者将运用到《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最常用的分析层次----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单位、次单位、个体,主要分析部门----军事部门、政治部门、经济部门、社会或文化部门、环境部门,体系类型----完全国际体系(这些国际体系通常包括套叠的所有部门的全部范围)、经济国际体系(这些体系缺乏军事—政治互动,但它们通常体现了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前国际体系(这些体系主要由社会—文化互动构成,尽管体系中也许包含着非商业贸易的成分)。
二、市民社会的变迁与国际体系的演进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1]当世界历史推进到1500年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并存着几个不同的国际体系。但是由于物质技术的限制,各个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能力很弱。“在陆上,欧亚大陆的物质技术取决于车轮的发明,适于牵拉、驮载和骑乘动物的驯化以及道路的拓展,还有快马传驿制度。在水上,则依靠发展真正的轮船(与木筏相对)、帆船、航海技术知识和港口。”[10]170各个国际体系间尚未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政治军事联系也无从谈起,因此各个国际体系还处于相对隔绝、各自发展的状态。在一些前现代国际体系内根本就不存在着市民社会形态。即便在市民社会发展较早的欧洲国际体系中,市民社会也只是局限于各个政治实体的内部,如果按照层次分析,市民社会则处于个体或者次单位的层次上,它们为了实现民众的自由经济,摆脱超经济强制在艰难抗争,没有走向跨国联合,也就无法在体系层次上发挥作用;而且市民社会的运作也只是在经济部门中展开,处于市民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社会。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市民社会在欧洲体系内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促成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经济联系和交往的范围扩大,不再仅仅是欧洲体系内各国间简单而松散的贸易,如今因为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欧洲的跨国经济联系变得频繁而密切,并且商业往来也跨出了欧洲的大门,走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市民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当时所处的状态,由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人们的海外贸易往往受到一些政治权势的制约、盘剥,也遭受着海盗的侵袭,而无法要求国家来为自己做主。于是,市民社会就处在了对抗国家的立场上,呼唤着国家的变革。市民社会的这种诉求恰恰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也迎合了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加强自身力量、摆脱外来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干涉的要求,于是市民社会的诉求推动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同时绝对主义国家靠着支持大航海、海外殖民地的扩展,进一步掠夺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进一步满足着市民们的愿望,也刺激了市民们的欲望。
此时,一方面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成了国际体系主体中的主流;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也挤压着甚至毁灭了一些原本与欧洲体系共生的国际体系,世界的权力中心向欧洲偏移。这样,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处在个体或者次单位层次上的欧洲市民社会,推动了欧洲国际体系内单位的变化,单位的变化进一步改变了欧洲的国际体系甚至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体系。恰如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市民社会这时还只是停留在国家政权内部,但是市民社会促成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却产生了体系层面的影响。
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虽然保证和促进了市民们对财富的渴望,但并没有促成市民社会的立刻深化。因为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存在,使人们不必在国内继续与王权争夺空间、维护私有财产,他们可以通过组织船队和跨国公司,踏上美洲、非洲、亚洲,或者挖掘黄金白银,或者贩卖黑人奴隶,或者运输香料,就能满足自己的经济欲求。如果说,这一时期市民社会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当17世纪来临时,各国公司的出现。如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有政府的资金和军队参与在内,但它们的目的始终以经济为主,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依附着公司,公司成了脱离政府超经济强制的典范。
但很快绝对主义国家的弊端显现出来。在欧洲各国国内的经济和自由市场得不到深入扩展时,强大的王权在最初疯狂殖民后,又将手伸向市民的口袋。市民社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是要与绝对主义国家相抗衡,争夺自己的经济空间。市民们起来反抗,他们要彻底摆脱超经济强制,他们要摆脱强大的王权专政,于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英国开始,在欧洲相继爆发。英国“1688年的革命,算是教训了王室,告诫它不要干预地方政府的事情。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一度想夺取政权:装货马车的赶车人、皮革商人和屠户的子孙,都出现于统治者的行列”,“财产权的神圣代替了君权的神圣”[12]。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彻底摆脱了超经济强制,实现了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引领了市民社会第一阶段的完成。
此后,在欧洲,一些有识之士或团体、媒体等看到社会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也看到了商业社会的弊端,他们开始或批判或讽刺商业社会的阴暗面,以引起人们的警觉,开始向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迈进。1711年在英国创刊的报纸《观察报》就试图提升社会的道德标准。市民社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进一步扩展,从单纯的经济部门转向社会文化部门,市民社会由摆脱超经济强制为主、其他方面为辅的抗争,转变到以批判社会本身、治理社会为主了。市民社会从这一时期开始强调人权、平等、正义,强调普世价值,一方面处在制衡国家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又处在规约社会的立场上。欧洲的市民社会在国际合作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最初的经济合作到此时舆论的合作、协会团体的合作和定期会议等形式,使市民社会所能关涉的地理范围实现共通,也使市民社会所关涉的方面、对象实现了扩展和深化。
但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欧洲的市民社会深入发展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市民社会形态还处在漫长的初级阶段。随着欧洲列强殖民程度的加深,亚洲、非洲和美洲原来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被纳入欧洲体系,一些原本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力量微弱的地区,逐渐诞生了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得到壮大。这种被殖民者催生壮大的市民社会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作为对列强挑战的回应,殖民地人民意识到自身处于被压制、被剥削的状态,对这种状态极端不满,从而结成市民社会团体,通过舆论、游行、罢工等活动,为了自身的权益而抗争。另一种形态是在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殖民宗主国的移民来到殖民地,他们把市民社会精神带给当地的土著民,在移民的领导下,反对殖民当局的市民社会诞生了,例如,莫桑比克白人农民联盟就曾向政府施加压力,创设公开招股的公司,如谷物市场联会和奶制品联会[13]。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殖民地的第一种市民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最终转化为民族主义,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完成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
民族主义浪潮从北美大陆发端,影响波及到欧洲,与反绝对主义国家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成就了大革命。市民社会在殖民地的发展,再度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了欧洲列强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国际体系的单位迅速增加,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国际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市民社会的跨国运动也越来越频繁,以往只是在欧洲范围内展开的各市民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现在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市民社会已然从最初的个体或者次单位层次,跃进到单位甚至体系层次上来,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民社会组织虽然在单位和体系层次上运作,但是相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却显得弱小,需要通过传导效应影响到主权国家的行为。
市民社会真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是在二战以后,市民社会组织也成了国际体系的主体之一,市民社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既包括地理范围的扩大(如从个别国家内部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范围),也包括关注领域的扩大(如最初是经济等简单的几个方面,现在市民社会的关注则是非常广泛,包括人权、环境污染、妇女地位、核武器扩散等等问题)。市民社会组织的行动影响能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部门。此时,市民社会综合发挥了制衡国家、参与国家、与国家互补等作用。除此之外,市民社会还对跨国公司的举动进行着监督和批判,市民社会组织也就因此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
三、 全球体系与全球市民社会
我们置身在全球化时代,这已经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二战后,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空前增强,尤其是随着电讯业的现代化和网络的普及,更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联系,“地球村”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时代,国际体系也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各个殖民帝国已经无力再统治殖民地,196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布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14],使主权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与此同时,国际体系的单位正在增加,在主权国家之外,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甚至也可以跻身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单位,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一些弱小国家来说更加强大,早在1998年世界经济和跨国公司100强的排名中,通用汽车居第24位,花旗集团居第56位,大众汽车居第57位,西门子居第64位[15]。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具备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特征,形成了强大的权力实体[16],同时,非政府组织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论者称“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迄今为止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形成一个由包含主权国家在内的多元性主体构成并具有世界规模的复合性政治框架,即全球体系”。这样一个全球体系也就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完全国际体系,在该体系中,无论层次上还是单位上的界线都越来越被彼此的互动和影响所模糊。在全球体系中,“蝴蝶效应”日益明显。
但全球体系并不代表着和平与和谐,在全球体系中,有些国家努力获得核武器,产生了核危机;有些国家出于自身目的,违背国际法,避开联合国发动地区性战争;而有些大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倾倒有毒垃圾。恰恰因为“蝴蝶效应”的明显加强,使得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这时,全球市民社会就担当了治理者的角色。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跨国家‘市民社会’正呈现出生机,目睹了种种旨在推动和平、人权、环境和社会改革的社会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17]这个新的跨国家的市民社会就是全球市民社会。当然,全球市民社会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各个团体建立起了跨越国家边界的战略联合,还在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关注焦点是跨国性问题”[18]。
由于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市民社会,在全球议题上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关于发展、人权和环保议题,他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国际政治。例如自二战结束以来,非政府组织就一直在持续地强化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同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展开合作,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展开合作。“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就一直在游说各国执行更加严格的人权保护标准。它们为人权设置的定义具有更广泛的专指性,通过公布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例和掀起国际声讨运动,敦促各国鉴别和惩罚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这些努力对于各国的行为以及进一步建立尊重人权的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府统治的权力往往是由上而下的,通过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力向度是多元相互的而非单一的或由上而下的。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而充满灵活性和适应性。
面对着大型跨国公司具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跨国公司单纯为了商业利益而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全球市民社会也把矛头指向一些跨国公司,对跨国公司的不合理行为进行抗议或者舆论施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管理有害废物国际贸易的《巴塞尔公约》中有一处漏洞,从而使公司在进行有毒废物贸易时能够避开禁令,“绿色和平运动”曾致力于将国际谈判的注意力集中到《巴塞尔公约》的这一条上。2006年8月下旬,荷兰托克公司租用的货轮通过代理公司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10多处地方倾倒了数百吨有毒工业垃圾,引发严重环境污染。托克公司虽然提前向科方通报了垃圾的剧毒性,但并没有遵守《巴塞尔公约》关于处理危险垃圾的相关规定,同时忽视了科特迪瓦在处理这些垃圾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科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事件造成10人死亡,另有超过10万人次因呼吸障碍或其他不良反应到医院就诊。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在揭露该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这些非政府组织成员还不顾危险,前往科特迪瓦与当地的政府和民众一起参与对托克公司的施压和对有毒垃圾的治理。
全球体系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关系就这样处在了共生又共同制约的地位上。全球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全球市民社会的出现又进一步推进了全球体系各层次和各部门之间的融通。另一方面,在全球体系中,主权国家、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都成为了体系的主体,但是前二者的影响力和能够动用的直接资源要远远超过后者,因此对后者的地位进行着挤压;同时全球市民社会又对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进行着批判和规约,尽管有时力量微弱,但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特色,也是较之前市民社会的一大进步,能够直接在体系层面对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施加影响。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先是追求摆脱超经济强制,进而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早期,市民处于政治体内部,但是其摆脱超经济强制的诉求也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国际体系的扩展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市民社会在一步步壮大,其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影响能力也在提升。二战后,随着全球体系的成型,市民社会组织成为全球体系的主体之一,对于促进完全国际体系的良性发展和对全球治理都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正来.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125.
[2]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78.
[3]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30-131.
[4]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序言29.
[5]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阎学通,陈寒溪,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11.
[6]莫顿·卡普兰. 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M]. 薄智跃,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9:21.
[7]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53.
[8]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 苏长河,信强,何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29.
[9]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2.
[10]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M]. 刘德斌,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1]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3.
[12]戴维·罗伯兹. 英国史:1688年至今[M]. 鲁光桓,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15.
[13]Makumbe J M. Is There a Civil Society in Afric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74(2):306.
[14]王铁涯,田如萱. 国际法资料选编[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2:11.
[15]阿兰·鲁格曼. 全球化的终结[M]. 常志霄,沈群红,熊义志,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1:72.
[16]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242-251.
[17]米歇尔·曼. 全球化是否终结了民族国家[M]∥俞可平. 全球化:全球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13.
[18]Turner S. Global Civil Society, Anarchy and Governance: Assessing an Emerging Paradigm[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8,3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