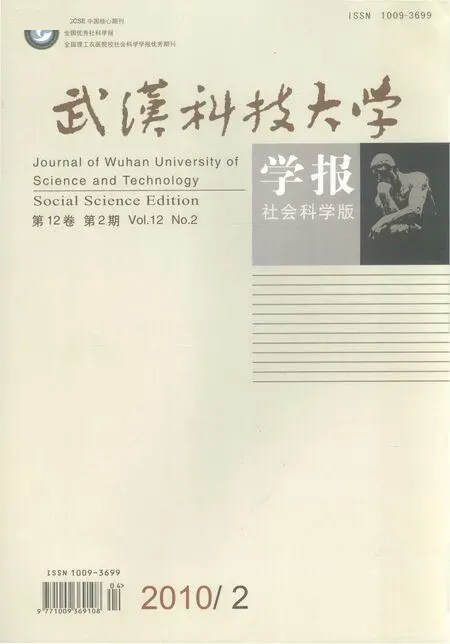重审《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共相能否在“辨证”中吞没感性?
2010-03-21刘贵祥
刘贵祥
(1.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2.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马克思曾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从“感性确定性:这一个和意谓”的辩证分析入手开始哲学的精神之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开端的开端”和“秘密的秘密”。可见,重新考查《精神现象学》的开端,辨明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探求黑格尔哲学的隐性立场和基本倾向,并呈现黑格尔哲学在他的批判者和现代哲学参照下的得失意义重大。
一、《逻辑学》开端与《精神现象学》开端的比较
黑格尔哲学体系以《逻辑学》为开端。《逻辑学》则以“纯有”为开端。“有”、“无”、“变”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第一个三段式,也构成黑格尔哲学大厦的第一块砖。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纯有”是什么,为什么要以“纯有”为开端,哲学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争论,但是不管这些观点差别多大,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逻辑学》必须从最纯粹和最普遍的东西开始。在《逻辑学》中,“纯有”即是纯思维,哲学必须以纯思维为对象和开端,并且必须要摆脱一切历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1]。可见,“纯有”作为《逻辑学》的开端,它同时也是《逻辑学》中所出现的第一个绝对知识,它必须要上升到纯粹思维的层次并摆脱一切“历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才能够探讨“存在”这样的哲学问题。
和逻辑学不同,《精神现象学》以“感性确定性”为开端。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得很明白:“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的或者现存着的东西的知识。我们对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知识,必须只像它所呈现给我们的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2]63这种不夹杂概念把握的认识就是感性确定性。感性确定性的德文表达是“ die sinnliche Gewissheit”,英文的表达是“sense-certainty”,汉语的翻译是“感性确定性”。需要指出的是,感性确定性的表达在汉语中极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黑格尔要肯定的是感性本身的“确定性”,但是黑格尔的意图恰好相反,他认为感性虽然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知识的真理不在感性的易变性本身,而在如何用共相把它固定下来这一点上。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die sinnli-che Gewissheit”应译为“感性的确知”,而不是感性确定性[3],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再以英文的表达为例,黑格尔要表达的这层意思同样也是很明显的。如Donald Phillip Verene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言》一文中就指出,黑格尔“sense-certainty”的含义“不仅是指有一个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如何被确知”[4]。英语对“die sinnliche Gewissheit”的翻译在这里虽然也是二手语言,但是它表达“感性如何被确知”这一点上比汉语贴近得多。当然,本文仍然仅限于突出这一含义,这一术语的使用仍然沿用“感性确定性”。
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基本定位是“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而对《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定位则是“意识的经验科学”。意识的经验科学目的是探讨真正的知识,“这部《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产生科学的因素,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2]1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黑格尔探求的真正目的是概念的认识,因为只有概念的认识才算得上真正的知识。但要达到概念认识,不经历艰苦而漫长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当然,《逻辑学》没有这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的探索,也无法真正开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以伟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的。
概而言之,《精神现象学》的末端构成《逻辑学》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认为,为了讨论纯存在,《逻辑学》的这个前提是应该忘记的。至少应该忘记精神现象的这种意识的经验形式,而让它里面孕育出来这种绝对知识以纯粹的方式不受束缚地发展起来。“彷佛一切过去的东西对于它来说都已经丧失净尽,而且视乎它从以前各个精神的经验中什么也都没学习到”[5]。显然,在知识论的传统中,从追求思维的纯粹性这一点上来说,黑格尔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问题是黑格尔为了“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想要完全忘记纯粹概念粗糙的出生地,这一做法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的抽象意识虽然和最初的感性意识不同,但是感性意识作为抽象意识的真正发源地,抽象意识不可能完全脱离感性意识独立存在,而且感性意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还具有各种发展的多重向度,不能完全被抽象的理性思维所吞没。但是,众所周知,黑格尔却在随后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中,最终用“纯粹思维”把感性意识完全清洗和吞没了。黑格尔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总体上说,这正是黑格尔思维辩证法的秘密。
所以,若把《逻辑学》的开端与《精神现象学》的开端作一比较,前者从“纯有”开始,后者从“感性确定性”开始只是表面的不同,实质上二者在思维方式的运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逻辑学》的开端更纯粹,而《精神现象学》不得不从“感性确定性”开始。这样一来,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就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秘密。
二、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及其隐性立场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描述出了个体意识由感性确定性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最终把意谓完全纳入了共相。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方法蕴含着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黑格尔正是在思维的“辩证”中用共相把意谓最终吞没。可以说《精神现象学》的开端运用的方法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小公分母”。黑格尔完成这一点通过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让考察对象和考察尺度合一
现象学以意识发展史为考察对象,但考察尺度本身又是意识发展史完成了的结果,即绝对精神(实质上还是意识本身)。这样考察对象即是考察尺度,差别只是这个考察对象有待展开自身而已。“感性确定性的这种具体内容使得它立刻显得好像是最丰富的知识,甚至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知识……此外感性确定性又好像是最真实的知识;因为它对于对象还没有省略掉任何东西,而让对象整个地、完整地呈现在它面前。但是,事实上,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它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么多:它存在着。而它的真理性仅仅包含着事情的存在”[2]63。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黑格尔可以把“感性确定性”当成“纯存在”,但这个“纯存在”并不具有什么独立自存的意义,它一定会被更高层次的知识所代替。所以,感性的确定性最终要被理性的确定性所代替,直到感性确定性发展出绝对知识为止,就此而言,感性确定性是确证意识发展的一个环节。因此,总观《精神现象学》的目的,表面上看,黑格尔对人类意识发展史在作完全客观的描述,实质上黑格尔的描述已经先以人类普遍意识的发展程度为前提了。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开端的影子。事实上正像前面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精神现象学》中以萌芽和潜能的方式,包含了他后来整个体系抽象思维的原型。“感性确定性”正是《逻辑学》中“纯有”的影子和原型。这是黑格尔将哲学的开端理解为圆圈的必然结果。《逻辑学》的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在思维内部“永不停息的循环”,它本质上是由近代意识哲学这个隐性立场提供的。差别只在于,《精神现象学》走的是上升的道路,用的是分析的办法;《逻辑学》走的是下降的道路,用的是综合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现象学》一方面被看作一条达到真正科学的道路,一个‘纯粹知识’的形成过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已经完成的‘绝对知识’在回忆它自身走过的历程”[6]175,这个历程本质上就是感性确定性被完全纳入认识共相的过程。
(二)用抽象思维冒充感性,然后用共相吞没意谓
黑格尔实现这一点通过两个步骤。第一,把《精神现象学》的走完全程后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实体化,即变为绝对精神。这一点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只不过感性确定性作为思维的萌芽,它作为最直接、最抽象的真理性还有待展开自身为共相。“被宣称为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的这种纯有,如果我们试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这种纯有中还包含着更多的别的东西……即在这种直接感性确定性里纯有立刻就分裂为前面已提到的两个‘这一个’:作为自我的这一个和作为对象的这一个”[2]64。这句话中的“我们”相当重要。黑格尔考察的对象是意识的发展史,尤其是个人意识的发展史,那么,考察尺度只有在意识发展走完它的全程时才能出现。但是,现在在这里意识发展史尚待展开,却已经先行出现了“我们”这个先在的思想尺度。那么这个先在的思想尺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无人身的抽象思维本身,即马克思所言:“举止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这整个观念,无非始终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7]334这个“无脸、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抽象思维”,可见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所在。第二,绝对精神在反观自己的来历中,把感性和感性的对象分割开来,让主体和思维分离。这样,最初作为实实在在的感性确定性就失去了对象,只有脱去对象这一杂质的束缚,感性才可能上升到绝对精神。黑格尔正是借助这个抽象的普遍意识,他才能把感性确定性看作是“自我”这一个和“对象”这一个的对立。可见这个冒名为“我们”的普遍思维其实正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个绝对观念作为思维着的精神,“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也就是说:“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7]328这样一来,感性、意谓就被完全纳入共相。感性和意谓一旦被纳入共相本身,黑格尔就可以任他的理性思维之马自由驰骋。本来,感性确定性作为意谓,是人和世界上手时的源初状态,它是“前逻辑的”。但是,当感性确定性被看作是还有待上升和展开的抽象性和直接性时,感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及意谓的不可表达性被狭窄化。它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从感性确定性上升为共相和普遍性。这样,当感性确定性走完全程反观自身时,意谓乃是被完全纳入认识的共相本身。这是一条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为止求“我思”的道路。
(三)利用语言对实在的颠倒功能
在感性确定性内部,作为对象的这一个和作为自我的这一个还是抽象的相互独立。当我们用语言说出意谓是“这一个”时,我们同时是把“这一个”当作普遍的东西来说的。这样一来,意谓的“这一个”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而保存下来的是作为抽象共相的“这一个”。这样一来,认识和对象、语言与实在原先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语言是较真实的东西: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否定了我们的意谓;并且既然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语言仅仅表达这种真理,所以要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2]66。正因为如此,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转变为共相和语言的真理性。“因为那感性的‘这一个’是语言所不能到达的,而语言是属于意识范围,亦即属于本身是共相或普遍性的范围”[2]72。语言和实在本身存在着一种矛盾,语言不可能完全穷尽实在。但是,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则把语言作为概念和共相的本性泛化和神圣化了:“语言具有这样的神圣性质,即它能够直接地把意谓颠倒过来,使它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即共相),因而使意谓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2]73意谓真的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吗?不是。原则上,意谓并不是“不可言说的”,而只是语言是“不可穷尽”的。事实上,语言除了有普遍的规范作用以外,它本身就是人们情感和生存状态的原初表达。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语言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的普遍的规范性和可传达性,至于语言的模糊性和对情感的表达性,语言的这些“杂质”对概念思维来说恰恰是要清洗掉的。这样一来,黑格尔就不给概念思维以外通达世界的方式留下任何余地,感性确定性最终失去了一切合法性。黑格尔“将感性活动所获得的丰富意谓扬弃和消融在抽象意识的概念、共相之中,将一切不可说的东西(或不如说:不可规范、不可穷尽的东西)在科学和理性的蒸馏器中蒸发掉——这就是思辨哲学的秘密”[6]160。
概而言之,《精神现象学》虽然以感性确定性为开端,但是由于黑格尔仍处在近代哲学知识论的传统中,以意识哲学为其隐性立场,所以抽象思维的运动最终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用共相吞没了感性。海德格尔后来对近代意识哲学的这种内在运行机制有着深刻的揭示:“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8]由此可见,从理性思辨专制下拯救出人的感性,重新确立感性本身的合法地位,就成为黑格尔哲学以后的主要任务。
三、从两个不同路向看感性的重新确立
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曾称黑格尔哲学是“普照的太阳”,但是,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这一“普照的太阳落山了”。卡尔·洛维特后来在回顾和总结黑格尔逝世12年以后新哲学的发展状况时说:“恰好是1843年这一年决定了以后一百年哲学的命运,这一命运现在才又变得可见了。在这同一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这些19世纪的最后一批亦或是第一批哲学家们想理解从现实得出的共同原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或一种纯粹的‘理性’或一种绝对‘精神’,而是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9]29洛维特的这一概括非常准确。黑格尔哲学以后,对感性的肯定重新沿着两个基本路向展开。一个是在非理性主义哲学那里得到肯定;另一个是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得到肯定。在前一种路向上,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尼采是典型代表;在后一种路向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典型代表。
首先,看以克尔凯郭尔为首所代表的非理性趋向。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抗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思辨化倾向,谴责他把哲学和宗教结合的泛神论做法;二是突出个人面对虚无的绝望和生存状态,用生活的辩证法对抗黑格尔思维的辩证法。就克尔凯郭尔哲学来说,他的焦点始终是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在此意义上,他通常被看作是第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
至于叔本华,众所周知他是第一个在黑格尔活着时公开和黑格尔对抗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是意志。世界根本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展开,而是意志盲目冲突的结果。至于人的认识,叔本华认同康德的批判哲学,认为直观是世界的真理,表象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那种认为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是第二性的观点是把事情搞反了。“从我全部的基本观点看来,这一切说法都是把实际的关系弄颠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10]。这样被黑格尔哲学忽视和打发掉的感性又作为人的生命活动被肯定下来。
叔本华的悲意志论哲学深深地影响了尼采,尼采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中走出来后形成了自己的“强力意志”学说。尼采明确肯定生命意志的积极方面和对理性认识的基础地位。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和悲剧哲学就是对生命意志的最大张扬,理性认识只不过是强力意志更好地实现的手段而已。“对痛苦本身的肯定,对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东西的肯定……这种最后的、最欢乐的、热情洋溢的生命肯定,不仅是至上的认识,同时也是为真理和科学所严格证实的认识,并且成了科学和真理的基础”[11]。
其次,再看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上文洛维特所说,费尔巴哈哲学的贡献就在于用“感性直观”取代黑格尔的“理性思辨”。由于费尔巴哈重新把感性和感性意识理解为人的实在性及其最后确证,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费尔巴哈在哲学上是一种感觉论和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的恢复。在费尔巴哈那里,所谓的感性,首先是指对象在感觉之外存在,同时也是在语言和思维之外存在。费尔巴哈说:“这种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12]68这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意识表明的就是感性存在,这几乎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以语言为共相对感性意识的吞没应该重新被颠倒过来:对于感性意识来说,一切语词都不过是专名(Nomina proria),是意识的符号,因此,“对于感性意识来说,语言正是不实在的东西,虚无的东西”[12]68。黑格尔之所以根据语言否定感性确定性,那是因为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地考察过感性意识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评价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主要在于“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13]。
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哲学过分注重直观和自然,因此他的哲学缺陷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黑格尔哲学缺陷,而且还从根本上放弃了黑格尔哲学能动的方面,尤其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和否定性的辩证法。这样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缺陷克服之路就只走了一半。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被马克思所克服,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54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4]78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最终被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代替。这样,费尔巴哈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过渡的中介。马克思最终用“感性活动”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
总之,黑格尔哲学以后,理性的至上性和绝对性的地位被动摇了。正如洛维特所说,以上两种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路向虽然不同,但他们都开始从“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出发。这是黑格尔以后这些学说具有的一个“统一的基本特征”,即“这个基本特征也因此贯穿在他们对黑格尔的纯粹‘思维’的三重批判中,这种批判是在给‘激情’(克尔凯郭尔)、‘感性直观’和‘感觉’(费尔巴哈)、‘感性活动’或者‘实践’(马克思)恢复名誉的旗号下进行的”[9]29。这就是说,黑格尔以后,哲学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但共同点都已和近代意识哲学的知识论的传统不同。具体说,以上这两种新路向已经共同代表了一种“生存哲学”的新路向。
[1]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5.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罗伯中.论黑格尔的感性确知概念[J].学术研究,2006(3).
[4] Donald Phillip Verene.Hegel’s absolute :an introduction to read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44.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4.
[6]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C].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3):55.
[9] 卡尔·洛维特.克尔凯郭尔与尼采[C].李理,译.哲学译丛,2001(1).
[10]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01.
[11] 尼采.看哪这人:尼采自述[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9.
[12]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2.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