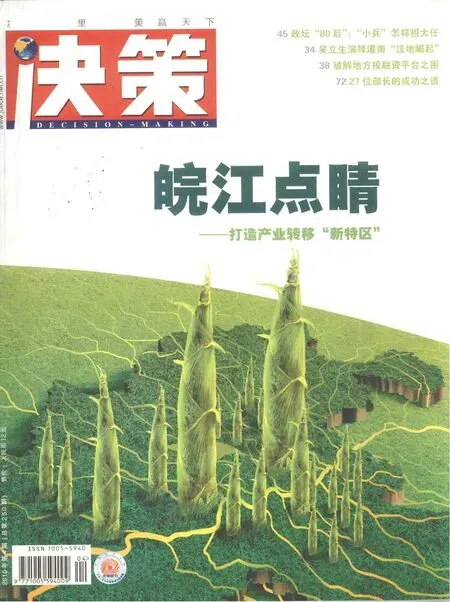蕉岭草根民主试验
2010-03-01刘龙飞
■马 华 刘龙飞
一场以防治村官腐败为初衷的农村治理改革试点,在广东省蕉岭县启动。这种制度体系被概括为“一种草根式的权力平衡”。
一群对农村充满兴趣与理想的“80后”,主导了一次“蕉岭试验”,试图为新世纪农村建设探索一条新路,为现阶段农村诸多治理和发展问题求解。
多方力量的参与,使得这场试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学界的理论和村庄现实的结合,则激起了创新的火花。在广东这个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对农村建设和发展模式的大胆试水,再一次吸引了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目光。
村务监事会横空出世
败为初衷的农村治理改革试点,在广东省蕉岭县三圳镇启动。
2009年7月,试验村之一广育村成立了村务监事会,力图从加强监督权入手,改变该村的治理现状。实际上,由于长期监督的缺失,村务公开流于形式,广育村村民怀疑该村100 多万的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被前任主任及其家族私吞,充满愤怒的村民利用一年前的村委会换届,在一举将前村主任“选下台”之后,少数村民仍然不断上访,致使该村一度成为蕉岭县的“问题村”。
为了避免缺乏监督给村庄继续带来危害,课题组在决定借鉴当地纪委部门的实践探索,从加强监督权入手,在村庄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这种制度体系被徐勇教授概括为:“一种草根式的权力平衡”。它通过成立“村务监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召集组”,确定“监事会监督、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的村级权力结构形式。“村务监事会”专职监督,其成员由村里“三老”
在村民自治全面铺开的过程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基层民主的核心内容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村民自治中的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失去监督的权力在村庄肆虐,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危害。
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是村务监事会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卢尧生对于村民自治问题十分了解,“一方面村民自治后,村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另一方面民主监督乏力,成为村民自治中最薄弱、最难发挥效益的一个环节。”

2007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农实验课题组和蕉岭纪委的帮助下,一场以防治村官腐(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担当,这些村庄的“长老”往往“荣誉感强、有责任心,并且有较丰富的知识经验和业余时间,监督村干部也少有顾忌”,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介绍。而“村务监事会”定期向上级纪委反映情况,则更增强了这一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督效果。
“村务监事会”监督着村委会,而专门负责召集村民或村民代表召开决策会议的“村代会召集组”,则是村庄权力体系三足鼎立中的另外一足。涉及到集体利益的决策,或者有部分村民提出需要讨论的决议,都需要“召集组”负责召集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才能最终决定,召集组成员对这一规定早已烂熟于心,并随时准备发挥自己的作用。
“监事会的特点就是让监督贯穿于村委会的村务决策、村务管理之中,对村务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面监督。”而村代会召集组则“让村代会真正掌握决策权和监督权,让村民真正参与到村务决策和管理中来,必要时候,他可以组织村民大会,启动罢免村干部程序,对村委会产生必要的威慑作用。”在对这套权力制衡体系进行概括的时候,卢尧生介绍说。
广育村对这一制度体系借鉴的时候,将村务监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确定为“召开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大会,协商提名候选人后,通过选举产生”,从而使这一机构对村干部更具威慑,面对这一监督体系,该村主任长叹一声说:“广育村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组织机构,而且是经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我现在是上面有县镇纪委监督,下面有‘村纪委’监督,看来想犯错误都难啊!”
监督权得到保障为农村的“善治”打开了突破口,广育村信访量的下降和干群关系的缓和,则是其最明显的效果。“这个模式虽然现在看起来很粗糙,但背后隐藏的理念是很深刻的”,在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徐勇教授对这一模式的价值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这种“草根式的权力平衡”,使得“受监督的权力更有力量”,蕉岭的试验,“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模式,是观察社会转型时期乡村问题的一个窗口。”
“让合作成为村民的习惯”
能力建设是农村“善治”的决定性因素,现阶段农民表达和合作能力的不足,直接制约了乡村内生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根据南农试验对4 个试点村的一项评估调查,试验村普遍存在着村民不能正确识别利益,政策、法规掌握程度低,语言文字能力较差,乡镇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较弱,农村制度化表达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缺乏利益表达能力,使农民在公共政治参与中输在了起点,而缺乏组织合作能力,则使他们失去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
曾坑村是广育村的一个自然村,居住人口有300 人左右,该村距离村委会有8 公里左右的山路,长期以来由于道路原因,曾坑村民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曾坑所拥有的丰富钾长石矿也无法运输出来,影响了这部分人口的生活和发展。为了能打通与外界联系的路线,该村村民一直渴望能修好从该村到村主干道的水泥道路,但是由于工程耗资较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该村村民的意见比较强烈。2008年,南农试验课题组入村后,通过与村干部和部分村民的协商,最终确定了一方面组织村干部到蕉岭县农业局以及广福镇政府,为争取项目资金进行积极的游说工作,另一方面发动村民筹资投劳的方式修建曾坑公路。
去蕉岭县政府部门筹集资金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刚当选村委主任不久的黄坤荣身上,黄虽然曾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但是性格比较内向,“第一次和县领导说话的时候,我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楚。”回忆起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和县领导说话的情景,黄坤荣说。
最终在课题组成员与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上级部门答应了出资大部分、村民集资部分的形式修好曾坑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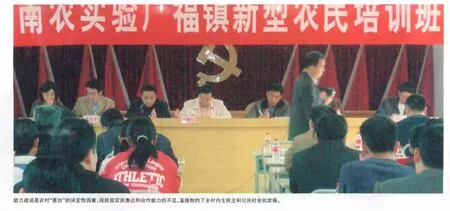
“通过曾坑公路建设,一方面培养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现任村干部的能力得到迅速的提升”,曾坑公路建设唤醒了村民的参与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使得村民更加懂得如何通过表达提出利益要求,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利益。曾坑公路修好之后,在课题组的提议下,曾坑公民自己组织了护路理事会,自己筹资开展了曾坑公路灯亮化工程。在曾坑的感染下,广育村的其他自然村也自发组织筹资,使本村的路灯亮了起来,截至2009年1月,整个广育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灯光亮化工程,该工程不仅没用国家一分钱,而且维持其运行的电力成本问题也在村民的协商参与下得到解决。
“农民一旦学会解决村庄公共问题的方式,会在村庄记忆当中得以保留”,徐勇对村民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解释。而对于课题组来说,在修建曾坑公路期间的努力,使他们真正打开了培养村民政治参与能力的突破口,课题组成员惊喜的发现,村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随后村里的自来水管道修建、矿产纠纷事件等,都在村民的合作和民主协商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民主成为村民的习惯”。
蕉岭试验能走多远?
“蕉岭模式”的诞生以及村民合作与表达能力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说,是外力(研究机构、媒体、地方政府等)介入下的通过完善农村制度建设、培养村民能力、培育村庄内生力量的方式促进乡村治理。对这种模式,有学者担心,一旦缺少了外力的推动,这种创新很可能会举步维艰。事实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进行的几次村治试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试验时轰轰烈烈,试验结束后,村庄又恢复原状。因此,摆在课题组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外力退出,如何让这种治理模式依靠农村内生力量顺利运转?”
“很多地方的制度创新都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甚至是采取一种强行入轨的手段来推进的。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也挺有意思”,外力的介入,目的在于改革分权,而推动改革,则需要集权的力量,矛盾由此而生。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党国英教授,则提出质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考虑成本。一个小村庄,能有多少公共事务,有必要叠床架屋地搞那么复杂吗?”他认为,蕉岭纪委和南农试验课题组实践的村治模式,面临着成本过高的问题。
实际上,随着试验的不断深入,课题组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外力推动下的农村治理模式,如何避免在失去外力推动后回到原点?试验结束退出村庄之后,到底能给村庄留下些什么?
2009年12月30日,南农试验第二期项目正式开始,这期主题为“农村资源整合与地方治理创新”的项目,将以培育农村内生力量和内在机制为基础,对接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激活市场机制与乡村社会资本,通过整合村庄内外部资源激活农村的本土崛起。
与前一期工作相似,南农试验的第二期工作也将采取多方参与的方式进行,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的联合将成为继续推进的动力。但课题组这一次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这种外力推动的治理方式融入村庄内部之中,如何通过内在机制的培养,让民主成为村民的习惯,让制度成为村民的一种理念,让内在力量成为村庄崛起的根本动力。
这无疑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但却是更有意义的一次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