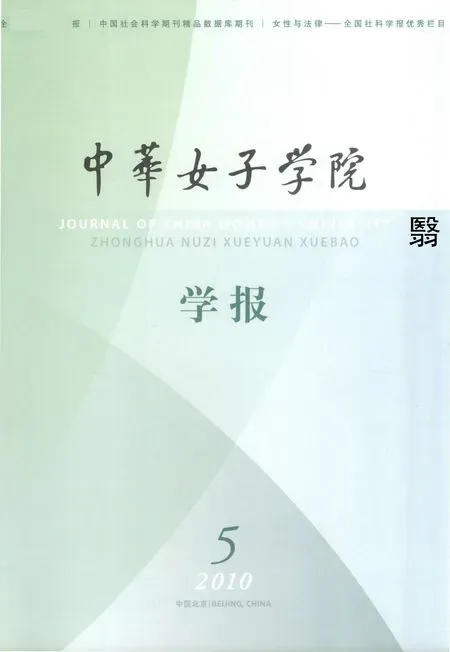清末女子留日运动述论
2010-02-16谢忠强
谢忠强
(运城学院 思政部,山西 运城 044000)
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新旧文化转型的媒介,更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载体。故而,留日学生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综观目前既有之成果,论者多着墨于男性留日学生,而鲜有关于女性留日学生之专论。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依据零星资料的相互印证,对清末女子的留日运动进行初步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几乎都被禁锢在家庭中,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更难言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中国近代社会虽从1842年后即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艰难历程,但“直到戊戌维新时期,近代妇女运动才真正兴起。”[1](P69)
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竟惨败蕞尔小岛,赔款割地,震动一时人心。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提倡向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和通过明治维新而富强起来的日本学习。维新派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妇女问题。他们以进化论、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为武器,积极宣传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指出,“中国女学之废久矣。海内之女二万万,求其解文义,娴雕虫,能为花草风月之言者,则已如凤毛麟角,若稍读古书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圆氏其人者,则普天率土几绝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乌得为学问矣乎?而其聊绝也若是。记曰:‘人不学,不知道’,群二万万不知道之人,则乌可以为国矣!”[2](P386)除痛陈清末传统女子教育现状之不堪外,梁启超还直截了当地把女学的兴衰提高到了“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高度。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要救亡图存“非提倡女学讲求胎教不可”。他还十分形象地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失教,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 ,印度 ,波斯、土耳其是也。”[3](卷一)
维新派对女学教育重要性的宣传逐渐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1898年前后,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掀起了国内反缠足、办女学的妇女解放运动,进步人士开始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年在不少大城市以及南方的个别县城都办起了为数不等的女子学校。”[4](P134)国内女学的大量涌现为清末女子赴日留学提供了直接的原动力。毕竟普及教育需要有充足的师资,而当时的状况是,女学的大量出现和要发展女学,却没有足够的女教员(当时清廷规定,女学校不能用男教师),这不能不说是影响当时女子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由于国内教育制度未立,设备缺乏,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女教师,于是,有识之士主张女子留学,使之接受教育以充实国内女学师资。[5](P54)以周馥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就坚决主张,“欲遍设女学,亦非于此时兼派女子速成师范及养成女子教员不可。”[6]而清末女子出洋留学,出于诸多现实的因素考虑,多将日本当成首选。一则“日本女子的文化程度与我国相去不远,中国女子的才智能够赶得上她们”,再则“中国与日本距离较近,便于往返”,三则“学费节省,便于苦读。”[1](P329)
除了国内兴办新式女子教育的大量人才需求之驱动外,当时日本国内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也为推动清末女子留学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为缓和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对日之仇视,表示愿意资助中国学生留日并呼吁日本政府予以政策支持。”[7]为配合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政策,日本女子教育界也积极行动,希望中国女子赴日学习。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日本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望月兴三郎向他力陈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8](P747),进而建议清政府重视日本的女学模式。日本著名女学人下田歌子更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望或一二人先尝试,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9]显而易见,日本女学教育界人士的良好愿望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在培养新女性方面的共识,大大推动了清末女子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
二
清末国人留学日本之运动起于甲午中日战后,但早在1870年浙江宁波人金雅妹就“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入日本求学”[10](P273),堪称清末女子留学第一人。继金雅妹之后,1899年6月,9岁的夏循兰随家人到日本,就读于下田歌子任教的华族女子学校。1900年,钱丰保随父兄一起赴日。1901年上半年,在下田歌子于日本东京麴町创设的帝国妇人协会中,设立了招收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实践女子学校。1902年6月,吴稚晖订立广东大学堂章程后赴日时,与他同行之“曹丽云、陈彦安、华桂、胡彬夏、周佩珍、俞文婉、冯袁塞和吴芙”等八女多入该校学习。[5](P55)1903年后,留日女学生日渐增多。一些爱国女青年为了赴日留学,冲破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克服经济上的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到东京去。据统计,截至1904年底,在日的中国女留学生已超过50人。
从1870年到1904年,清末女子留学日本的人数上虽然有所增加,但“从女学生的年龄、未曾毕业即随父兄回国,以及其丈夫留学日本等史实来看”,这一时期女留学生大都是以伴读身份来日就读的“附属”留学生,且多为自费,尚不具备“明确的留学目的”。[11](P37)是为清末女子留日运动的初期发展阶段。
为了更科学地引导、规范女子留学日本,清廷驻日公使杨枢通过各省同乡会和东京留学生会馆向国内宣传一些注意事项,“诸如行李不宜多带”,“衣服以青、蓝二色为主”,“装饰不宜用钗环钏镯之类”,“不要带女仆”,“来前要放足”,“及早与东京的留学生会馆取得联系”等。[12](P136)随着清廷鼓励留日政策的推行、留日条件的宽松以及留日女子的大力宣传,进入1905年,赴日女子日渐增多。“1905年3月,奉天省旗女静婉,自备费用率女伴7人前往日本留学;5月,云南有13名女子赴日;9月,广西容县的陆书蕉和陆菱娟在龙胆女学堂毕业后,一起东渡;湖南王恒之偕其女弟赴日留学,有20余名女学生同行。”[5](P58)安徽庐江的吴弱男、吴亚男姐妹也于这一年到达日本,分别进入青山米国女学院和英和女学校学习。另外,辽宁省派熊希龄到日本考察教育后,即和下田歌子签订合同,每年派15名女子到实践女子学校学习。据统计,1905年在日留学的中国女子已超过百人。进入1906年后,随着清廷对留学日本管理的加强,留学日本进入有组织时期,在女子留日方面,虽然自费女生仍占多数,但官派留日女子开始有所增加并呈现出一定的计划性。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一次就派了21名学生到实践女校攻读速成师范科,同时将原来自费留日的钟肇子、韩淑瑶、富伯贞、杨庄、黄国巽、黄辉等人拨改官费。[13]同年,江西南城的欧阳雅琴、江苏的王季昭和杨荫榆等也都奉官派东渡。截至1907年12月,中国留日女生总数达139人之多,并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
很明显,从1905年到1907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中国女子留日学生无论是从人数的增加,还是从其明确的留学目的来看,均较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可谓清末女子留日运动的高潮时期。
1908年之后,鉴于经过前两个发展阶段的积累,中国女子留日的规模、运作模式均已稳定,中日两国的教育管理部门便逐渐加强了对中国女子留日运动的管理和约束,以提高其学习质量。如,日方在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协进会”上决定废止速成科、改设学制3年的普通科和师范科的基础上,1908年4月日本的实践女子学校又制定了新的《外国留学生规程》,用以规范中国女子的留学运动。《外国留学生规程》明确规定了入学者的资格限制和10条学生守则。此规程的制定,使中国女学生的入校制度和在校管理更加严格,学生们的在校活动完全处于校方的监督、管理之中。无独有偶,1910年7月,清廷学部更出台了限制女子留日的政策:“女生游学,为养成母教之基,关系至重。中国女学尚未发达,虽不能限以中学毕业程度,亦应慎重选择。嗣后女生自费赴日,应由地方官呈请学司考验,必须受过本国教育,文理明顺,品行聪淑者,地方给咨东渡,否则,仍令入本省学堂肄业。至自费补官费,应以考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奈良女子师范、蚕业讲习所三部女校为限,照考取等第,挨次推补。其从前记名女生,非考入以上三校者一律除名。”[14]
由于中日两国对于中国女子留学教育门槛的抬高、国内新式女子学堂培养人才的增多以及部分留日女生的学成归国已大大缓解了国内对于新式女性人才的需求,再加上中国女性赴欧美留学者日渐增多,从1908至1911年的四年间,中国留日女子人数一直没有太大的增加。据统计,在1908年至1910年清末女子留日运动的末期,中国女子在日学习人数每年始终维持在100人左右。“1908年为126人,1909年为149人,1910年为125人”,1911年则“迅速降至81人”。[5](P60)
三
清末的中国女子留日运动前后共经历了从“萌芽探索”到“高潮发展”,再到“约束规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间虽历经了近30年的漫长历史,但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中国女子留学日本者之数目“仅及男子的百分之一”。[15](P56)应该说,从清末留日的女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总数与清末中国将近“二万万”妇女之间的比例来看,清末留日女子的数量实在是太过微小,甚至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然而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我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末中国女子留日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进行认真总结。
首先,清末女子留日不仅大大推动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他们在留日期间所展示出的良好精神风貌,也为中国女性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尊重。明治维新后,日本特别重视女子教育,其贤妻良母式的教育理念相对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文化体制的巨大优越性,一度使日本国内对中国女性形成了“鄙夷”和“轻视”的固定化思维模式。然而,当中国女子逐渐留日后,通过其良好精神风貌的展示,大大改变了此前日本国内对中国女性的偏见。据1902年12月份的《大陆》杂志《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之声价》一文评论,中国女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也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留学生中有夫婿在东京留学者,会晤之际,其应对之仪式,周旋之情谊,实称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以今观之,殊为不然。”[15](P54)另据下田歌子评论,“中国妇女概言之,伶俐且敏慧,教以一事,不崇朝而已谙熟不忘,亦有一隅反三者”,而且还“善娴交际,而巧应对”,“今视其情态,旋似美国妇人,此明标进取气象者,非吾邦妇人,专以温顺贞婉为要之可比也。”[16]
其次,清末女子留日运动通过对女权运动的亲身实践和宣传,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压迫妇女的种种陋俗痼习,留日女生坚决主张改良而革除之。1903年4月8日,中国留日女生组成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甫一成立,就呼吁女生“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根据此宗旨,留日女生以《江苏》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兴女学、恢复女子独立人格等妇女解放的文章。为了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清末留日女生还组织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子复权会”、“留日女学会”等社团组织,创办了《女学报》《女子魂》《白话》《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留日女学会杂志》等刊物,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及为取悦男性而缠足的礼教遗毒。
再次,留日女生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合法权利的侵犯,同时也显示了其自身的革命力量。随着新思想的日益普及,清末留日女生的爱国热情也不断高涨。1903年4月份“拒俄运动”起,中国留日女生积极投身其中。“留学女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17]部分女生还加入了日本红十字会笃志护士会,学习救护,为投入战斗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8]虽然最后由于来自清廷和日本政府等各方面的干涉,学生军终未回国,但运动中女学生们的行动,显示了其高度的爱国热情和独立的斗争姿态。
最后,清末女子留日运动还大大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甚至有些女留学生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为推翻清廷的腐朽统治作出了积极贡献。清廷的腐朽使留日女生的救国道路逐渐转向了革命。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先后有何香凝、秋瑾等近20余名留日女生参加其中。他们为了准备国内起义,不仅捐资献物,而且将生死置之度外,或者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派组织的暗杀等革命活动,或者利用女性之便屡次由国外向国内运送弹药、传递情报,或者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战地救护活动。留日女生在日本及回国后的革命活动,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
[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2]陈元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
[4]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5]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6]周馥.江督周咨商江西巡抚选派养成教员公文[J].教育杂志(直隶),1905,(4).
[7]谢忠强.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8]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3.
[9]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J].游学译编,1902,(1).
[10]周棉.中国留学生大辞典[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3]选派留学日本女学生之姓名[J].直隶教育杂志,1907,(3).
[14]记事:学部慎重女生游学[J].教育杂志,1910,(8).
[15]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6]下田歌子.述教育中国妇女事[N].顺天时报,1907-01-12.
[17]学生军缘起[J].湖北学生界,1903,(1).
[18]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会社之缘起[J].浙江潮,1903,(5).